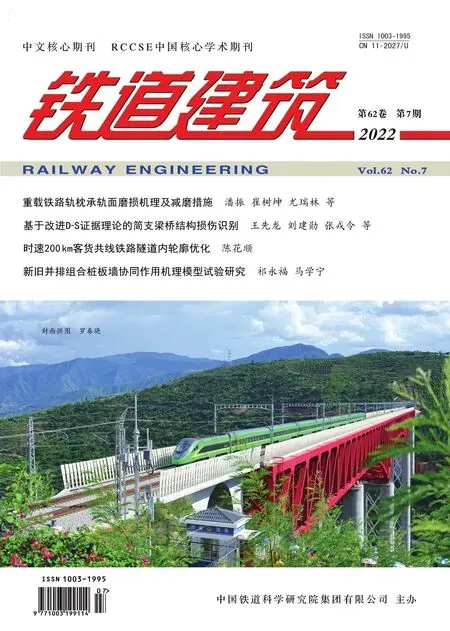基于BP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算法的大變形隧道位移監(jiān)測(cè)數(shù)據(jù)分析與應(yīng)用
劉博峰
中國(guó)交通建設(shè)股份有限公司軌道交通分公司,北京 100088
新奧法是應(yīng)用巖體力學(xué)理論,以維護(hù)和利用圍巖的自身承載能力為基礎(chǔ),采用錨桿和噴射混凝土為主要支護(hù)手段,控制圍巖的變形和松弛,使圍巖成為支護(hù)體系的組成部分,并通過(guò)對(duì)圍巖和支護(hù)的量測(cè)、監(jiān)控來(lái)指導(dǎo)施工,其已廣泛應(yīng)用于我國(guó)山嶺隧道[1-5]。為掌握施工過(guò)程中圍巖穩(wěn)定程度和支護(hù)結(jié)構(gòu)受力、變形的動(dòng)態(tài)信息,隧道開(kāi)挖后應(yīng)及時(shí)監(jiān)測(cè),并把結(jié)果和建議反饋給參建各方,以達(dá)到指導(dǎo)施工和動(dòng)態(tài)設(shè)計(jì)的目的。監(jiān)控量測(cè)貫穿施工全過(guò)程,其中位移測(cè)量簡(jiǎn)單可行并且意義重大。隧道位移影響因素有很多,但對(duì)監(jiān)測(cè)數(shù)據(jù)的常規(guī)分析,大部分采用一元非線性回歸,所有因素的作用效果均以時(shí)間的變化體現(xiàn),沒(méi)有考慮各個(gè)因素的相互影響。
本文以連接中國(guó)云南省昆明市與老撾萬(wàn)象市的電氣化鐵路線上的景寨隧道為例,利用BP(Back Propagation)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算法的數(shù)據(jù)驅(qū)動(dòng)自適應(yīng)和多維函數(shù)映射能力,編制程序分析在時(shí)間和距掌子面距離雙重影響下隧道拱頂沉降和凈空變化規(guī)律,為同類隧道監(jiān)測(cè)數(shù)據(jù)的分析提供一種新思路。
1 工程概況及監(jiān)測(cè)方案
1.1 工程概況
景寨隧道總長(zhǎng)9 509 m,圍巖以泥巖、頁(yè)巖、板巖等軟巖為主,受構(gòu)造影響節(jié)理裂隙發(fā)育,巖體破碎。由于隧址區(qū)存在高地應(yīng)力、順層偏壓、斷層破碎帶等不良地質(zhì),部分段落在開(kāi)挖過(guò)程中圍巖變形過(guò)大,變形速率快,變形持續(xù)時(shí)間長(zhǎng),導(dǎo)致掌子面后方初期支護(hù)段變形嚴(yán)重,拱架扭斷變形。個(gè)別監(jiān)測(cè)斷面單日最大變形超過(guò)24 cm,累計(jì)最大變形超過(guò)180 cm。隧道施工安全風(fēng)險(xiǎn)高,對(duì)監(jiān)測(cè)數(shù)據(jù)依賴性強(qiáng)。
1.2 位移監(jiān)測(cè)方案
根據(jù)Q/CR 9218—2015《鐵路隧道監(jiān)控量測(cè)技術(shù)規(guī)程》,隧道拱頂沉降和凈空變化為必測(cè)項(xiàng)目。根據(jù)圍巖情況,在圍巖地質(zhì)條件較好區(qū)段監(jiān)測(cè)斷面間距取10 m,各監(jiān)測(cè)斷面布置2~3 對(duì)測(cè)點(diǎn);在地質(zhì)條件較差區(qū)段如DK409+130—DK409+165 區(qū)段監(jiān)測(cè)斷面間距取5 m,每個(gè)斷面布置5對(duì)測(cè)點(diǎn),如圖1所示。

圖1 地質(zhì)條件較差區(qū)段變形測(cè)點(diǎn)布置
利用BP 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算法,對(duì)隧道大變形段DK409+145—DK409+165 一典型斷面的隧道拱頂沉降、凈空變化進(jìn)行數(shù)據(jù)分析,根據(jù)分析結(jié)果對(duì)隧道變形發(fā)展進(jìn)行預(yù)測(cè)。
2 變形實(shí)測(cè)數(shù)據(jù)分析
隧道變形與時(shí)間、距掌子面距離的關(guān)系曲線見(jiàn)圖2。時(shí)間軸0 點(diǎn)對(duì)應(yīng)的日期為2020 年12 月5 日。因不同斷面支護(hù)時(shí)間不同,以變形速率顯著減小時(shí),即各斷面距掌子面距離為15 m 處作為支護(hù)前后的分界點(diǎn)。

圖2 隧道變形與時(shí)間、距掌子面距離的關(guān)系曲線
由圖2 可知:①支護(hù)前各斷面變形均隨距掌子面距離增加而快速增加;支護(hù)施作后變形逐漸趨于穩(wěn)定。其中DK409+155—DK409+160 區(qū)段的拱頂沉降、拱肩和邊墻的水平收斂較大,并且距掌子面距離越近,變形速率增長(zhǎng)越快,說(shuō)明在該區(qū)段巖體易受擾動(dòng),穩(wěn)定性差,施工過(guò)程中需加強(qiáng)監(jiān)測(cè)并及時(shí)采取強(qiáng)支護(hù)。②與其他4 個(gè)斷面相同部位相比,斷面DK409+165 的最終水平收斂較小,說(shuō)明該處巖體具有良好的抗側(cè)向變形能力。③斷面DK409+145、DK409+150拱頂沉降增長(zhǎng)速率較小,開(kāi)挖支護(hù)后受距掌子面距離的影響小,說(shuō)明該處巖體抗豎向變形能力良好。④DK409+155—DK409+160 區(qū)段隧道在支護(hù)前拱頂沉降急劇增長(zhǎng),及時(shí)支護(hù)后變形曲線逐漸近似平行于距離軸。距掌子面距離超過(guò)75 m 后,則轉(zhuǎn)為近平行于時(shí)間軸(圖2 圈中區(qū)域),即變形曲線受時(shí)間的影響增大,表明在支護(hù)前變形受距掌子面的距離和時(shí)間雙重影響,支護(hù)后巖體受臨近施工掌子面擾動(dòng)較大,使其變形隨距掌子面距離(15 ~ 75 m 范圍內(nèi))增加而逐漸增加,距掌子面的距離大于75 m 后,斷面受施工擾動(dòng)的影響降低,此時(shí)斷面以蠕動(dòng)變形為主。距離與時(shí)間對(duì)隧道不同施工階段的變形有顯著影響,因此預(yù)測(cè)在兩個(gè)因素共同作用下隧道變形趨勢(shì),將有利于施工中提前采取合理措施。
3 BP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算法
BP 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算法是一種按誤差逆?zhèn)鞑ビ?xùn)練的多層前饋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算法,應(yīng)用較廣泛[6-8]。一般分為輸入層、輸出層及隱層,層間各個(gè)神經(jīng)元之間全連接,而每一層內(nèi)的神經(jīng)元不連接。該算法的學(xué)習(xí)過(guò)程包括數(shù)據(jù)正向計(jì)算及誤差反向傳播,通過(guò)不斷迭代計(jì)算最終給出在滿足誤差要求下輸入值和輸出值之間的關(guān)系。由于隱層的存在,算法具有多維非線性函數(shù)映射能力,已有理論證明三層結(jié)構(gòu)的BP 網(wǎng)絡(luò)能夠以任意精度逼近任何非線性連續(xù)函數(shù)[9]。BP 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如圖3 所示。其中x1、x2為輸入層參數(shù);h11—h14為第一層隱層結(jié)點(diǎn);h21—h24為第二層隱層結(jié)點(diǎn);y為輸出層參數(shù)。

圖3 BP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示意
4 BP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算法的工程應(yīng)用
4.1 數(shù)據(jù)分析模型建立
采用回歸分析法對(duì)隧道位移進(jìn)行分析。回歸函數(shù)方程有指數(shù)、對(duì)數(shù)、雙曲線函數(shù)等[10]形式。在滿足規(guī)范要求的基礎(chǔ)上,為了提高模型的精確度,結(jié)合本項(xiàng)目施工現(xiàn)場(chǎng)實(shí)際需求,數(shù)據(jù)模型輸入層有時(shí)間和距掌子面距離兩個(gè)參數(shù);輸出層只有位移一個(gè)參數(shù)。
4.2 計(jì)算流程和預(yù)測(cè)方法
經(jīng)試算,數(shù)據(jù)分析模型中的BP 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設(shè)定為含有2個(gè)隱層的4層結(jié)構(gòu),2個(gè)隱層的結(jié)點(diǎn)均為4,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為2?4?4?1。為了更好地匹配訓(xùn)練函數(shù),對(duì)輸入數(shù)據(jù)進(jìn)行標(biāo)準(zhǔn)化處理,使其均位于[0,1]區(qū)間。計(jì)算流程如圖4 所示,采用雙控制條件(誤差和總訓(xùn)練次數(shù))同時(shí)控制算法進(jìn)程。將達(dá)到最大指定次數(shù)后輸出誤差最小的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參數(shù)用于數(shù)據(jù)預(yù)測(cè)。

圖4 BP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計(jì)算流程
斷面DK409+135 的拱頂沉降實(shí)測(cè)值見(jiàn)表1(僅列出奇數(shù)號(hào)數(shù)據(jù))。BP 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計(jì)算采用擬合、預(yù)測(cè)的方式循環(huán)進(jìn)行,即先利用1—15號(hào)實(shí)測(cè)數(shù)據(jù)進(jìn)行訓(xùn)練,對(duì)16—20 號(hào)數(shù)據(jù)進(jìn)行預(yù)測(cè),再利用1—20 號(hào)實(shí)測(cè)數(shù)據(jù)進(jìn)行訓(xùn)練,對(duì)21—25號(hào)數(shù)據(jù)進(jìn)行預(yù)測(cè),以此類推,考察BP 算法的回歸與預(yù)測(cè)能力。其中最終擬合值是對(duì)全部實(shí)測(cè)數(shù)據(jù)的擬合分析值,預(yù)測(cè)值為基于分階段實(shí)測(cè)數(shù)據(jù)的推測(cè)值。

表1 BP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算法拱頂沉降數(shù)據(jù)分析結(jié)果
4.3 預(yù)測(cè)結(jié)果分析
不考慮距掌子面距離的影響時(shí),根據(jù)不同數(shù)據(jù)預(yù)測(cè)的拱頂沉降時(shí)程曲線見(jiàn)圖5。

圖5 不考慮距離的影響時(shí)拱頂沉降時(shí)程曲線
從圖5(a)和圖5(c)可知:BP 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算法依賴于已經(jīng)給定數(shù)據(jù)的變化趨勢(shì),尤其是最后幾個(gè)數(shù)據(jù)的變化趨勢(shì)。對(duì)于圖5(b)中的突變,從算法層面無(wú)法預(yù)料,這導(dǎo)致圖5(b)中相關(guān)系數(shù)R2值比圖5(a)小。在圖5(c)中由于從第30 到第35 個(gè)實(shí)測(cè)數(shù)據(jù)一直近似呈線性遞增狀態(tài),使得BP 算法給出的預(yù)測(cè)數(shù)據(jù)仍然為遞增狀態(tài),而實(shí)際上從第875 h之后,即從第36個(gè)實(shí)測(cè)數(shù)據(jù)開(kāi)始,拱頂沉降增幅逐漸減小,這導(dǎo)致圖5(c)中實(shí)測(cè)值與預(yù)測(cè)值的R2進(jìn)一步減小,可見(jiàn)利用BP 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算法進(jìn)行數(shù)據(jù)預(yù)測(cè)時(shí),875 h之前數(shù)據(jù)變化趨勢(shì)占決定性地位。雖然圖5 中三組數(shù)據(jù)的R2值呈遞減狀態(tài),但整體仍接近于1,預(yù)測(cè)值仍具有一定參考價(jià)值。
為進(jìn)一步驗(yàn)證BP 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算法的準(zhǔn)確性,對(duì)拱頂沉降實(shí)測(cè)值、BP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算法擬合值及施工現(xiàn)場(chǎng)采用的指數(shù)函數(shù)擬合值進(jìn)行對(duì)比。BP 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算法擬合值、指數(shù)函數(shù)擬合值的均方根誤差分別為8.309、31.126,說(shuō)明利用BP 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算法得到的擬合值更貼合實(shí)測(cè)值。因此,采用BP 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算法擬合更加快捷、實(shí)用,且可達(dá)到較高精度。
5 結(jié)論與展望
通過(guò)對(duì)景寨隧道不同斷面位移數(shù)據(jù)進(jìn)行分析,采用BP 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算法對(duì)拱頂沉降進(jìn)行擬合與預(yù)測(cè),并與實(shí)測(cè)值、施工現(xiàn)場(chǎng)采用的指數(shù)函數(shù)擬合值進(jìn)行對(duì)比,得到如下結(jié)論:
1)斷面支護(hù)(距掌子面15 m 內(nèi))前隧道變形受距掌子面距離和時(shí)間雙重影響,支護(hù)后(距掌子面15 ~ 75 m)以受距離影響為主,距掌子面距離達(dá)到75 m后逐漸轉(zhuǎn)變?yōu)橐允軙r(shí)間影響為主。
2)考慮時(shí)間和距離兩個(gè)因素的BP 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算法在量測(cè)過(guò)程中可不斷進(jìn)行曲線擬合并給出預(yù)測(cè)值,使用靈活,且可達(dá)到較高精度,為隧道監(jiān)控量測(cè)數(shù)據(jù)的處理提供了一種新思路。
3)雖然BP 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算法具有優(yōu)越性,但其擬合及預(yù)測(cè)對(duì)初始輸入數(shù)據(jù)的依賴性強(qiáng)。以后可以增加更多原始數(shù)據(jù),如鋼支撐內(nèi)力、錨桿軸力、圍巖條件、地下水位等,使預(yù)測(cè)模型更貼合實(shí)際。BP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已有多種改進(jìn)算法,如遺傳算法、混沌算法、模擬退火算法等,后續(xù)可以利用改進(jìn)的BP 算法進(jìn)一步提高算法收斂速度及計(jì)算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