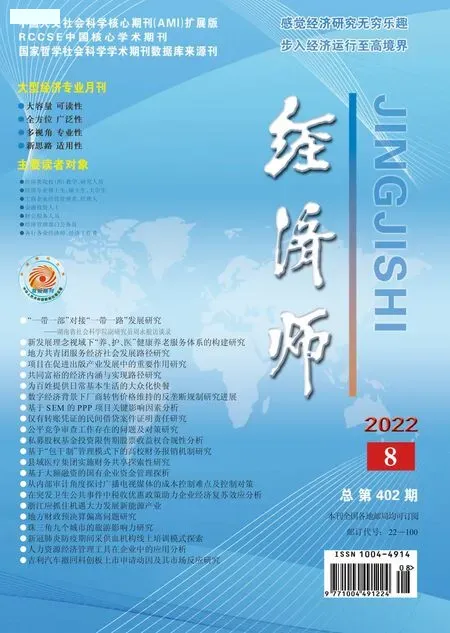私募股權基金投資限售期股票收益權合規性分析
●王瑞川 姚 丹
私募股權基金是資本市場中最為活躍的投資主體之一、作為投資企業撬動社會資本投向科技創新領域的重要投融資載體,存在投資限售期股票的可能和需求,本文以私募股權基金為視角,對于私募股權基金參與投資這一新興標的,通過主體地位、標的權利、交易模式等方面進行合規性分析。
一、標的方面分析:股票收益權、股票收益權轉讓的法律性質和實踐
(一)股票收益權為股權的一項權能
股票收益權作為新興投資標的,無明確的界定、缺乏法律規制,因此作為本文的研究核心和出發點,先進行分析:
首先,收益權概念早已有之,收益權是權利主體基于對資產的權屬,能夠獲得可預期收入的權利,于會計概念而言,所有資產未來均能夠帶來預期收入的流入,以此推論那所有資產都可以成為收益權的基礎資產(或稱底層資產),收益權需依附于其基礎資產,收益權的內涵與價值取決于基礎資產,基礎資產不同,衍生出諸多類型的收益權,常見的如票據收益權、應收賬款收益權、高速公路收費收益權等股票收益權概莫能外,同樣依附于基礎資產,也可剝離出來金融化,只是其依附的資產更加特殊,為上市公司股份,而前述列舉主要是基于債權關系衍生的收益權,此外還有物權收益權,如林地使用權收益權等。
其次,關于其他類型的資產收益權的規定在逐步出臺,如應收賬款項目收益權已經有監管法規中國人民銀行〔2017〕第3 號《應收賬款質押登記辦法》加以規定,2018 年中國人民銀行等四部委聯合出臺的《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規定,私募產品的投資范圍包括“未上市企業股權(含債轉股)和受(收)益權”,在一定條件下資產管理產品可以“投資于未上市企業股權及其受(收)益權”,這里的收益權應指的是股權收益權這一特定的收益權類型。
最后,股票收益權當屬基于股票所有權衍生的收益權,《民法典》總則編第五章統領性地規定了民事權利的類型,包括傳統的人格權、物權、債權、繼承權、知識產權,甚至包括數據、網絡虛擬財產這類新權利,當然也包括股權這一“投資性權利”,而股票收益權并非法律明文規定的任何一項單獨的民事權利,他產生于股權,屬于股權的一項權能,就類似于物權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權能一樣,派生于股權這一民事權利。
(二)股票收益權轉讓屬于債權請求權范疇
由于股票收益權并非單獨的民事權利,它不像物權、債權一樣可以單獨地發生移轉,物權變動和債權轉讓后都實實在在發生了權利人的變更轉換,例如債權人A 將對B 的債權轉讓給受讓人C,則B 未來履行債務償付義務是向C 而非A 履行的,而股票收益權轉讓卻未發生基礎關系的變動,股票持有人繼續享有對標的公司的股東權利,標的公司仍向股票持有人分配股利,而非向股票收益權的受讓方分配紅利。股票收益權轉讓可謂是一種虛擬的金融工具,基于信用而生、交易雙方通過合同條款來安排和創設,并未發生實際的轉移,因此,屬于債權性質,屬于請求權范疇。
股票收益權轉讓屬于債權請求權范疇,但有別于普通借貸的特殊的債權請求權,是一種特殊的投資關系。根據《公司法》第四條規定,“公司股東依法享有資產收益、參與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權利”,若僅將股票權利中的資產收益權能進行轉讓,在無特別約定的情況下,將不會影響到作為股東依法行使參與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權利。已有司法判例(如在“王志榮訴鄧振浩民間借貸糾紛〔2017〕滬01 民終17號”)一案中,法院結合股票收益權轉讓及相關協議內容,一般認為股票收益權轉讓及回購交易非單純的借貸關系,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性質非借款關系,由此可知,對于股票收益權轉讓及相關協議中法律關系性質問題,司法實踐態度目前比較一致,不會將其單純界定為借貸關系。
二、投資主體方面分析:私募股權基金與股票限售規制
私募股權基金以期滿退出為導向,在投資期內因投資方向和持股比例及股東地位等的不同可以分為不同類型的投資者,為了便于分析,在此與股票限售政策關聯,就與目標上市公司的關系而言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一是特殊投資者,主要指持股5%以上大股東、IPO 戰略配售方、上市公司定向增發投資方,此類投資者共同特征是對上市公司的經營管理具有重大影響。該類投資者轉讓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關于持有期限、賣出時間、賣出數量、賣出方式、信息披露等規定,并應當遵守證券交易所的業務規則。特殊投資者條件較為苛刻,比如定向增發對象的確認需通過上市公司股東會決議,戰略配售為發行人與主承銷商共同商定,往往對條件都有限定,尤其是IPO 階段往往需要與上市公司主營業務相關或者能夠產生戰略協同效應,因此,屏蔽了不少對于上市公司股票感興趣的外部投資者,這就是產生私募股權基金投資限售期股票需求的原因之一。
二是關聯投資者,主要包括上市公司的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等,此類投資者共同特征是掌握上市公司內幕信息,特殊投資者很可能也是關聯投資者,普通投資者若是目標公司的關聯方也可能成為關聯投資者。根據證券監管部門的窗口指導意見,上市公司作為實際控制人的關聯私募基金,無法直接參與該上市公司的非公開發行股票,這又成為產生私募股權基金投資限售期股票需求的另一個原因。
三是普通投資者,指除特殊投資者和關聯投資者以外的投資方,不具有上述特殊身份或內部關聯關系。私募基金股權若作為普通投資者投資限售期股票收益權,在主體身份方面不存在其他限制。
三、交易模式方面分析:回購模式及買斷模式的合規性探討
(一)關于回購模式
最為通常的模式為附條件回購模式:股票收益權轉讓后,私募股權基金的退出渠道是融資方購回,通過股票收益權的轉讓和回購,實際達到的經濟效果是轉讓方從受讓方處獲得資金的融通,特殊之處即在于將上市公司股票的收益權作為一種財產性權利,從股票整體性權利中分離出來單獨交易,協議簽署后受讓方主要獲得兩大類請求權,第一類是向賣方請求在約定的時間內劃轉買方所應取得的股票收益的請求權,第二類是向賣方請求在約定的時間之內支付確定的回購對價的請求權,以上兩類請求權均不屬于法律所規定,而是通過合同來創設的法律關系,屬于一種新類型的證券交易法律關系。
(二)關于買斷模式
還有一種是買斷套現模式:通常是沒有資格成為戰略配售的股東,或者因不滿足條件等無法直接參與定向增發,但看好標的公司股票行情,選擇購買并承擔限售期內的所有盈虧,也可能是限售期股票的賣家急于賣出套現,限售股票持有人與私募股權基金簽訂協議之后,轉讓股票收益權給基金以獲取對價,并將標的股票質押給基金,待限售期結束之后直接完成股票過戶,私募股權基金的退出渠道是屆期辦理股票過戶登記,通過股票二級市場減持。買斷模式與回購模式最根本的區別是是否回購股票,買斷模式沒有附回購條款。
(三)兩種模式是否違反限售規定
收益權的具體交易模式不限于上述兩種,還存在以收益權為基礎的信托、ABS、質押融資等,那是進一步的金融衍生,與《資管新規》要求消除多層嵌套的理念不符,在此不作討論,無論哪種模式,核心的焦點是是否突破了監管機構的限售規定,即是否存在突破限制價格、限制轉讓和解禁期限的要求。由于股票收益權需依附于作為其基礎資產的股票,在內涵與價值上股票收益權與基礎資產存在重疊,因此,并不能完全排除轉讓收益權被認為變相轉讓限售期股票的可能性,通常的回購模式下由于屬于債權性質的轉讓相比而言風險較小,但買斷模式下由于可能被認定實為屬于基礎資產的轉讓,即被認定為限售期股票的轉讓而面臨更大的風險。
回購模式中,最大的問題是被認定為利用明股實債的方式規避私募基金禁止信貸的監管,因為回購模式被認為是“通過收益權轉讓就可以使私募基金從事的信貸類業務偽裝成投資交易業務,規避監管是收益權交易大量出現在資管行業當中的最直接原因。”
買斷模式中,限售期內限售股股票收益權轉讓因不涉及到限售股股票的過戶轉讓,尚未構成違反限售期內不得轉讓的情形,也未被認定為屬于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的證券“賣出”行為。但是否被認為是規避監管要求,在形式上未發生交割,但實質已經達到交割效果而被判定為規避了限售期的規制要求,仍待討論,相關案例很少,相對近似的案例有一例:海泰新光的大股東在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掛牌期間,為規避發行對象數量限制而將其定增所獲股票收益權(且不包括表決權、處置權)轉讓出去給員工以給予員工股份權益,其采用的方式類似于通過員工買斷,后來在海泰新光申請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并在科創板上市過程中,由于被認為該行為屬于存在股份代持,上交所要求對授予股份全部予以規范和還原。
總之,若是采用實質重于形式的原則進行判斷,買斷套現模式因并非借用限售期股票融資,而是實質上可能具有轉讓股票權利的意思,存在的風險較大,也需要關注避免海泰新光案例中被認定為存在股份代持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