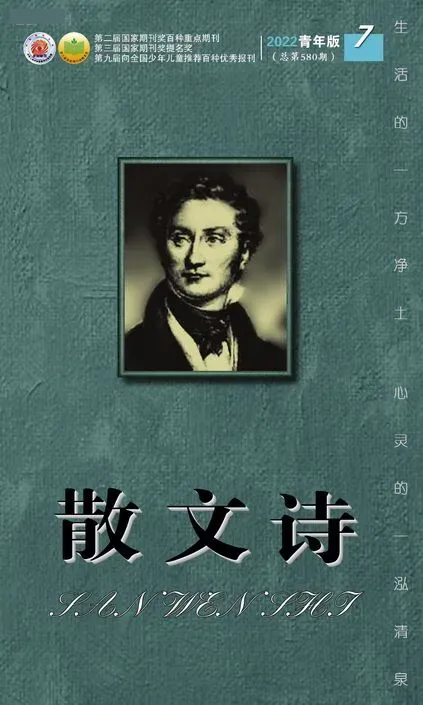鞏溝
淮源小月
薔薇苔
刺,是叢林法則中一項重要條款。
對于粗暴的入侵者,刺仗劍直擊,甚至脫離母體,折翅對抗。
肉中刺的痛感反應,便是讓野薔薇在鞏溝野性十足。以葳蕤之態搶占,或堅守地盤。
來回放牧,光禿禿的南山北壑,溪岸堤埂,總算有一簇簇保留下來的隱私。
薔薇的嫩苔,甘甜微澀。
三月,牧童們一定爭相去,抽茅芽,掐薔薇苔。
跟著牛羊去吃草,我長出了青色的胡須和鬢毛。
注定,我是長不出奶的。擠出的,也只是鞏溝的草木性格。
踩 青
踩青,就是把青草踩入泥田,備肥。
綠色,囤積成有機肥,足讓這個化工泛濫的時代羨慕與嫉妒。
一定是鞏溝的白茬田。
用水泡軟泥土的骨頭,在水田里聽任父親——一個鄉下人,一頭牛,一盤耙,耕耘。撫平坎坷。
春天,草長鶯飛。
野蒿,貓兒眼,禿妮子頭,癩蛤蟆棵……這些被牛嘴過濾的綠色,重新得到重用。
姐姐的鐮刀,閃爍著稚嫩的光芒。草,被姐塞進竹筐,一挑挑挪到水田里。一小撮、一小撮均勻鋪開。再一腳腳踩進泥里。
泥水濺過姐的褲管。頭發粘在姐的臉上。
姐的青春,在水田里,變綠,變黑,變肥。
姐彎腰,把自己插在腳印里,長成肥壯的秧苗。
姐只上過小學。踩青,是姐春天里的作業。
秋風從樹葉下穿過
夜,剖開一枚清露,容我躺下。在鞏溝支起紗帳,重溫母親懷里的暖。
滿天的星星,將童心喚回。從一數到十,再從十數到一。再也不能像兒時那樣,把星星數進夢里。
輾轉。
該有流螢,飛過了。該有蒲扇,搖起了。牛郎與織女的故事可以結束了。半導體的收音機可以關掉了。
不遠處,我恍惚聽到父親的鼾聲。
我聽到母親搖紡車的聲音。
我趕緊側耳屏息。
只有秋風從樹葉下穿過。
忽地,一顆星星落下。接著,像流星雨。天空只剩下母親離開時的那雙眼睛。凹陷的眼眶,瘦,隱忍著痛。
深邃的,絕望的,留戀的眼神。
圖中的數目代表了在|M|次采樣中對應緩沖器的調整次數.我們在算法中去掉那些調整次數不大于1的以及與重要節點沒有相連的緩沖器.重要節點定義為調整次數大于一定數量的節點,在實驗中我們設置為5,總共采樣次數為10000.例如,在圖5中,我們去掉那些虛線描述的節點.這種過濾不僅僅可以加速算法,也通過圖的分解降低了問題的空間.
秋,露好大,濕了我的枕。
我是父親的一棵麥苗
在鄉下,父親一直像是被罰抄作業的學生,反復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寫那些相同的漢字。
漸漸地,父親的犁鏵越來越淺,筆畫越來越粗。勞動號子的高聲部上不去了,父親的牧鞭再也抖不出閃電來。
終于,父親翻不過那道田埂。他把自己的汗珠播種進土壤。
鄉村,十月懷胎。地里的麥子,開始著手替父親,揚眉吐氣。
麥葉,似年輕時濃密的發絲,凌亂地貼在父親的額頭。
綠,是父親常常在我們面前展示的胸肌。
父親喜歡枕雪而眠,父親說,父親二字,必以男人作注腳。
不理會那些風。或言語。
一頁頁撕去日歷,似在扯拽著父親的胡須。我是父親的一棵麥苗,坐在白雪的痛上,解鎖春的暗語。
稻草人
莊西邊,后沖田,上面的一口塘,叫后塘。緊挨著塘的幾塊田,是我們各家的秧底。
年底犁出,炕透,追肥。
三月,大把兒們借著水勢,套牛用木耙盤軟它。
秧底,有秧苗的底氣。雜交水稻未出世前,稻種的用稻量好大。在水缸里浸泡三至五天,稻芽初露,直接均撒入平整的泥田。
看秧雞。替每一個家守住豐產的第一關。
父親會把看護任務交給稻草人。
父親以我的模樣,扎的。把它插在田頭。
每天上學,放學,我都要去給它輸點人的靈氣。
我知道,父親是用稻草人接替我鄉下的現世身,好讓我遠走高飛。
淮草坡
那些草,是淮河給的名字。那道坡,是父親的母親給的名字。我從我的母親那里知道了,那草叫淮草,那坡叫淮草坡。
淮草坡長滿淮草。淮草叢里,有綠蟬,有山楂果,鵪鶉蛋,也有我最害怕的馬蜂窩與蛇。
淮草長滿我的童年。
淮草坡的淮草,葉軟,稈硬。是鄉下草房子的上等材料。是鞏溝當年唯一上市的經濟作用。
有鞏溝人的品性。
父親,曾帶著它,走南闖北。
直至今天,每次我摸到自己的脊骨時,仍先想起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