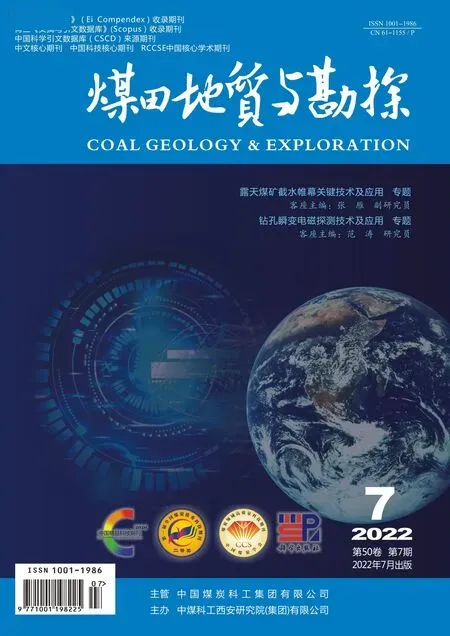基于植被區劃和生態敏感性的中國煤礦生態恢復策略
周宏軒,王昭清,濮宏桐,陶貴鑫,孫 婧
(中國礦業大學 建筑與設計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
我國能源結構特征為“貧油、少氣、富煤”;煤炭一直以來都是我國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和重要驅動力,占我國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比例超過55%[1]。我國能源結構特點決定社會與經濟發展依賴煤炭的格局難以在短時間內改變[2]。因此,我國經濟與科技的快速發展仍將以煤炭作為重要的能源驅動力,對煤炭資源的科學開發與利用依舊是未來幾十年的重點。
煤礦區域屬于一類小型的“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3],由社會、經濟和自然3 個子系統耦合而成。當前生產煤礦的經濟與社會子系統不斷趨于完善與和諧,但自然子系統卻因長期煤炭開采活動而深度受損;在資源枯竭及政策影響下,我國多處煤礦相繼關閉,也伴隨著社會退化、經濟衰退和自然受損等現象。無論是開采還是關停,煤礦均在不同程度上造成當地自然生態環境損傷,在“水(水文、水質)、土(土壤、土地)、氣(大氣環境)、生(生物組成與多樣性)、礦(礦產資源與生物地化循環)”等多方面均有體現,煤礦區域生態環境受損增加生態風險,影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甚至威脅“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體,不利于我國全方位可持續發展和生態文明進程的推進[4]。
因此,有必要進行煤礦的生態恢復研究與實踐,以便維持或重構和諧的生態系統。基礎研究方面,當前研究大多關注單一煤礦或單一礦區內的幾個煤礦生態修復策略,主要集中在設計層面的景觀營造[5-6]與景觀修復[7],并賦予景觀相應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8];也有通過土地復墾實現農業開發[9],或在管理層面上提供生態修復資金保障的建議[10],但在較大空間尺度上的煤礦生態恢復研究比較罕見[4]。目前,僅有對黃河流域提出的生態恢復技術[11]和相應的宏觀策略[12],以及對我國西部地區生態恢復關鍵技術與發展方向的預判[13]。實踐方面,我國煤礦區生態恢復研究與工程實踐已有多年歷史[14],并在全國范圍內廣泛推廣,取得良好的進展,包括生物多樣性[15-16]、土壤理化特性[17]以及地表景觀重建等方面[18],但我國早期煤礦生態恢復實踐大多數受企業開采范圍以及地域行政邊界所限,往往局限在某一處或某幾處礦區內進行,屬于局部層面的工程實踐,較少涉及區域甚至國家尺度的協調統一,缺少相關總體規劃與策略的制定。
在全國生態文明建設進程中,國土空間規劃以生態文明建設為核心價值觀,要求對全國范圍進行統籌,制定更高層級的煤礦區域生態恢復規劃與策略[19],以此促進流域和全國尺度上的生態恢復,并積極發揮生態系統服務的功能與價值。2020 年,自然資源部頒發了《全國重要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重大工程總體規劃(2021-2035 年)》,標志著全國范圍內的生態恢復已經成為國家戰略。面對國家戰略、國土空間規劃的重大需求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的發展趨勢[20],我國煤礦區域迫切需要在國家尺度的宏觀層面上制定相應的生態恢復規劃與策略,對煤礦區域的生態恢復進行總體把控。但我國幅員遼闊,煤礦分布較為分散,覆蓋全國多個省/市,水文地質環境復雜[21],開采方式及其造成生態環境受損的結果差異較大[22],導致全國范圍的煤礦生態恢復規劃與策略的制定極具挑戰性。因此,全國范圍內煤礦區域生態恢復規劃的研究需要由淺入深,在高度異質性的破損生態空間中,提取適用的參數,用以衡量生態恢復的緊迫性及重要性,據此制定相應的生態恢復秩序策略。
針對上述問題,以我國2020 年重點煤炭規劃區現存煤礦為研究對象;以自然恢復為主,人工為輔,從充分發揮自然恢復能力的理念出發,通過疊加植被區劃來明確生態恢復的潛在植被類型;綜合研究對象的多種生態敏感性并進行歸一化計算,以表征生態恢復的緊迫性;探索煤礦生態恢復獲益人口以確定生態恢復的重要性;使用聚類分析找出煤礦生態恢復最關鍵區域,為制定科學合理的煤礦生態恢復規劃提供依據。
1 研究區域與方法
1.1 研究區域
我國煤礦主要分布于山西、陜西、河北、內蒙古、河南北部、山東西部、云南、貴州和四川等地區,少部分分布在新疆、甘肅、青海、寧夏、黑龍江、吉林、遼寧等地區。筆者通過高德地圖API 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獲取全國范圍內2020 年煤礦的POI 數據(Point of Interest),其中包含煤礦的名稱和坐標等信息。在ArcGIS 平臺中將上述數據與全國重點煤炭規劃區進行疊加分析,得到全國重點煤炭規劃區內煤礦的空間分布情況。如圖1 所示,我國重點煤炭規劃區內共有煤礦2 207 處。山西、陜西、內蒙古等地是現存煤礦的主要集中地區;云南、貴州和四川也是我國重要煤炭規劃區的聚集地;此外,安徽北部、河南東部、山東西南部、河北南部和東部、東北部部分地區以及新疆部分地區也有較多的煤礦分布。

圖1 我國重點煤炭規劃區煤礦分布Fig.1 Distribution of coal mines in the national key coal planning area
1.2 歸一化綜合生態敏感性(NIES)數值計算方法
煤礦區域礦山廢棄物中的酸堿、礦物質和重金屬成分通過雨水的滲透、徑流等方式進入地層,導致周圍區域出現土壤酸化、侵蝕及鹽漬化現象;而礦山的疏排水和突水及因露天采礦對土壤的破壞則會引起礦區周邊區域出現土壤流失及沙漠化問題[23]。針對煤礦區域的生態敏感性評價,選擇沙漠化敏感性、石漠化敏感性、鹽漬化敏感性、凍融侵蝕敏感性、酸雨敏感性、土壤侵蝕敏感性共6 個敏感因子作為基礎條件開展研究。敏感性數據來源于中國生態系統評估與生態安全數據庫[24],是按敏感性等級分類的無量綱柵格數據,等級1、3、5、7、9 分別對應不敏感、輕度敏感、中度敏感、高度敏感和極敏感,數據空間分辨率為1 km×1 km。
不同生態敏感性在不同地區影響程度及主導性具有差異,在對其進行綜合空間疊加時,不同地區的上述各種敏感性權重難以通過專家打分的層次分析法確定,如凍融敏感性主要在我國北部及西藏等地區起主導作用。因此,為保留不同生態敏感性在不同地區原有的離散程度,將各個區域的6 種生態敏感性(凍融侵蝕、沙漠化、鹽漬化、石漠化、土壤侵蝕、酸雨)進行空間疊加,得到綜合生態敏感性值,隨后采用極值處理法(離差標準化)[25],對原始數據進行線性變換,使其落入[0,1]范圍,以便進行直觀比較,綜合生態敏感性值線性變換計算方法如下:

式中:x為綜合生態敏感性值;k為6 種生態敏感性指標;Ck為第k個指標的生態敏感性等級值;xmin和xmax分別為所有綜合生態敏感性序列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最后按自然斷點法對NIES 進行分級并展示。
1.3 空間自相關分析方法
通過空間自相關分析方法評價不同NIES 煤礦的空間自相關性及聚集模式[26-27],空間自相關分析方法選擇莫蘭指數,分為全局莫蘭指數(Global Moran’s I,GMI)和局部莫蘭指數(Local Moran’s I,LMI)。其中,GMI 用于評價不同NIES 的煤礦在空間上是否存在自相關性;而LMI 則用于分析空間位置上某一煤礦與鄰近煤礦的NIES 關系,計算方法如下:

式中:S為標準差;n為全國重點煤炭規劃區中煤礦POI 點總個數;NIESi和NIESj分別為第i個煤礦POI點和第j個煤礦POI 點的歸一化綜合生態敏感性值;為n個煤礦POI 點的歸一化綜合生態敏感性平均值;Wij為煤礦i和j之間的空間權重矩陣,空間權重矩陣根據空間相鄰情況將空間單元連接的定義為1,把不連接的定義為0。
S和的計算方法如下:

GMI 的取值為(-1,1),當GMI 為正值時,表明不同NIES 的煤礦間存在顯著的正自相關;當GMI 為負值時,為負相關;當GMI 為0 時,無空間自相關性。另外,GMI 的置信區間取決于P值(此空間模式為隨機產生的概率)和z-score(反映數據離散程度的標準差的倍數),二者是相互關聯的,故還需對GMI 的P值和z-score 進行顯著性檢驗。當P<0.05 時,置信區間為95%,空間模式存在自相關(聚集或離散)的概率是95%;當P≥0.05 時,空間模式有95%的概率為隨機分布模式;當P<0.01 時,概率更高,結果更加可信,見表1。

表1 GMI 不同置信區間的臨界P 值和z-scoreTable 1 Critical P-values and z-score of different confidence intervals of GMI
LMI 中,將某煤礦NIES 大于NIES 平均值的表示為高值,反之則為低值。NIES 高值煤礦的鄰接煤礦為高NIES,則為高-高聚集;其鄰接煤礦為低NIES,則為高-低聚集;同理,NIES 低值煤礦的鄰接煤礦為高NIES,則為低-高聚集;其鄰接煤礦為低NIES,則為低-低聚集。基于莫蘭指數分析,聚集模式可分為5 類:不顯著表示無自相關性,為隨機分布;高-高聚集表示NIES 高值的煤礦被高值包圍;低-低聚集表示低值包圍低值;高-低聚集表示高值被低值包圍;低-高聚集表示低值被高值包圍。
1.4 聚類分析
聚類分析是一種常用的數理統計學方法,依據數據之間的差異程度將數據分為不同的類或簇[28]。以各個煤礦的NIES 和生態恢復獲益人口為屬性,在SPSS 17.0 軟件中采用K 均值聚類分析,將煤礦分為不同類別,同一類別的煤礦具有較為相似的屬性,而不同類別的煤礦之間屬性差異較大。
2 煤礦區域生態恢復綜合分析
2.1 潛在植被類型
依照生態學原理,本地植被對當地氣候和環境具有高度適應性,是當地生態恢復的重要物種。但我國地域遼闊,不同地區的土壤性質、光照強度和氣溫、降水量等氣候條件都存在較大差異[29],植被組成和優勢物種差別較大;但相同或相近地域植被群落的演替進程、階段性和最終物種組成較為類似。由于國土空間規劃對煤礦區域的未來用地屬性仍不明確,本文以“借自然之力恢復自然”的理念為指導,以我國植被區劃作為當地煤礦生態恢復的潛在植被類型,即認為當地煤礦生態恢復過程將朝向潛在植被類型發展。
根據全國重點煤炭規劃區內的煤礦數據和中國植被區劃數據[30](來源于中國陸地生態系統數據庫)疊加的結果,得到重點煤炭規劃區煤礦生態恢復的潛在植被類型(圖2)。我國重點煤炭規劃區煤礦主要分布在暖溫帶落葉闊葉林區域、溫帶草原區域和亞熱帶常綠闊葉林區域;此外,在寒溫帶針葉林區域、青藏高原高寒植被區域、溫帶荒漠區域和溫帶針葉落葉闊葉混交林區域也有煤礦分布。總體來說,在沒有人工干預和其他因素擾動的情況下,各個區域將會演替為適應當地氣候與環境的植被類型,這是順應自然的結果,但同時也應綜合考慮國土空間規劃及區域的自身發展條件。

圖2 基于植被區劃的煤礦生態恢復潛在植被類型Fig.2 Potential vegetation types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coal mines based on the vegetation zoning
2.2 煤礦的生態敏感性
按照敏感區劃分,我國可分為東北水土流失區、黃淮海平原鹽漬化區、東南酸雨水土流失區、內蒙古與新疆沙漠化鹽漬化區、黃土高原水土流失區、云貴高原酸雨水土流失區、青藏高原鹽漬化區共7 處敏感區[31]。將不同生態敏感性情況在ArcGIS 中通過式(1)、式(2)進行計算,得到全國NIES 空間分布情況,并將其與煤礦POI 數據相疊加,獲取煤礦的NIES(圖3)。

圖3 不同歸一化綜合生態敏感性區域煤礦分布Fig.3 Distribution of coal mines in different normalized integrated ecologically sensitive areas
多處煤礦分布在極高NIES 區域中,其中較為密集的共3 個區域:一是位于河北東部、南部以及山東北部,共81 座煤礦;二是位于西南部的云南和貴州交界處,共48 座煤礦;三是位于內蒙古與遼寧交界處,共25 座煤礦。此外,還有218 座煤礦較為零散地分布于高NIES 區域,其生態恢復同樣較為緊迫。
以NIES 為空間自相關分析依據,GMI 分析結果見表2,結果表明:由于P<0.01,不同NIES 煤礦分布表現為空間自相關,即聚集或離散關系;且z-score>2.58,表明煤礦呈聚集分布;GMI=0.250 703,表明全國重點煤炭規劃區煤礦顯著正自相關。

表2 GMI 分析結果Table 2 GMI analysis results
不同NIES 煤礦聚集模式如圖4 所示,灰色的點表示分布聚集模式不顯著,說明這類煤礦為隨機分布,主要分布在新疆西北部、山西北部、內蒙古、黑龍江東部及遼寧中部,少部分分布在陜西南部、四川西南部。高-高聚集主要分布在河北、內蒙古、陜西、山東、安徽及云南、貴州、四川3 省交界處;低-低聚集主要分布在山西、陜西和河南,少量還分布在甘肅、青海和新疆地區。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可采用相似方法進行生態恢復,但高-高聚集相比于低-低聚集更亟需生態恢復。

圖4 LMI 分析圖Fig.4 LMI analysis
如圖4 所示,高-低聚集和低-高聚集的點相對較少,前者主要分布于山西、河南和黑龍江;后者僅分布在山東和遼寧。針對高-低聚集和低-高聚集,可以采用差異化的生態恢復方式協同恢復,即高NIES 區域優先進行恢復,并需人工介入以輔助自然恢復;同時,在區域角度上,通過演替進程較快的區域帶動演替進程較慢的地區,從而達到協同恢復的效果。
2.3 基于緩沖區分析的煤礦生態恢復獲益人口
煤礦生態恢復將直接提升煤礦周邊環境質量,包括大氣、水和土壤環境改善;當地居民將因煤礦生態恢復在多方面獲益,如良好的人居環境和景觀休閑空間等。本文以5 km(居民騎行可接受的最遠距離)作為煤礦生態恢復改善人居環境質量的輻射范圍,對煤礦進行緩沖區分析。如圖5 所示,獲益人口在20 萬以上的煤礦數量為115 處,多分布在山西以及山西、河北與河南3 省交界處,在河北東部地區也有分布;少數分布在內蒙古、新疆、黑龍江、吉林、遼寧、陜西、甘肅、云南、貴州地區。

圖5 煤礦生態恢復后獲益人口數量級Fig.5 Population level benefiting from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coal mines
獲益人口介于15 萬~20 萬的煤礦共117 處,主要分布情況與獲益人口20 萬以上的類別相似,少數分布在河北東部、山東、安徽、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新疆、寧夏、云南、貴州部分地區;獲益人口數介于5 萬~15 萬的煤礦共755 處,主要分布在山西、河北東部、冀魯豫交界處,少數分布于新疆、甘肅、內蒙古、陜西、黑龍江、吉林、遼寧、云南、貴州、四川地區;獲益人數在5 萬以下的煤礦數量最多,共計1 220 處,主要分布在山西、陜西、內蒙古、寧夏、河北東部、河南西北部及云南、貴州、四川交界處,少數分布在新疆、青海、甘肅、河北、山東、安徽、遼寧。上述結果表明,我國煤礦數量多,生態恢復將為大量居民提供優良的自然環境本底以及良好的公共空間。因此,有針對性地制定生態恢復方案,停止煤礦生產對周邊生態環境的破壞,將逐步改善當地人居環境質量,持續產生社會、經濟以及生態效益。
2.4 基于聚類分析的煤礦生態恢復優先級
煤礦生態恢復獲益人口是煤礦生態恢復規劃的重要依據,本文將煤礦NIES 與獲益人口數量進行聚類分析,如圖6 所示。在劃分的4 個類別中,第1、第3和第4 類的NIES 平均值相差較小,但在人口數量上具有較大差異,因此,聚類結果中煤礦生態恢復獲益人口是主導因素,而煤礦的NIES 為次要因素。第2 類較特殊,NIES 較高,獲益人口數量較多,此類煤礦主要分布在貴州六盤水市(5 處)與河南洛陽市(1 處),其中六盤水市屬于典型的山地喀斯特地貌類型,溝壑縱橫,酸雨和石漠化的生態敏感性較高,生態環境較為惡劣[32],因此,此處煤礦應當優先進行恢復。

圖6 煤礦歸一化綜合生態敏感性和煤礦影響人口數量的聚類分析Fig.6 Cluster analysis between normalized integrated ecological sensitivity and population of coal mines
3 我國煤礦區域生態恢復原則
全國煤礦的生態恢復應整體性、全局性和系統性地考慮[33]。從植被區劃、生態敏感性、煤礦恢復獲益人口和綜合分析的角度,筆者認為,煤礦生態恢復原則如下:第一,貫徹“借自然之力恢復自然”理念[34],采用本地鄉土物種,遵循生態恢復學原理;第二,生態敏感性高的煤礦具有較高的生態恢復緊迫性;第三,以煤礦之間的空間聚集模式,制定區域生態恢復策略;第四,生態恢復應當盡量先恢復獲益人口較多的煤礦;第五,需要充分平衡西部生態涵養以及東部經濟發展的關系;并且需要在多個省份之間進行權衡,符合國土空間總體規劃的需求。
4 煤礦區域生態恢復策略
第一,西南地區煤礦主要集中在云南、貴州和四川交界處,石漠化和酸雨侵蝕是當地高生態敏感性的主要原因。植被區劃上,該地區主要屬于常綠闊葉林區域,僅云南少數煤礦區屬于熱帶雨林區域,因此,常綠闊葉林和熱帶雨林應成為其潛在植被恢復類型。煤礦造成該地區生態系統極度退化,故生態恢復需選擇耐酸、耐瘠等環境適應性強的植物,如蒺藜、黃蒿、刺莧。另外,由于煤矸石等因素使土壤酸度增強,污染使植被生態恢復更加困難,除選擇耐性植物外,還可通過優先種植次生群落的先鋒樹種,如光皮樺、楊樹、馬桑、構樹、楤木,以增加恢復煤礦的生物多樣性。該區域大部分煤礦NIES 屬于高-高聚集模式,NIES 屬于極高和高度敏感,且其生態修復獲益人口總數較高,應優先進行生態恢復并采用相似的方法和策略,即主要關注地表土壤及地下水系。在地表土壤層面,主要采用農業生態修復模式以改善生態環境;以煤礦為中心,開展人工生態恢復,并且距離中心越遠,人工干預程度越低[9];依據采煤塌陷地表形態,因地制宜地進行垂直分帶治理,采用復合型立體生態農業發展模式,廣泛應用高效集水節水技術[35]。在地表以下層面,需要針對農業設施保水問題在犁底層以下采用土工膜,并在地表下和犁底層以上打樁夯實防止水分側滲[36]。其中,貴州六盤水市煤礦生態恢復獲益人口數量較多,且煤礦聚集程度高,應優先恢復,并需要高強度的人工介入,如在合適時間和空間引入先鋒物種、改善土壤理化條件并加強生態恢復區的空間格局管理,為不同演替階段物種入侵與分布提供必要條件。少數煤礦NIES 屬于低-高聚集模式的區域,NIES 屬于中度敏感并低于全國NIES 平均值;幾處煤礦屬于隨機分布,NIES 屬于中度敏感,此類煤礦的生態恢復獲益人口數量較少,可以通過少量人工干預控制生態風險,再通過自然恢復逐步向潛在植被類型演替。
第二,東北地區和內蒙古東北部的煤礦主要集中在黑龍江、吉林、遼寧3 省與內蒙古東北部交界處,黑龍江東部以及內蒙古北部。上述3 個區域生態敏感性來源在空間上具有較大差異,黑龍江、吉林、遼寧與內蒙古東北部交界處主要是沙漠化和酸雨侵蝕;黑龍江東部主要是沙漠化、土壤侵蝕和鹽漬化;內蒙古北部主要是凍融和沙漠化。黑龍江、吉林、遼寧與內蒙古東北部交界處屬于干旱與半干旱地區過渡帶,該地區在植被區劃上屬于暖溫帶落葉闊葉林區域,可先種植當地草本植物減輕沙化和生態退化現象,以落葉闊葉樹木組成的群落作為潛在恢復植被類型。針對露天開采引起的地表破壞主要采用水土流失防治、土地復墾以及植被恢復的對策。其中,NIES 屬于高-高聚集模式的煤礦主要分布在遼寧西部與內蒙古交界,生態問題較為類似,可采用相似的方法進行生態恢復,該地區僅有少數煤礦生態恢復獲益人口在20 萬以上,應作為生態恢復的重點,具有高度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并且可以作為區域的示范工程。針對因露天開采形成的大量邊坡需要人工介入,穩固邊坡以降低地質災害風險[37]。對于地下開采造成的沉陷區應采用有效復墾方案,推動農業種植結構和區域產業結構的轉型與升級,促進農、林和牧業產業化發展,形成集中連片恢復模式,以減輕景觀破碎化程度[38]。對于低-高聚集模式和隨機分布的煤礦,其NIES 值較低,但煤礦生態恢復的獲益人口數量具有差異,獲益人口多的煤礦應采用少量人工介入引導恢復,而獲益人口數量較少的煤礦則建議通過自然生態恢復向潛在植被類型演替。在黑龍江東部地區,植被區劃屬于溫帶針葉落葉闊葉混交林區域;在生態敏感性方面雞西市與鶴崗市屬于隨機分布類型,NIES 值較低,僅受沙漠化和鹽漬化影響;雙鴨山市煤礦則屬于高-低聚集模式,NIES 值較高,面臨土壤侵蝕、沙漠化和鹽漬化的脅迫。雞西市與鶴崗市的煤礦可以通過種植耐鹽、耐旱和耐寒的植被進行生態恢復,以改善土壤條件[39],并向潛在植被類型轉變;雙鴨山市需要更多的人工介入,如根據生態恢復學原理增加植被覆蓋度對抗雨水沖刷和冰雪融水對土壤的侵蝕,或根據煤礦塌陷形態對地形進行整改,通過建設梯田減緩水土流失并合理安排農林牧比例。內蒙古北部在植被區劃上屬寒溫帶針葉植被區域,但其煤礦區域被極度破壞,且當地受沙漠化和鹽漬化影響較多,建議種植耐鹽和耐寒的草本植被,并且逐步向針葉樹木群落過渡;此外,該地區煤礦聚集模式大多為隨機分布,其生態恢復策略建議采用少量人工介入引導,再充分進行自然生態恢復。
第三,河北、山東和安徽煤礦所在區域以沙漠敏感性為主,其中,河北和山東的NIES 值較高,而安徽較低。在植被區劃上,上述3 個省份均屬于暖溫帶落葉闊葉林區,可以作為潛在恢復植被類型。在空間關系上,分布在這3 省的煤礦大多為高-高聚集模式,可采用相似的生態恢復方法。此外,雖然這些煤礦生態恢復獲益人口數量不等,但因煤礦較為密集,故均應有一定優先級。其中,河北省屬于京津冀協同發展區域,應先行恢復,且該區域屬于中高潛水位地區,地下開采造成較大的塌陷面積和較深的積水,因此,其生態恢復需綜合考慮沙漠化及塌陷區積水的影響。生態恢復方式可采用挖深墊淺的復墾方式,進行水產養殖與種植農業相結合的生態恢復策略[40];也可將食物鏈作為紐帶,構建小型生態系統,實現“桑基魚塘”的生態智慧模式;對于地質條件較好或者已經穩定的沉陷區域,通過填充煤矸石、表面覆土措施,使其達到可以種植以及建設的程度。此外,在山東省存在部分隨機分布和低-高聚集模式的煤礦,且獲益人口總數較多,雖然NIES 值較低,但是需要人工介入起引導作用,使煤礦向進展演替方向發展。
第四,在黃河中游流域,主要以陜西、山西與河南為代表。其中,陜西南部、山西與河南北部大部分煤礦處于生態敏感性較低的區域,主要受沙漠化影響。在植被區劃上,上述地區屬于暖溫帶落葉闊葉林區域,可作為生態恢復的潛在植被類型。在空間關系上,上述地區煤礦大多屬于低-低聚集模式,少數屬于高-低聚集模式和隨機分布模式。此外,該區域生態恢復獲益人口總數較多,屬于生態恢復的重點區域。因該區域生態敏感性較低,可以通過輕度人工介入將煤礦生態恢復引導至進展演替。依托黃河流域的豐富資源,可使用黃河泥沙對塌陷區進行填充與復墾[41],也可開發新技術通過煤炭開采治理脆弱的生態環境[11]。在陜西北部和內蒙古交界處的煤礦存在高-高聚集模式,主要受凍融侵蝕、沙漠化和鹽漬化影響,可采用類似黑龍江東部的策略。
第五,內蒙古西部、寧夏、青海東北部、甘肅、新疆北部地區煤礦NIES 基本較低,甘肅、內蒙古西部、寧夏較少煤礦為高NIES,其敏感性以凍融侵蝕、沙漠化、鹽漬化為主導。此區域地廣人稀,在植被恢復方面,可采用節省人力、物力的自然修復方式;根據我國植被區劃,新疆北部、內蒙古西部、寧夏以溫帶草原植被類型作為潛在恢復目標,新疆西北部、甘肅西部、青海北部恢復為溫帶荒漠植被,青海東北部植被恢復目標為青藏高原高寒植被。內蒙古西部煤礦分布較集中,NIES 空間聚集除隨機模式外多為高-高聚集模式,內蒙古地區土地沙漠化,可對高-高聚集模式煤礦采用“灌木和種草”植被重建及生物笆鋪設邊坡面、設置網格沙障等人工修復方式,以達到保持水土的生態恢復效果。寧夏、青海、甘肅、新疆地區煤礦分布較分散,NIES 空間聚集模式除隨機模式外均為低-低聚集模式,其生態恢復應以自然修復為主,輔以相似的人工修復策略,基于該地區干旱少雨的特點,可采用滴灌、微噴灌等微灌技術滿足煤礦邊坡面植被的需水要求;植被恢復樹種應選擇耐旱、耐瘠、根系發達的樹種,青海煤礦植被人工恢復可選擇星星草、垂穗披堿草、冷地早熟禾作為典型植被種類。
5 結 論
a.我國具有幅員遼闊、植被分布地帶性明顯、生態環境差異巨大、人口分布不均的特點。煤炭開采在不同區域造成不同程度的生態環境破壞,須對煤礦地區進行全面、系統、有序、有效的生態恢復。
b.將6 種生態敏感性的數值進行歸一化處理,得到歸一化綜合生態敏感性指標(NIES),作為衡量我國生態敏感性的指標。根據NIES 值,我國大部分煤礦屬于聚集分布,僅有少量煤礦屬于隨機分布,對于聚集分布的煤礦需采用系統與協同的生態恢復方式;隨機分布的煤礦可單獨制定生態恢復方案。
c.我國煤礦生態恢復策略制定需要尊重生態恢復學原理,使煤礦生態恢復向潛在植被類型的方向發展。同時也需要根據煤礦群體之間的空間關系、生態敏感程度以及受益人口數量制定相應的生態恢復策略。在策略制定的過程中,難以通過植被區劃和生態敏感程度直接劃分區域,應根據煤礦聚集和分散劃分不同區域分別進行煤礦生態恢復策略制定,以區分并滿足生態恢復緊迫性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