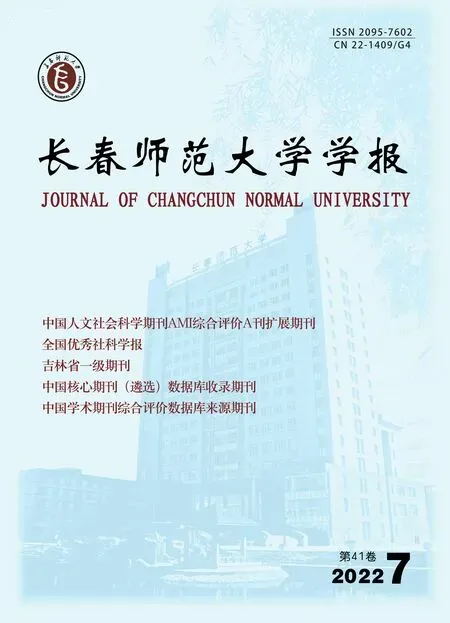《禮拜五或太平洋上的靈薄獄》的創作主體和接受主體研究
李 曼
(安徽新華學院 外國語學院,安徽 合肥 230088)
1966年,42歲的法國作家米歇爾·圖爾尼埃(Michel Tournier)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說《禮拜五或太平洋上的靈薄獄》(VendrediouleslimbesduPacifique,以下簡稱《禮拜五》),小說于次年出版后一舉獲得法蘭西學院小說大獎。《禮拜五》是對《魯濱孫漂流記》一書的改寫,前者是20世紀產生的作品,后者則是18世紀產生的作品。不同的時代背景、社會文化和創作主體,使得相同的人物有了不同的關系,相似的情節有了不同的結局,類似的寓言有了不同的寓意,也使得接受主體享受到更多元的文學趣味。而不同的接受主體在欣賞同一部著作時,得到的享受和收獲也有所不同。可見,對文學作品的創作主體和接受主體進行全面探究,不僅能夠幫助我們更深入地解讀一部優秀作品,還能給作品注入新的生命力。
一、艾氏文學四要素

圖1 艾氏文學四要素坐標
美國文論家艾布拉姆斯教授(Meyer Howard Abrams)在《鏡與燈:浪漫主義理論與批評傳統》中認為,任何藝術品都會涉及四個要素。第一要素是作品,即藝術產品本身;第二要素是生產者,即藝術家;第三要素由人物、行動、思想和感情、物質和事件或者生命感覺的本質構成,即世界;第四要素是欣賞者,即讀者[1]4。艾氏將“作品”置于“世界”“藝術家”和“欣賞者”之間,并建立了如下模型安排這四個坐標(圖1)。他同時指出,這四個要素的坐標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所處理論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含義[1]5。
我們試圖通過對“生產者”(創作主體)和“讀者”(接受主體)的研究,深層次解析“作品”和“作品里的世界”,進而反思“現實世界”。
創作主體是文學批評和研究中最難以捉摸的因素,因為任何人的意識活動都是比較復雜的,一部作品所呈現的可能僅僅是作者在某個特定時期的一小部分意識。但離開創作主體研究作品往往是片面的,因為創作主體有時會自覺不自覺地呈現在其敘事文本之中,如敘事方式、角度以及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都是創作主體精心安排的。接受主體是所有讀者,一部文學作品的歷史生命如果沒有接受主體的參與,那么這個作品就是沒有生命的。但接受主體可能處于不同的時代,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他們可以更自由地賦予文本其它意義,從簡單的接受到理性的批評,從認識的審美標準到理性的生產轉換,他們絕不僅僅是被教化的對象。作品是接受主體了解創作主體和世界的一扇窗,對創作主體和接受主體的把握有利于更好地了解作品的現實意義。
二、創作主體與《禮拜五》
米歇爾·圖爾尼埃是20世紀文學流派新寓言派的代表,他以小說家、哲人作家、教育家等多重身份屹立于世界文壇。其作品多以人們熟悉的故事為基礎,加入自己的哲學思想進行重新詮釋。《禮拜五》雖是對《魯濱孫漂流記》的改寫,但圖爾尼埃沒有像笛福那樣在作品中頌揚西方文明,提倡改造自然。他筆下的魯濱孫沒有沉醉于自己在荒島上建立的秩序及收獲的物質成果,而是不斷地進行內心探尋和反思,最終順從本心回歸自然。圖爾尼埃為何會有這樣的思路?我們可以從他的個人經歷及作品創作背景兩方面來理解。
(一)創作主體的重要經歷
1924年,圖爾尼埃生于法國巴黎第九區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其父母都曾在索邦大學學習德語,因此他在成長過程中經常接觸到德國文化。圖爾尼埃的童年并沒有因為有兩個高知父母而變得更幸福,相反,他在很小的時候就嘗盡痛苦和孤獨的滋味。在自傳體散文集《圣靈之風》中,他自述是一個極度敏感且體弱多病的孩子,4歲時受到過極可怕的侵害——被兩名突然闖入其房間的醫生裝扮的陌生人用夾鉗夾掉扁桃體。這件事給他幼小的心靈造成了極大傷害,導致他一直無法完全信任別人,哪怕是最親密的人[2]17-18。
圖爾尼埃從小就不適應巴黎的氣候,他討厭自己的故鄉巴黎。正如他自己所述:“當你出生在第九區的勝利大街,你蹣跚學步的地方是布滿恐怖時期(指1792—1794年的恐怖統治時期——筆者注)受害者骨灰的路易十五廣場(指協和廣場),你不會想歌唱這里,只想嘔吐。”[2]211931年,7歲的圖爾尼埃被父母送到瑞士格施塔德的一個兒童膳宿公寓(主要面向有錢人家體弱多病的兒童)。圖爾尼埃對那里控制飲水的做法非常不滿,他整個童年時期都被口渴折磨。這個膳宿公寓的每個房間住兩個孩子,一般會安排一個年長的和一個年幼的孩子同住,以期年幼的孩子可以得到保護。和圖爾尼埃同住的是一個11歲的西班牙男孩,這個本該保護圖爾尼埃的男孩卻成了他的噩夢。圖爾尼埃在《圣靈之風》中寫道:“他的保護從第一天起就帶有專橫的奴役性質,他常用一條小細繩來折磨我。我很小就知道這個看起來無害的玩意能夠給兒童虐待狂提供多少種折磨手段。”[2]24年少時痛苦的經歷讓圖爾尼埃對整個社會心懷不解甚至怨恨,但他并沒有在痛苦中沉淪,而是在孤獨中專注思考并深深愛上了哲學。因此對圖爾尼埃而言,哲學是愛好,亦是治愈年少傷痛的良藥。
圖爾尼埃曾在索邦大學攻讀哲學并于1945年畢業,之后選擇留學德國繼續學習哲學。他最初的志愿是做一名哲學教師,但因在哲學教師資格會考中失利,圖爾尼埃轉入翻譯、媒體及出版領域工作。他曾說過自己的文學志向是從1949年7月開始的,因為那一天被告知自己并沒有出現在教師資格會考通過名單中。實際上,十多年之后圖爾尼埃才真正投入寫作,并以文學作家身份被大家熟知。自1967年出版第一部小說《禮拜五》之后,圖爾尼埃在文學道路上越走越遠,先后斬獲法蘭西學院小說大獎(1967)、龔古爾文學獎(1970)、歌德獎章(1993)、厄爾巴島國際文學獎(1985)、卡佛文學獎(1991)、地中海文學獎(1992)、馬拉帕蒂國際文學獎(1993)等諸多獎項,多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并于1972年榮膺法國龔古爾文學院院士。2016年,圖爾尼埃在家中去世,時任法國總統奧朗德發表致哀聲明,盛贊他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偉大作家。龔古爾獎評委會主席貝爾納·皮沃在他的社交網站上寫下這樣一句話:明天開始,當人問我“誰是在世的最偉大的法國作家?”我再也不能回答“米歇爾·圖爾尼埃”。
(二)《禮拜五》的創作背景與既定主題
圖爾尼埃所處的時代是資本主義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當時,歐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逐步過渡到帝國主義階段,兩次世界大戰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分布,也讓人們對戰爭的野蠻和殘酷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在改寫笛福的故事之前,圖爾尼埃就對魯濱孫和禮拜五這兩個人物有過諸多思考。在《圣靈之風》中,圖爾尼埃承認笛福的《魯濱孫漂流記》是成功的,他認為禮拜五這個人物的出現是笛福最天才的設計,但同時他表示笛福只是用無盡的勞作讓魯濱孫受折磨。圖爾尼埃把魯濱孫的故事比喻成一顆種子,它被風吹到各地,在當地環境和思想的影響下產生了眾多新的作品,每一代人都能在魯濱孫的故事中體會到講述自我以及更好地認識自我的需要。[2]217-219因此,對從不同角度重寫魯濱孫的故事并在其中描繪當代人的情緒和向往,圖爾尼埃認為是有益處的。1967年《禮拜五》面世之后,為進一步發揮小說對青少年一代的教育意義,圖爾尼埃于1971年完成了該小說的改寫版——《禮拜五或原始生活》(Vendredioulaviesauvage)。1978年,在小說集《松雞》(LeCoqdeBruyère)中,圖爾尼埃續寫了魯濱孫的結局。可見,圖爾尼埃對魯濱孫的故事非常感興趣,也很有想法。他想通過自己的加工創作向世人展示不一樣的魯濱孫和禮拜五,講述對當代讀者更有現實意義的故事。
雖然《禮拜五》是在《魯濱孫漂流記》基礎上的改寫,但兩部小說在主題和哲學深度上有明顯的不同。圖爾尼埃曾明確表示,《禮拜五》這部小說的真正主題是“兩個人在一個荒島上發生的兩種文明的碰撞與融合。”[2]228可見圖爾尼埃的禮拜五和笛福的禮拜五從根本上是不同的。圖爾尼埃認為禮拜五也是某種文明的代表;而笛福筆下的禮拜五只是魯濱孫的一個尚未開化的仆人,不算一個文明人。圖爾尼埃還表示,真正讓自己感興趣的不是兩種文明在某一特定發展階段的結合,而是展示文明痕跡如何在一個經歷極度孤獨的個體身上逐漸消失,揭示生活和生命的基礎,呈現通過各種方式在荒島創造的新世界。[2]229圖爾尼埃還敏銳察覺到,隨著人類自由和財富的增加,人類越來越感到孤獨,而日益增長的孤獨感是當代西方人最危險的傷口[2]221-222。他曾這樣評價自己筆下的魯濱孫:“懂得調整孤獨并把它上升至生活藝術的高度。”[2]225-226小說中魯濱孫身上體現的對孤獨的掌控感以及他對周遭事物的各種反思,與作者童年的痛苦經歷及成長過程中接受的專業教育是分不開的。圖爾尼埃通過對魯濱孫一系列內心活動的描寫,塑造了一個有哲人傾向的全新的魯濱孫,讓讀者感受到這個魯濱孫不僅是孤獨的受害者,同時也是孤獨的主人。可見,文明的融合及直面孤獨是圖爾尼埃創作的兩個既定核心主題。在圖爾尼埃看來,自己的小說充滿創造性和預見性,而笛福的《魯濱孫漂流記》局限于描述利用文明社會所獲得的條件和習得的技能來重建文明社會,因而只具有單純的回溯性。
三、接受主體與《禮拜五》
“文學作品只有被接受并產生影響才能流傳下去,未被接受的作品無論如何都不會進入文學的歷史進程。”[3]顯然,無論是笛福還是圖爾尼埃的作品都已經進入文學的歷史進程。
國內外學者作為專業的接受主體,對《禮拜五》的研究屢見不鮮。在國外,1967年《禮拜五》一經面世就獲得了巨大成功,自然成為眾多學者的研究對象。這些接受主體從不同角度對小說進行研究,如:從兒童文學改寫角度對《禮拜五》進行深度剖析;從人類學、社會學、神話學、心理學等角度對作品進一步解讀;還有學者研究該作品中反映的哲學觀及哲學思想,等等。曾擔任伽利瑪出版社審稿員的法國后現代主義先驅雷蒙·格諾這樣評價《禮拜五》:“這是一個讀過佛洛伊德、薩特和列維·斯特勞斯的作者對《魯濱孫漂流記》的重寫”[4]。總之,西方批評界對這部作品及融會其中的現代哲學思想推崇備至,評價極高。
國內學者對這部小說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雖比國外稍晚,但研究視角十分多元。如:梳理魯濱孫的精神探索之途,解讀魯濱孫、禮拜五與荒島的全新三角關系;對小說的敘事序列進行整體分析;對該小說進行“他化研究”;從互文性理論、他者的構建與消解或生態批評的視角重新解讀作品;還有學者分析了該部作品里體現的道家思想;另外,作品中體現的哲學觀也是國內學者很感興趣的研究內容。中國翻譯家柳鳴九先生在王道乾譯版的《禮拜五》序言中評價道:“這類小說作為人類物質文明現實社會發展中的一種反思出現,它以駭世驚俗、近乎極端的方式,對現代文明表示了否定的態度……它否定的傾向會引起嚴肅的關注,激起深刻的思考,有助于人類文明在否定之否定的更高層面上發展的更全面、更健康……”[5]把一部作品和人類文明的發展聯系到一起,足以看出柳老先生對該部作品的推崇。總之,國內研究者普遍認為《禮拜五》是對笛福原作的一次成功改寫。
優秀的作品還會有許多非專業的接受主體,這些普通讀者也會對作品有所感觸。18世紀的讀者看到笛福的小說可能對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引以為豪,因為笛福筆下的魯濱孫會對禮拜五進行一系列改造,這正是殖民主義在“他者”土地上建立新秩序的寫照。20世紀的讀者讀《禮拜五》時,可能只對小說中蘊含的哲學思考印象深刻,但很難意識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重要性,更不會對作品中涉及的文明融合有所感悟。而當21世紀的當代讀者捧起這本小說,并把作者所處時代的社會文化因素以及作者本身的經歷和受教育背景考慮進去時,很容易在圖爾尼埃的改寫之作中看到創作主體想要傳達給接受主體的關于孤獨、文明及自然的見解。
四、《禮拜五》帶給當代文明世界的啟示
當今社會,諸多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都取得了輝煌成就,但伴隨這些進步的卻是人類自身的各種情感危機、自然環境的破壞以及文明之間的沖突。作為新寓言派的哲人作家,圖爾尼埃通過改寫給讀者呈現了不一樣的禮拜五和魯濱孫,也給我們所處的文明世界帶來一些啟示。
(一)關于孤獨
圖爾尼埃和笛福筆下的魯濱孫都是有堅定信念和勇敢意志的主人公,他們都沒有被荒島上的孤獨吞噬。大體來看,在禮拜五出現之前,兩個魯濱孫比較相似,他們都曾迷茫頹喪,但也都試圖在荒島上重建文明社會。不同的是,笛福筆下的魯濱孫很快戰勝了恐懼和孤獨,投入荒島的建設之中,情緒相對穩定;而圖爾尼埃筆下的魯濱孫情緒更加多變和反復:沒有同類令他孤獨,恩泰的出現讓他快樂,禿鷲間的食物爭奪使他惡心,越獄號受挫他感到失望,船長尸體的消逝讓他內疚又慶幸,泡在爛泥塘里使他平靜,制作出輕盈的小舟讓他開心,種植出茂盛的麥子讓他倍感親切……這些每天都會發生在人類身上的情緒讓圖爾尼埃的魯濱孫顯得更具“人性”,更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在圖爾尼埃的筆下,魯濱孫能夠在恐懼中不屈,在孤獨中反思,通過不斷的思考和多變的自我暗示讓自己在一次次精神沉淪之后得到救贖。比如在他的第一篇航海日志中,他這樣寫道:“所謂德行就是勇氣、力量、對自己的肯定、對物的控制。而罪孽就是自暴自棄、放任、逆來順受。”[6]
意識到禮拜五可能摧毀自己在島上建立的系統后,魯濱孫雖然憎恨他,但也在航海日志中反思自己的做法是否有悖于仁慈。當禮拜五再次出現讓他反感的行為時,他會把反感藏在心里。隨著讓他反感的事情越來越多,魯濱孫也曾怒火中燒,但隨后便能找到自我治愈的辦法。由此可見,圖爾尼埃筆下的魯濱孫感性與理性并存,且十分善于通過思考和聯想來控制自身的情感。
孤獨是現代人普遍存在的一種情感危機,生活中被孤獨吞噬的例子不勝枚舉。如何面對孤獨?圖爾尼埃用魯濱孫的荒島生存經歷告訴我們:你的思想就是你戰勝孤獨的最佳武器。
(二)關于文明的融合
結合作者的創作動機,我們能夠從魯濱孫和禮拜五在荒島上的相處和磨合中看到與當今全球化發展非常契合的一個主題:當兩個文明相遇時,只有消除文明沖突,摒棄文明優越感,才能實現文明的共存和融合。
在魯濱孫和禮拜五最初相處的時間里,對上帝和孤島環境心存敬畏之心的魯濱孫對這個阿勞干人展現了徹底的殖民者態度,他認為禮拜五是個愚蠢的、沒有靈魂的、馴良無比的低等人。但當他在島上的建設被禮拜五無意摧毀之后,魯濱孫慢慢理解了禮拜五,認為禮拜五的行動是自然本性使然。禮拜五在他眼中變成了沖動、慷慨、愛笑的土著,他還能和禮拜五玩得很有趣。通過望遠鏡發現禮拜五和羱羊在搏斗中雙雙跌落懸崖,他會急忙趕去施救。他還會按禮拜五的要求做一些他也不明就里的事情并為此感到高興,比如往羊皮上撒尿。禮拜五在魯濱孫面前敲碎象征魯濱孫的木偶人的頭顱后,魯濱孫明白自己再也不是希望島的總督了,但也不會就此淪為奴隸。他當著禮拜五的面,狠狠地抽打著象征禮拜五的沙子人像。他們的關系在這種你來我往的博弈中慢慢恢復平衡,從主仆關系逐漸演變為同伴關系。禮拜五扮演魯濱孫,魯濱孫就會十分配合地扮演禮拜五。魯濱孫認為這種角色扮演對自己是有益的,他對過去自己奴役禮拜五的行為深感愧疚。魯濱孫和禮拜五各自代表一種文明,在白鳥號到來之前,他們已經消除了文明沖突,摒棄了文明優越感,實現了兩種文明之間的共存與融合。
(三)關于回歸自然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我們更加清醒地認識到人類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對當代讀者而言,圖爾尼埃的《禮拜五》實現了對笛福《魯濱孫漂流記》的超越,因為它巧妙地將“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這一先進理念融入作品中,讓讀者們看到了文學有時確實會走到科學的前端。如果說丹尼爾·笛福的故事是為了表現人類對大自然的征服欲望,那么圖爾尼埃的版本更像是為了展現人類對自然的回歸渴望。
在《禮拜五》的結尾,白鳥號帶來了魯濱孫的同類,他短暫地思考過回到英國會怎樣。但登船與船長共進晚餐后,文明人的飯菜讓他感到難以消化,和船長相談不歡,船上的各種見聞……一切都讓他覺得先前自己所處的文明世界里的文明人是粗暴和貪得無厭的,原先文明社會中的正常現象讓如今的魯濱孫無所適從。他明白自己不再屬于那里,于是決心留在島上,并為此感到欣喜。結合作品反映出的魯濱孫的性格特點,他拒絕返回文明社會的行為很好理解:他經歷過文明社會的善和惡,體會過文明社會的喜和悲,在島上的28年里他和自然建立了更加和諧安逸的關系。因此,短暫地和文明社會打交道后,他有了比較,意識到希望島的自然環境沒有人類社會的各種弊端。
圖爾尼埃的作品直接以“禮拜五”命名,顯示了在其作品中原始人禮拜五地位比文明人魯濱孫更重要。禮拜五不僅是破壞者,也是創造者,他甚至教會魯濱孫釋放自己的本性。正是因為禮拜五,魯濱孫才慢慢愿意親近自然,融入自然,崇尚自然,最后回歸自然。這讓我們對“文明社會”有所反思:如果不能尊重自然,不能與自然和諧相處,一味地征服自然,那現代人就會走上一條危險的不歸路。人類只有尊重自然,回歸自然,才能重獲精神的凈土。
面對不同時期的文學作品,讀者作為接受主體,各自處于各自的時代。如果對創作主體及其所處時代的社會文化背景有所了解,那么一定能夠更好地理解他們的作品和作品中的世界,從而更全面地理解文學作品所要傳達的信息,更深刻地體會文學作品的社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