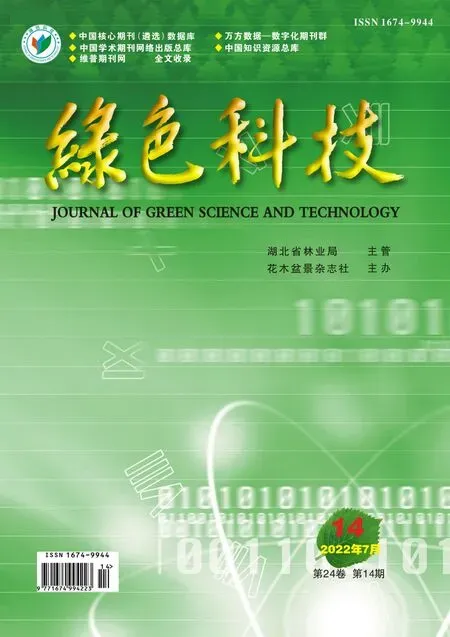宜昌地區大氣污染特征及氣象影響分析
成 勤,王清龍,劉 俊 ,張 翠,饒少林
(1.宜昌市氣象局,湖北 宜昌 443000;2. 宜昌市環保監測站,湖北 宜昌 443000)
1 引言
氣象條件作為影響空氣質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制約著污染物的稀釋、擴散和轉化,其中氣溫、相對濕度、降水量、風速等要素與空氣質量相關性最為顯著[1~4]。大氣污染具有復合性和區域性特征[5],多數研究表明PM10、PM2.5等污染物濃度與氣溫負相關[5~8],也有研究認為溫度與PM10正相關[9]。我國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地主要大氣污染物與相對濕度顯著正相關[5,6],而長江中下游多個城市大氣污染物與相對濕度顯著負相關[10,11]。降水總體有利于空氣質量改善,受降水量、降水強度、降水時長、污染等級等因素影響,對不同種類污染物的清除效果有所差別[11~14]。風速與大氣污染物濃度總體呈負相關[15],但超過一定閾值后,污染物濃度反而增加[12,16,17]。
進一步研究表明,氣象要素對大氣污染物的積聚、擴散作用復雜,且受監測站點地形、區域位置影響顯著[18~20]。宜昌市東西高差大,長江穿越其間,形成了自西部山地向東部平原開口的“喇叭口”地形。受此特殊地形影響,宜昌地區主要大氣污染物為PM2.5、PM10和O3,大氣污染特征與周邊相差較大,氣象要素對污染物影響機制也不盡相同,有必要進一步分析,為空氣污染防治行動提供技術支持。
2 資料和方法
2.1 數據來源
資料時長為2016~2020年,來源于宜昌市環保監測站和宜昌市氣象局保障中心,主要包括PM2.5、PM10日平均質量濃度(以下簡稱濃度)、O3濃度(最大8 h 滑動平均值)、日平均氣溫、相對濕度、降水量、平均風速、最大風速。
2.2 分析方法
日平均風速為一天中風速的平均值。日最大風速為一天中任意10 min 平均風速的最大值[2]。有降水時,相對濕度一般為100%,污染物受降水沖刷作用影響,濃度明顯下降,因此分析相對濕度與污染物關系時,采用無降水時段數據。環境及氣象監測數據均通過K-S檢驗,符合正態分布特征。以皮爾遜相關系數表征污染物濃度與氣象要素的相關性,雙尾檢驗的顯著水平為0.01和0.05。將降水前后污染物濃度的變化率定義為清除率[22](R)。
3 結果分析
3.1 大氣污染特征
統計宜昌地區各月污染物平均濃度及污染日首要污染物種類,結果如圖1所示。PM2.5濃度冬季最大,平均值為99 μg/m3,夏季最小,平均值為23.6 μg/m3。PM2.5/PM10冬季最大,夏季最小,均值為68.6%,PM10的變化趨勢與PM2.5基本一致。PM2.5為首要污染物的時段集中在11月份至次年2月份,每月平均16.8 d,PM10為首要污染物的天數較少。除2019年1~2月份外,PM2.5、PM10濃度以及出現污染的日數呈逐年下降趨勢,與周邊地區變化趨勢一致[11]。2019年1月份和2月份分別出現31 d和17 d的PM2.5污染,其中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數分別為11 d和1 d,主要是因為2019年初歐亞高緯度兩槽一脊形勢穩定,有利于冷空氣頻繁南下和堆積,與常年同期相比,冷空氣頻繁但勢力偏弱,風力較小,靜穩天氣長時間維持,1~2月份氣溫偏低2.0 ℃,降水量偏少30%~40%,且多以短時小雨為主,對污染物的清除作用不明顯。
O3濃度夏秋季節最大,平均值為116 μg/m3,2017年開始出現以O3為首要污染物的污染過程,O3濃度及其超標天數呈逐年增加趨勢[3],其中2019年6~10月份較常年同期增加較多。主要是因為2019年出現伏秋連旱,日照充足、晴熱高溫,與常年同期(6~10月份)相比,降水偏少40%~50%,排歷史同期倒數第3位,為O3濃度升高提供了有利的氣象條件。

圖1 污染物濃度(a)及首要污染物天數(b)月分布
3.2 相關性概況
計算各污染物濃度與主要氣象要素(平均氣溫、相對濕度、降水量、平均風速、最大風速、最多風向風速)的相關系數,結果如表1所示。從表1中可以看出,所有氣象因素中,平均氣溫與污染物相關性最好,平均氣溫與O3濃度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達0.619,與PM2.5和PM10顯著負相關,相關系數分別為-0.598和-0.526,與多數研究結論一致[5~8]。相對濕度與PM2.5正相關,與PM10和O3濃度負相關,這一特征與武漢等長江中下游城市相反[10,11],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以上文獻中,未去除降水對相對濕度和污染物濃度的影響。降水量與PM10、PM2.5和O3濃度均負相關[22],相關系數分別為-0.243、-0.204和-0.134。平均風速、最大風速、最多風向風速均與PM2.5、PM10濃度負相關,即風速越大,顆粒物濃度越小。平均風速、最大風速、最多風向風速均與O3濃度正相關。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地面氣象要素與各污染物濃度相關性顯著,有必要進一步定量分析。

表1 污染物濃度與氣象要素相關系數
3.3 平均氣溫與污染物
統計不同溫度下的污染物平均濃度,結果如圖2所示。0~9 ℃時,PM2.5濃度大于75 μg/m3(輕度污染),峰值出現在3 ℃,達103.1μg/m3,PM2.5和PM10相關性高,變化基本一致。平均氣溫3 ℃ 以下時,PM2.5、PM10濃度隨氣溫下降而減小,其原因主要是3 ℃ 以下時,宜昌市多受較強冷空氣影響,冷鋒過境前,天氣回暖,隨著冷氣團南下,以PM2.5、PM10為主的顆粒物進入“喇叭口”,造成空氣污染,冷鋒過境時氣溫迅速下降,多伴有降水、大風,有利于顆粒物的水平擴散和沉降,造成了顆粒物濃度隨氣溫降低而下降。3 ℃ 以上時,隨氣溫升高,PM2.5和PM10濃度下降。O3濃度隨氣溫升高呈顯著上升趨勢,27~34 ℃時,O3濃度穩定維持在120 μg/m3上下。以上分析結果與前文相關性分析結論一致。另外,15~17 ℃ 時,冷空氣較活躍,有利于顆粒物輸入,氣溫起伏大,日照充足,光化學反應增強,PM10、PM2.5和O3濃度均有所上升,易出現PM2.5-O3復合污染[23]。

圖2 污染物濃度隨氣溫分布
3.4 相對濕度與污染物
統計不同相對濕度下的污染物平均濃度,結果如圖3所示。相對濕度小于50%時,污染物濃度隨著相對濕度的增加,呈波動增長趨勢,且振幅較大,容易出現PM10或O3污染天氣。相對濕度在50%~80%時,隨著相對濕度的增加,PM10和O3濃度緩慢下降,PM2.5濃度上升,與前文相關性分析結果一致。相對濕度大于80%時,O3濃度明顯下降,PM10和PM2.5濃度呈波動上升趨勢,在接近飽和(100%)時陡增,均達到最大值。主要是因為在冬季冷空氣主體來臨前,宜昌受西南暖濕氣流影響,近地面減壓增濕,相對濕度增大,顆粒物吸濕增長,早晨和夜間常出現逆溫層,垂直和水平擴散條件變差,使得本地污染物濃度增大,加之前沿冷空氣不斷引導北方污染物南下,進入宜昌“喇叭口”,導致污染天氣發生。
3.5 降水與污染物
參考中國氣象局降水等級劃分標準,結合樣本數量分布,將降水分為0.1~4.9 mm、5~9.9 mm、10~24.9 mm、25~49.9 mm和 ≥ 50 mm,分析不同量級降水對污染物的清除作用,結果如圖4所示。
從圖4中可以看出,降水量與PM2.5的清除率占比相關性最好,PM2.5的正清除率占比連續增加,由51%升至87%,負清除率占比連續減小,由45%降至13%。PM10的正清除率占比先增后減,5~24.9 mm時清除效果最好,正清除率占比達60%以上,暴雨及以上時,清除效率反而下降,負清除率占比變化趨勢相反。O3的正清除率占比波動增加,最大達73%,負清除率占比波動減小,最小為27%。0清除率占比變化不大,且均較小(小于7%)。

圖4 不同量級降水清除率占比分布
3.6 風速與污染物
統計不同平均風速時,污染物平均濃度可知,顆粒物(PM10和PM2.5)濃度總體呈減小趨勢。當平均風速在3.3~3.7 m/s時,風速增大使地表粉塵和建筑粉塵被風帶起,導致顆粒物濃度增大[12](圖5a)。統計不同最大風速下污染物濃度,發現了相似規律,PM10和PM2.5濃度在最大風速小于7.4 m/s時,隨風速增大而下降,最大風速小于1.6 m/s時最為顯著,在最大風速大于7.4 m/s時,波動幅度增大(圖5b)。
當平均風速小于2.1 m/s時,O3濃度隨風速增大而增加,最大值為99.74 μg/m3。當平均風速大于2.1 m/s時,風對O3擴散稀釋作用增強,O3濃度逐漸減小(圖5a)。O3濃度在最大風速小于4.0 m/s時,隨風速增大而顯著增大,在最大風速4.0~6.8 m/s時,緩慢增加,在最大風速大于6.8 m/s時,波動幅度增大(圖5b)。
4 結論
(1)宜昌地區主要污染物為PM2.5、PM10和O3,除2019年受頻繁弱冷空氣和伏秋連旱天氣影響,污染加重外,空氣質量整體變好。
(2)顆粒物濃度與平均氣溫整體負相關,但3 ℃ 以下時,PM2.5、PM10濃度隨氣溫下降而減小。O3濃度與平均氣溫顯著正相關,27~34 ℃時維持在120 μg/m3上下。15~17 ℃ 時易出現PM2.5-O3復合污染。
(3)相對濕度50%以下時,與污染物濃度正相關。相對濕度在50%~80%時,與PM10和O3濃度負相關,與PM2.5濃度正相關。相對濕度大于80%時,O3濃度明顯下降,PM10和PM2.5濃度呈波動上升趨勢,在接近飽和時陡增。
(4)降水量與污染物濃度均呈負相關。降水量與PM2.5的清除率占比相關性最好,PM2.5的正清除率占比連續增加。PM10的正清除率占比先增后減,5~24.9 mm時清除效果最好。O3的正清除率占比波動增加。
(5)風速的增大有利于顆粒物濃度降低,但在平均風速為3.3~3.7 m/s時,地表粉塵和建筑粉塵被風帶起,導致顆粒物濃度增大;O3濃度在平均風速2.1 m/s以上時,隨風速增大而減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