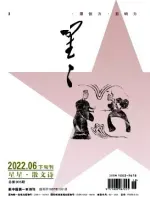節氣之美
姜 明(四川)
基本上每過半個月,便有一個美好的名字等著你,你會猝不及防、驚呼連連:“哇,都谷雨了,難怪今天下雨了!”也可能你會欣逢其會、正中下懷:“我說嘛,天氣這么熱,可不今天就是立夏了嘛!”
立春、清明、谷雨、立夏、小滿、秋分、白露……這些美好的漢字,構成了一冊活色生香的群芳譜,這是古代先人們給日月星辰、山川風物取的名字,也是他們給田壟麥地、果蔬花草寫下的契約,還是他們對氣候和人體氤氳交錯、和衷共濟達成的共識。那么美,像不同風姿的女子,在不同的季節,不同的山頭,與你平分秋色、共享春光,你不知道,美的究竟是景色,還是女子。
中國的節氣,第一大美就是她們的名字,你窮盡想象力,沒辦法取出更好的名字。我經常看到這些名字就想入非非,就想:多么美好!春分,我與愛人共坐春風;芒種,忙著耕種,不可荒廢光陰啊;小滿,不可完滿,小滿是福,千萬要知足常樂啊……二十四節氣,沉湎勾連于那種文字的美,是人的第一大本能,稍加生發,對其內涵、意蘊的想往,會讓人在瑣碎的日常中,涌動出對自然和詩意的熱愛。足可見,好的文字,就是山水畫,水流有聲,山青見骨,雅淡空靈,旨歸心懷。我無法說明對她們的喜愛,但我很清楚的是,愛她們的名字,進而愛彼時的天氣物候、愛當下的生活、愛身邊的人——節氣,仿佛就是一種幸福提醒:此時多么美,愛她!珍惜她!
節氣是群芳譜,是山水畫,但是很顯然,詩意絕對不是節氣的主旋律,節氣首先是對勞動的禮頌,是對生產的致敬。每一個節氣對應的都是農時,對應的是彼時的勞作和辛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節氣就是耕作圖,是古人對農時、農作進行網格化精準管理的一種備忘錄——
“春分麥起身,一刻值千金。”
“鄉村四月閑人少,才了蠶桑又插田。”
“小滿過三車,忙得不知他。”
“芒種栽薯重十斤,夏至栽薯光根根。”……
在書本和我們的想象中,鄉村的勞作也許充滿田園牧歌式的美好,但在現實生活中,更多的則是日曬雨淋的艱辛和人與天斗、天公負人的無奈,勤勞豁達的中國人,卻并沒有被微薄的收成所擊垮,而是順應自然、躬耕不輟、天人合一、取宜守則,于苦中作樂,于忙中養心。芒種,忙種,既要收割麥子,又要開種水稻,既充滿收獲的喜悅,又播種新一輪的希望,日子在苦累但美好的情愫中度過,誰能說中國的歷代農民就只有一個苦字能形容呢?苦當然不是財富,當然不值得夸耀,但是把苦修煉成為一句句的諺語、一個個的節氣,農民怎么就不是生活的藝術家?不是偉大的現實主義大師?
更多的時候,節氣充盈著生生不息、疊翠壘彩般的生命智慧。節氣節氣,一個節字,加一個氣字,蘊藏了古代中國人對宏大宇宙的極致概括和對個體生命的精微把握。我曾長時間認真冥思,有沒有可能從浩如煙海的辭海中找出兩個字來替換節氣?后來我斷定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節氣——節,是節律、節奏、節令、節制、節操,是人對自然、生命和社會關系的穎悟、讓渡、呼應和珍重;氣乃天地正氣,是“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所謂力與美,是“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之陰陽平衡、美美與共,是萬物相搏競榮的蓬勃活力和有序就位。“晝夜均而寒暑平”,春分是對天地自然的求衡與調和,也是對人戒貪止奢、互利共享的莊重提醒;“晝晷已云極,宵漏自此長”,夏至至長,長則漸短,盈虧相繼,提醒人宜常懷遠憂,慎始如初;鴻雁來,玄鳥歸,群鳥養羞,白露以唯美的物象和隱喻映射山高水長和花草枯榮,提醒人珍惜華年,不懼晚霜;草木黃落,蟄蟲咸俯,霜降以晚秋悲聲和樹樹霜華肅迎寒冬,提醒人磊落高潔、端莊凜冽……
是的,節氣之美,最美還是智慧的古人們對后人們的這一聲聲叮囑,這一句句托付。節氣,借物候的變遷,提醒我們珍惜時光,趁勢而為,“少年,你在三四月間做你該做的事,到八九月份,自會有收獲”。在被古人詩化、同時世俗化了的時空里做該做的、而且被反復證明是正確的事情,現代人是何其有福,而在二十四番花樣提醒、七十二候神性啟示下,縱萬丈紅塵、淵藪無限,終究行有規矩,歸有依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