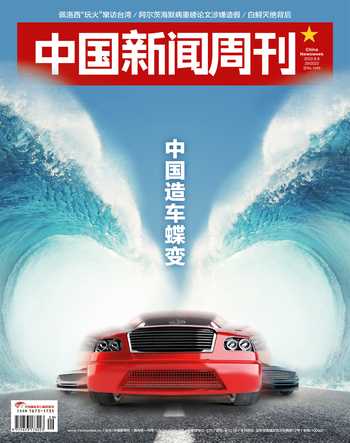跟不上氣候變化的企鵝會“消逝”嗎?
牛荷

南極洲的帝企鵝群。圖/視覺中國
走路蹣跚,又堪稱“游泳健將”和“潛水高手”的企鵝在地球上已誕生了6000多萬年,成為水中高手前,它還具有飛行能力。
7月19日,自然出版集團旗下刊物《自然通訊》在線發(fā)表的一項國際研究給出了企鵝由飛行到適應(yīng)海洋的詳細進化史。研究團隊通過構(gòu)建包括亞種在內(nèi)的24種現(xiàn)存企鵝和近代滅絕的3種企鵝的基因組數(shù)據(jù)集,首次將現(xiàn)存企鵝和最近滅絕的企鵝譜系的基因組數(shù)據(jù)與完整化石記錄相結(jié)合,重建了企鵝的進化史,并確定哪些基因有助于企鵝過渡至水生動物。
研究表明,企鵝是已獲得全基因組數(shù)據(jù)的鳥類中進化最慢的物種之一,這可能讓它們難以適應(yīng)目前全球變暖的速度。該研究合作者、布魯斯博物館的鳥類古生物學(xué)家丹尼爾·克塞普卡在回復(fù)《中國新聞周刊》的郵件中寫道,“從化石記錄中看到企鵝可以適應(yīng)氣候變冷或變暖,但問題是這種適應(yīng)往往需要數(shù)萬年甚至數(shù)百萬年。如果未來幾十年,全球持續(xù)快速升溫,包括企鵝在內(nèi)的大多數(shù)物種恐怕沒有足夠的適應(yīng)時間。”
翅膀變成鰭狀肢、身體呈流線型、長時間潛水、圓胖的身體……這些特征使得現(xiàn)代企鵝看起來并不像鳥類,卻有助于它們更好地適應(yīng)海洋生活和寒冷氣候。拉長時間來看,上千萬年以來,企鵝并未停止進化的腳步,伴隨著地質(zhì)、氣候、環(huán)境等因素的變化,形成了如今所看到的現(xiàn)代企鵝。《自然通訊》這項研究中,研究者們給出了企鵝進化的“全貌”。
研究顯示,6000多萬年前,企鵝祖先在古西蘭地區(qū),今新西蘭大陸出現(xiàn),隨后從古西蘭擴散到南美洲和南極洲。3400萬年前南極冰蓋形成,這期間分化出不少巨型企鵝。最近一次企鵝物種多樣化始于200萬年前第四紀大冰期,這一時期全球氣溫大幅變冷,中、高緯地區(qū),包括極地以及高山區(qū)在內(nèi)廣泛形成大面積冰蓋和山岳冰川。冰蓋擴大和環(huán)境變化促使企鵝開始遷徙到更廣泛的地區(qū),彼此之間逐漸隔絕開來,導(dǎo)致其快速分化出多種現(xiàn)生企鵝物種。
論文共同第一作者、深圳華大生命科學(xué)研究院副研究員周程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通過目前研究發(fā)現(xiàn)的最古老企鵝化石判斷,當(dāng)時的企鵝翅膀可能還具有折疊功能,但是已經(jīng)不能飛行。克塞普卡說,最早的企鵝祖先可能是從一種可以飛行的海雀類動物進化而來,由于前者尚未在化石記錄中被發(fā)現(xiàn),因此無法準(zhǔn)確知道企鵝何時失去了它們的飛行能力 。
該研究的通訊作者、浙江大學(xué)生命演化研究中心教授張國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物種分化往往伴隨著復(fù)雜的基因流動,這使得企鵝形態(tài)更加多樣化。據(jù)世界自然保護聯(lián)盟(IUCN),目前公認的企鵝物種共計18種,包括帝企鵝、阿德利企鵝、洪堡企鵝、黃眼企鵝等。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南半球廣大區(qū)域也分布著不同種群的企鵝。
“在漫長進化中,企鵝演化出一套適應(yīng)環(huán)境的‘基因秘籍’,在體溫調(diào)節(jié)、氧和、潛水、視力、體型等方面均有著相關(guān)進化基因,將企鵝塑造成如今的模樣,讓它們更好在寒冷環(huán)境和在水下生活。”周程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相較早期企鵝,現(xiàn)生企鵝在體型上逐漸趨向小型化,用于獲取食物的喙變得短小,由翅膀演變而來的鰭狀前肢更適合海洋環(huán)境。周程冉說,味覺方面,企鵝只保留了對酸味和咸味的感知,丟失了鮮、甜和苦味的相關(guān)基因,研究推測在寒冷的海洋中進食,后幾種味覺的丟失對它們而言影響不大。
多種基因突變還令企鵝有著很強的紫外線感知能力、視覺敏感度等,即便在弱光或昏暗的海水中也能保持敏銳的視覺。“海水中光的照射頻率和在陸地上存在明顯差異,企鵝如果自身不進化,長期在海水中會導(dǎo)致其視力受損。”張國捷說。
不同企鵝物種在海水中的潛泳能力也存在差異。周程冉舉例,從潛水時間和深度上看,帝企鵝是所有企鵝中潛水能力最強的,能在500多米深海區(qū)潛水約30分鐘,大部分小藍企鵝最多只能潛水幾分鐘。“這種差異除了基因?qū)用娴脑颍€受到企鵝棲息地環(huán)境以及食物資源影響。比如小藍企鵝一般選擇近岸地方捕獲食物,而且小藍企鵝的體型比帝企鵝小,食量也相對較小。”她說。

丹尼爾·克塞普卡認為,最早的企鵝祖先可能是從一種可以飛行的海雀類動物進化而來。圖/視覺中國
如今,企鵝已與棲息地形成適應(yīng)關(guān)系。比如同樣生活在南極的帝企鵝和阿德利企鵝,前者選擇冬季到冰蓋上的某一地區(qū)孵化下一代,帝企鵝幼崽外表為灰色,這與孵化地冰蓋的顏色相對應(yīng);后者則在春夏季到達南極海岸線進行繁殖,這時部分區(qū)域的冰川開始融化,地面的褐色巖石裸露出來,阿德利企鵝的幼崽顏色偏褐色。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中還將企鵝與360多種非企鵝鳥類的基因組數(shù)據(jù)進行比對,發(fā)現(xiàn)企鵝和其近緣的信天翁演化速率最慢。克塞普卡認為,這可能與壽命高于平均水平、后代數(shù)量少等因素相關(guān)。“發(fā)現(xiàn)這一點時很意外,因為企鵝和其他鳥類類群在體型和繁殖時間上并沒有顯著差異,我們沒預(yù)期到企鵝會比其他鳥類進化慢這么多。”張國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周程冉回憶,“當(dāng)時發(fā)現(xiàn)這一結(jié)果后,又對比了其他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親緣關(guān)系較近的水生鳥類比非水生鳥類的演化速率更低。因此推測原因可能和水鳥的水生特性也有關(guān)系。”
“從企鵝的演化速率來看,體重和演化快慢并沒有顯著相關(guān)性,但研究發(fā)現(xiàn)體型最大、生活在高緯度的帝企鵝演化速率是所有企鵝中最快的。”在周程冉看來,南極極端環(huán)境給高緯度企鵝帶來了較大的環(huán)境壓力。冰期和氣候波動等環(huán)境事件進一步推動了企鵝的遷徙、演化與分化,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高緯度物種對極端環(huán)境的適應(yīng)。“企鵝的物種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氣候變化、地質(zhì)運動等驅(qū)動的。”研究指出。
“企鵝演化速率慢,可能意味著它們需要更長時間適應(yīng)環(huán)境和氣候變化。”在周程冉看來,盡管目前企鵝已經(jīng)對海洋生活和南極環(huán)境產(chǎn)生了很強適應(yīng)度,但這種“強適應(yīng)度”建立在上百萬年的時間單位基礎(chǔ)上,目前監(jiān)測到全球明顯升溫的時間跨度縮短至過去的100年至300年間。企鵝能否快速適應(yīng)氣候變化,未來生存是否存在嚴重威脅,都是值得擔(dān)憂的問題。
世界氣象組織秘書長佩蒂瑞·塔拉斯2021年表示,南極半島是地球上變暖速度最快的地區(qū)之一,過去50年間上升了3℃。今年5月,塔拉斯稱,過去七年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七年,未來還會出現(xiàn)“有記錄以來的最熱一年”。“總體來講,整個南極的平均溫度在快速上升。”中國科學(xué)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李熙晨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不同區(qū)域溫度上升程度不同。一些站點還出現(xiàn)了爆發(fā)性增溫,雖然較為短暫、影響較小,但這種極端性現(xiàn)象卻越來越頻繁。
根據(jù)世界自然保護聯(lián)盟公布的企鵝信息統(tǒng)計,目前全球超過40%的企鵝生活在南極洲。張國捷分析,南極不規(guī)律的溫度變化可能對企鵝的繁殖影響較大,比如孵化困難;另外可能也會對周邊食物結(jié)構(gòu)產(chǎn)生影響,從而影響企鵝的遷徙路線和棲息地。
全球升溫導(dǎo)致的最直接結(jié)果便是冰川加速消融。據(jù)政府間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IPCC)數(shù)據(jù),自1990年至2022年,全球兩大冰蓋——格陵蘭島和南極洲的冰蓋都在消融,2010~2019年期間的損失率最高。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衛(wèi)星數(shù)據(jù)顯示,自2003年以來,南極洲正在以每年約1500億噸的平均速度流失冰塊,格陵蘭島每年流失約2800億噸。
李熙晨表示,過去十幾年間,整個南極冰川的融化速度加快了至少三倍。“如果氣溫后續(xù)仍然增加的話,未來南極冰川消融的速度可能會進一步增加。”他擔(dān)心的是,相較之前緩慢的冰川消融,未來某一刻西南極冰川可能會存在“崩潰式”消融的風(fēng)險。“如果整個西南極冰川都消融了,全球海平面至少會上升6~7米。這會造成很大危機,很多地方可能會面臨被‘淹’的命運。”
企鵝的生存與冰川息息相關(guān),它們在海冰上繁殖、休息和換羽,企鵝的食物——磷蝦也在冰層邊緣附近繁衍生息。克塞普卡說,帝企鵝每年冬季都試圖回到同一個地方繁殖,如果溫度持續(xù)升高,將很難找到穩(wěn)定而持久的冰來撫育后代。據(jù)美聯(lián)社報道,2016年,南極洲哈雷灣約一萬只小帝企鵝被淹死,因為海冰在小企鵝長出羽毛前就已破裂,該地曾是帝企鵝最大的繁殖地之一。2017年及2018 年,由于海冰沒有完整復(fù)原,導(dǎo)致這兩年每個繁殖季節(jié)這一地域的小帝企鵝幾乎都死亡。此后,哈雷灣幾乎再沒有出現(xiàn)過帝企鵝,而附近的道森蘭頓的帝企鵝數(shù)量出現(xiàn)明顯增加。
前述《自然通訊》的研究指出,相比祖先企鵝,現(xiàn)代企鵝的演化速率變低了。當(dāng)置身于全球變暖的氣候背景下,其生存現(xiàn)狀似乎并不樂觀。“在目前已知的企鵝物種中,約有四分之三已經(jīng)滅絕。”克塞普卡說。《中國新聞周刊》查詢世界自然保護聯(lián)盟的紅色名單發(fā)現(xiàn),目前現(xiàn)存18種企鵝物種中,12種企鵝的種群數(shù)量均出現(xiàn)遞減,被認定為瀕危、近危或易受傷害的物種共11種,占比超60%。其中黃眼企鵝、非洲企鵝、直頂企鵝、北跳巖企鵝、加拉帕戈斯企鵝已處于瀕危狀態(tài),加拉帕戈斯企鵝的成熟個體數(shù)減至1200只。

2019年,在新西蘭發(fā)掘到一些生物化石。以這批化石推測,大約在6600萬年前,曾經(jīng)有高160厘米、重80公斤的巨型企鵝棲息在新西蘭。
“目前看來形勢還比較嚴峻。”周程冉說,這些瀕危企鵝大多并未生活在南極大陸,而是生活在非洲、新西蘭等地。這些地方的種群更易受到人為因素影響,再加上氣候變暖、棲息地缺失等因素,導(dǎo)致現(xiàn)有種群不太穩(wěn)定。此次發(fā)表在《自然通訊》上的研究涉及的三種已滅絕企鵝大多都是基于這些因素消亡的。這三種滅絕企鵝分別是查塔姆島企鵝、查塔姆島黃眼企鵝、懷塔哈企鵝,此前都曾生活在新西蘭。
并非所有企鵝物種在氣候升溫后,都出現(xiàn)種群數(shù)量下降的情形。“不同企鵝物種應(yīng)對氣候變化的反應(yīng)存在差異,這可能和它們彼此不同的生活史相關(guān)。”張國捷認為。
據(jù)《科學(xué)美國人》2019年7月報道,1982年到2017年,隨著氣溫上升,南極西部半島的巴布亞企鵝繁殖數(shù)量從2.5萬只躍升至17.3萬只。據(jù)了解,巴布亞企鵝主要分布在南極半島、福克蘭群島和南喬治亞島,隨著冰層融化,它們會調(diào)整食物種類并擴大活動范圍,比如從捕食磷蝦轉(zhuǎn)移到魚類。在獲取食物方面,巴布亞企鵝可以以每小時22 英里的速度游泳并潛得更深,而阿德利企鵝則依靠漂浮的海冰來覓食。中國第38次南極科考隊成員閆登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企鵝數(shù)量減少并不意味著這些企鵝滅絕了,可能是因為當(dāng)?shù)氐臍鉁厣吆螅簌Z選擇遷徙到更寒冷的高緯度地帶重新定居,這需要至少幾十年的時間來監(jiān)測、跟蹤。
在李晨曦看來,盡管有《南極條約》等保護舉措,但當(dāng)置身于全球范圍內(nèi)碳排放、氣溶膠顆粒等污染物充斥的大環(huán)境時,南極也很難獨善其身。張國捷說,也不要過于悲觀,現(xiàn)在絕大部分企鵝還不是瀕危物種,企鵝自身在面臨環(huán)境變化時也會有協(xié)調(diào)機制。
但在周程冉看來,基于種種風(fēng)險因素,對于有些企鵝物種而言,未來可能會面臨滅頂之災(zāi)。 “氣候的劇烈變化在一定程度也可能超過它們的承受范圍。對企鵝自身來說,這可能刺激它們進行下一輪進化,或者某些物種將面臨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