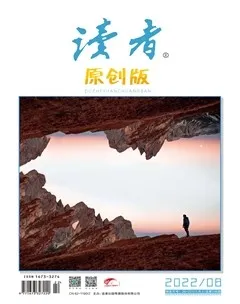喜歡新衣服的媽媽
文|柴嵐綺
一
媽媽愛美,但年輕時沒那個經濟條件去認真打扮。她說有一次干活掙了一塊錢,就去市集買布,和好朋友各做了一件襯衣,激動了很久。那時的她20歲出頭。
媽媽30多歲時,家里的經濟條件有所好轉,稍微有了一些積蓄,她托去上海出差的同事買了一件呢子大衣。那是她人生擁有的第一件呢子大衣,花了123塊錢。
大衣是人字呢質地的,灰黑色,媽媽回憶起那件大衣時總會加重語氣強調:“是全毛的!”西式大翻領,兩側有插兜,略收腰身,衣長到小腿肚,領口那里繡著“上海第一XX廠”的標識,中間那兩個字我忘了。
退休以后,媽媽搬到了我們小區,幫我們接送小孩。那件后來被我喊為“123”的呢子大衣她早已不穿了,但又舍不得扔。我很喜歡那種復古又溫暖的調調,便說:“把‘123’傳給我吧!”“123”呢子大衣便從媽媽的衣柜來到了我的衣柜。
我僅試過一回,穿上以后有一種厚重的感覺,好像迎面吹來再大的風也不怕。后來我又因孩子上學搬了家,送了不少東西給買房子的人。過了兩年,在家尋不到“123”,一想,壞了,應該是擱在舊家衣柜的最上面,也留給買房子的人了。可他們哪里會知道,那是媽媽人生中的第一件呢子大衣,哪里會知道它被我們叫作“123”呢!這么一想,我便覺得對不起媽媽,對不起沉默的“123”。
二
20世紀90年代,有一段時間,媽媽很喜歡找裁縫做衣服。那時,街上裁縫店的生意都還不錯,有的還擁有最新出版的、讓人驚嘆的時裝書。常有人帶一塊布料站在裁縫店里,長久地翻著書選樣式,裁縫則在一旁埋頭“嗒嗒嗒”地踩縫紉機。有一回,我陪媽媽去裁縫店,她帶了一塊暗紋的毛料去做冬天的裙子。她從書上選了一個款式,仔細地交代師傅她想要的效果。師傅用那塊毛料做出來一件西裝裙,正面看上去普通,但后面開衩的地方捏出許多豎褶,媽媽喜歡這種小小的別出心裁。在當時的小縣城,媽媽只要走在街上,總會被陌生女孩熱情地詢問:“你這件衣服真好看,在哪兒買的?”“是在哪兒買的布,請哪家師傅做的啊?”媽媽既高興,又有點兒矜持。
記得有一年的母親節,我給她買了一件T恤。T恤是黑白細條紋的,很洋氣,那時不多見。媽媽很喜歡,洗干凈后將它放在五斗柜她的那一格抽屜的最上面,并叮囑我:“要是有人問你是從哪兒買的,你可不要說啊。”她喜歡與眾不同。
我是特別喜歡穿棉布衣服的人,每次買的新衣服總會被人當成是舊的,無人詢問。但我就是喜歡那種舊舊的、不突兀的安全感。可我給媽媽買衣服時就很大膽,因為媽媽有一種能駕馭各種類型衣服的自信氣場。有一次快過年了,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我在單位加班,忽然想到還沒給媽媽買過年的新衣服,趕緊沖到對面的百貨大樓,買了一件暗紅色的、左肩繡著珠花的長款棉衣,興沖沖地跑回去送禮物。正忙著做飯的媽媽把我罵了一頓,說我總是亂花錢,氣得我眼淚都出來了。但有一天,我下班后進入小區,忽然發現前面走著的是媽媽,她正在和鄰居散步,我聽到她說:“我的衣服都是我女兒買的……”
三
那么愛美的媽媽,現在已經70多歲了,得了慢性病,這兩年忽然失去了穿好看衣服的興致。去年整個冬天,她在家里就穿著我給她買的薄羽絨內膽,要是打算出門,就在外面加一件咖啡色格子的呢子外套。她說:“千萬不要買新衣服了。現在最怕家里堆滿厚衣服,一想到冬天過去了要洗那么多衣服,我就覺得很累。老了,干不動活了,就希望生活里的一切都簡簡單單的。”
穿過的確良、泡泡紗、府綢、絲絨、朱麗紋、重磅真絲、香云紗的媽媽,穿過呢子大衣、旗袍、一步裙、裙褲、腳蹬褲、甩褲的媽媽,曾經那么愛美、愛與眾不同的媽媽,說現在只想穿簡簡單單的衣服,不再染頭發,不再穿高跟鞋,只希望身體健康,不給孩子添麻煩。
前幾天,帶媽媽去看中醫時,她穿著我給她新買的紅色T恤和黑色束腳褲。束腳褲是那種涼絲絲的材質,她說穿著很舒服。“再買一條灰色的吧?不貴,幾十塊錢,夏天正好一洗一換。”她急忙擺手:“不要買了,不要買了!家里衣柜里還有那么多衣服呢!”
老中醫在里面忙著接診,很多人圍著他。我們在外面的長凳上等著,我坐在媽媽旁邊,打開手機在網店下單。這時,她扭頭喜滋滋地對我爸說:“看,非要再給我買一件新衣服!”
但那家網店遲遲沒有發貨,客服告訴我:“灰色束腳褲斷貨了,你申請退款吧。”我找到有同款的另一家店,又下單,客服第二天說:“現在灰色的那件短缺,如果想買,需要等,時間比較久,你愿意等嗎?”
我愿意等。我想象著,在陰雨的黃梅天氣里,南方的一家工廠中有車輛運輸來成匹的布料,有人把布料放到貨架上,也有心靈手巧的師傅在用機器趕工……當然,這是我想象中的一切,可能完全不是這樣的流程。我坐在回家的地鐵上,看著那筆待發貨的訂單,陷入這樣美好的想象,因為70多歲的媽媽現在很難輕易喜歡一件衣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