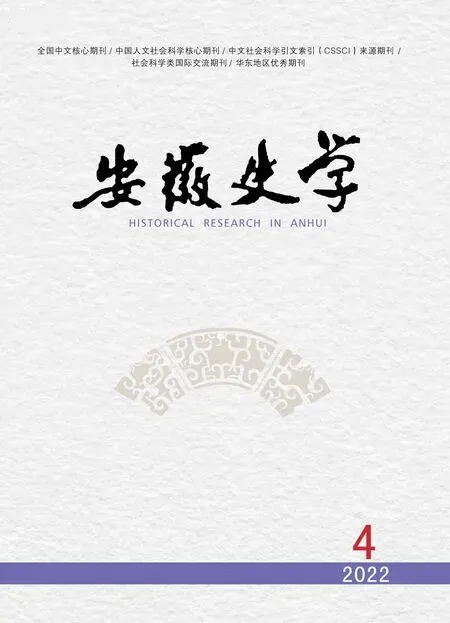元代路級官府首領官考論
薛 磊
(南開大學 歷史學院,天津 300350)
元代路總管府的官員可分為正官和首領官。達魯花赤、總管、同知、治中、判官、推官,屬于長貳正官;經(jīng)歷、知事、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fā)架閣,則屬于首領官,亦常被稱為“案牘官”“幕職官”。總領文職吏員以及案牘事務,是諸路首領官的基本職掌,“國朝之制,各路設首領官三員,總領六曹,職掌案牘,謂之賓幕”。(1)鄭玉:《師山集》卷3《送鄭照磨之南安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7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23頁。
路級是元代管民官府的最高層級,地位的重要性顯而易見。在路級官府的行政運作中,首領官的地位不容忽視。元代文人楊維楨甚至感嘆,“郡不得良二千石,幸而得一良經(jīng)歷,郡可治”。(2)楊維楨:《東維子文集》卷4《李經(jīng)歷治績序》,《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書店1989年影印本。有關元代首領官以及路總管府已有整體性的研究成果(3)許凡:《元代的首領官》,《西北師大學報》1983年第2期;張金銑:《元代路總管府的建立及其制度》,《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3期;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626—694頁。,但具體到路級官府的首領官,未見有專門討論。本文擬著重探討諸路首領官的制度起源、員額、印信、銓選等問題,并以黑水城漢文文獻為基礎分析首領官在路級官府運作中的地位。
一、路首領官制度溯源
元代路級官府大體是因襲和變通金代路總管府而來。(4)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第626頁。不過,金代路總管府的案牘事務由三名正官分領(5)《金史》卷57《百官志三》,中華書局2020年版,第1396頁。,元代路首領官的設置較多受到蒙古國時期漢世侯路制以及十路征收課稅所的影響。
蒙古國時期的漢世侯路制雜糅了行省、萬戶、兵馬都總管、都元帥等金朝官制的內(nèi)容。(6)張金銑:《元代路總管府的建立及其制度》,《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3期;王颋:《龍庭崇汗——元代政治史研究》,南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146頁。統(tǒng)領一路的漢世侯大多重視延請儒士擔任幕僚,部分幕僚的頭銜有“知事、經(jīng)歷、掌書記、書記等職”。(7)趙琦:《金元之際的儒士與漢文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84—85頁。雖然出現(xiàn)了經(jīng)歷、知事的名稱,但相關幕僚的頭銜是非常混亂和不規(guī)范的。
太宗窩闊臺汗二年十一月蒙古朝廷在漢地設置了十路征收課稅所。(8)《元史》卷2《太宗本紀》,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30頁。蒙廷只是直接任命了十路征收課稅所的正副長官,下屬官吏的人選多由課稅使決定,“凡佐吏,許自辟以從”。(9)蘇天爵輯撰、姚景安點校:《元朝名臣事略》卷13《廉訪使楊文憲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258頁。當時十路征收課稅所的幕僚多為經(jīng)歷、知事等。(10)趙琦:《金元之際的儒士與漢文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84—85頁。例如,邢州人馬亨先后擔任過真定路課稅所的掾史、知事、經(jīng)歷、副使等職。(11)《元史》卷163《馬亨傳》,第3826—3827頁。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重建路制,實行兵民分治,“始罷諸侯世守,立遷轉(zhuǎn)法”。(12)《元史》卷5《世祖本紀二》,第89、101頁。就首領官的設置而言,蒙古國時期的漢世侯路制和十路征收課稅所均對元世祖朝新建的路總管府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經(jīng)歷、知事等固定成為路總管府首領官的名稱;其二,保舉是元世祖朝初期諸路首領官選任的一個重要途徑。例如,自蒙古國時期開始濟南人王忱便是當?shù)厥篮顝埡甑哪涣牛雷嬷猎陱埡贽D(zhuǎn)任真定路總管,任命王忱擔任“知事,偕往”。(13)劉敏中著,鄧瑞全、謝輝校點:《劉敏中集》卷9《濟南王氏先德碑銘》,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112頁;張建彬:《大蒙古國時期的濟南張氏》,《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至元二年保定世侯張柔之子張弘范擔任大名路總管,征召阮某“充幕”。(14)任士林:《松鄉(xiāng)集》卷3《經(jīng)歷阮公墓志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6冊,第537頁;《元史》卷156《張弘范傳》,第3680頁。
至元五年王惲在擔任監(jiān)察御史后,向朝廷建言“選參佐”之法。“近聞朝省選用隨路總管,其法甚妙,然參佐尤當精擇。所謂掌司經(jīng)歷者,務要識大體,有議論,通案牘”。王惲認為至元二年“隨路總管許令帶行參佐二員”的規(guī)定會有結黨營私之弊,建議路總管保舉之人“交相為用,如真定府尹所保,用之保定,保定所保,用之他路之類是也”。(15)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90《選參佐》,《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2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460頁。這里的“參佐”,主要是指路首領官。此后,伴隨著朝廷選官制度的完善,保舉不再是諸路首領官選任的主要途徑。
二、路首領官的設置及其印信
《元史·百官志》僅載有諸路首領官的名稱和員額:經(jīng)歷一員,知事一員或二員,照磨兼承發(fā)架閣一員。(16)《元史》卷91《百官志七》,第2316頁。這一記載過于簡略,本文擬做三點補充。
其一,諸路首領官的品級。按《元典章》,諸路經(jīng)歷,從七品;知事,從八品。(17)陳高華等點校:《元典章》卷7《吏部一·職品·內(nèi)外文武職品》,中華書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13、219頁。根據(jù)大德十年中書省的咨文,諸路原設提控案牘一員,沒有品級。鑒于當時“到任正從九品員多,不能遷調(diào)”,經(jīng)吏部呈請,將諸路“提控案牘”改為“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fā)架閣”,由中書省“敕牒”任命,“給降從九品印信”。(18)陳高華等點校:《元典章》卷9《吏部三·首領官·敕牒提控案牘》,第 358—359頁。據(jù)此,大德十年諸路“提控案牘”改稱“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fā)架閣”,升為從九品。高仁曾指出《元史·百官志》將“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fā)架閣”的官稱誤記為“照磨兼承發(fā)架閣”(19)高仁:《〈元史·百官志〉“照磨兼承發(fā)架閣”釋誤》,《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32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91—194頁。,當確。“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fā)架閣”常被簡稱為“照磨”,鄭玉也提及諸路“照磨,初名提控案牘,行省版授。后改兼照磨承發(fā)架閣,乃命于朝,列第九品”。(20)鄭玉:《師山集》卷3《送鄭照磨之南安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7冊,第23頁。
其二,元世祖朝諸路首領官的員額,有過從三員到兩員再到三員的變化。對此,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兩篇事狀中留下了蛛絲馬跡,撰寫時間為至元五年到九年王惲擔任御史臺監(jiān)察御史期間。《彈大興府擅注案牘官事狀》:“今照得,隨路總管府元設提領案牘官已是罷去。今體察得:大興府卻將司吏韓仲禮充案牘官勾當。”(21)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89《彈大興府擅注案牘官事狀》,《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2冊,第451頁。據(jù)此,世祖初年,元廷廢罷了諸路“提領案牘官”。至元五年中書省公文載:“近為隨路所設經(jīng)歷、知事,職掌案牘,照領一切公事。”(22)陳高華等點校:《元典章》卷13《吏部七·公事·首領官執(zhí)復不從許直申部》,第509頁。可見,此時諸路首領官僅有兩員,即經(jīng)歷和知事。
至元八年二月,朝廷將諸路轉(zhuǎn)運司并入諸路總管府(23)《元史》卷7《世祖本紀四》,第133頁。,此后不久,諸路首領官又增設提控案牘一員。按《為運司并入總管府選添官吏事狀》,諸轉(zhuǎn)運司、奧魯總管府并入諸路總管府后,路總管府職掌事務劇增,王惲建言增加路府州縣正官和首領官的員額(24)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85《為運司并入總管府選添官吏事狀》,《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2冊,第406頁。,此建言應該被朝廷采納。至元十九年,又明確了提控案牘的級別,“凡總府續(xù)置提控案牘,多系入仕年深,似比巡檢例同考滿轉(zhuǎn)入從九”(25)《元史》卷82《選舉志二》,第2046頁。,此處“總府”當指路總官府。
其三,如何理解《元史·百官志》所載諸路“知事一員或二員”?筆者認為,一般來講,諸路知事為一員,二員實屬特例。筆者所見,元代僅有大都路(26)《元史》卷90《百官志六》,第2300頁。以及江浙行省平江路、腹里真定路設置過二員知事。如至大三年七月《江浙尚書省札付碑》、至正二十一年《平江路總管周侯興學記》兩塊碑刻題名中有兩員平江路知事;(27)《江浙尚書省札付碑》,《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49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頁;《江蘇省通志稿》金石24《平江路總管周侯興學記》,《歷代石刻史料匯編》第12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149頁。元代中后期四塊真定路碑刻題名中均有兩員真定路知事。(28)《常山貞石志》卷19《真定府增修廟學記》,《歷代石刻史料匯編》第13冊,第315頁;卷20《真定新建府署記》《真定路加葺宣圣廟碑》,第331、343頁;卷22《真定路學樂戶記》,第374頁。三路設有兩員知事應該與所轄民戶眾多有關,平江路的戶口數(shù)為全國各路之冠(29)孟繁清、楊淑紅:《元代平江路的人口發(fā)展——元代海運基地系列研究之一》,《元代文獻與文化研究》第2輯,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120—130頁。,真定路的戶口數(shù)在腹里地區(qū)僅次于大都路。(30)劉春燕:《元代真定路經(jīng)濟研究》,河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0年,第5—6頁。
路級官府三員首領官中的經(jīng)歷和照磨,均持有中書省禮部鑄造和頒發(fā)的官印,諸路“經(jīng)歷,今出吏部選,用七品印章”。(31)楊維楨:《東維子文集》卷4《李經(jīng)歷治績序》。湖北省荊門市出土過一方至元十四年“中書吏禮部”鑄造的“峽州路總管府經(jīng)歷司印”。(32)劉祖信:《荊門出土的元代八思巴印試析》,《江漢考古》1987年4期。1981年河北赤城縣出土過一方延祐二年七月中書省禮部鑄造的“云需總管府經(jīng)歷司印”。(33)王國榮:《河北赤城縣博物館藏印簡介》,《文物》1995年9期。大德十年以后,諸路照磨“給降從九品印信”。鄭玉言:諸路照磨“兼領對同承發(fā)檢舉勾銷,與夫圖籍之所藏、案牘之所庋,別有印章”(34)鄭玉:《師山集》卷3《送鄭照磨之南安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7冊,第23頁。,兼領官方文書最初的處理和最后的流轉(zhuǎn)、儲存,應該是照磨“別有印章”的主要原因。
地位介于經(jīng)歷和照磨之間的知事,是否擁有官印呢?筆者認為知事應該沒有官印。按《至正金陵新志》,元順帝至正年間的集慶路,“經(jīng)歷司,有印,經(jīng)歷一員;知事一員;提控案牘兼管勾照磨承發(fā)架閣一員,有印”。(35)張鉉:《至正金陵新志》卷6上《官守志一》,《宋元方志叢刊》第6冊,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5588頁。
由此可見,照磨印的使用范圍僅限于對案牘承發(fā)、架閣等的日常處理;而經(jīng)歷持印,反映出其在首領官群體中的主導地位。
三、路首領官的銓選
元世祖朝以后的路首領官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幕職,名為幕職,實為佐官。元人認為諸路首領官銓選與管民正官相同:“經(jīng)歷,今出吏部選,用七品印章……朝廷慎其選,與守令同,以廉明者有操尚者居之”(36)楊維楨:《東維子文集》卷4《李經(jīng)歷治績序》。,“夫知事,八品官爾,其任與三品等”。(37)程鉅夫著、張文澍校點:《程鉅夫集》卷15《送云伯讓序》,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頁。
為更詳細了解元代路首領官的銓選,筆者統(tǒng)計了一些具體個案。篇幅所限,僅統(tǒng)計了曾在江浙行省任首領官者的前職與遷轉(zhuǎn)職均較為明確的銓選個案,包括15名經(jīng)歷、10名知事、5名照磨,參見表1、表2、表3。
據(jù)表1、表2、表3,將江浙行省諸路首領官的前職與遷轉(zhuǎn)職簡單歸納如下:15名經(jīng)歷中,6名的前職曾任高層衙門吏員、4名為管民正官、5名為首領官;3名遷轉(zhuǎn)職為高層衙門吏員、8名為管民正官、3名任首領官、1名任場務官。10名知事中,4名前職為高層衙門吏員、1名為管民正官、2名為首領官、3名為儒學教官;2名遷轉(zhuǎn)職為高層衙門吏員、5名為管民正官、3名為首領官。5名照磨中,4名前職為高層衙門吏員、1名為場務官;3名遷轉(zhuǎn)職為高層衙門吏員、1名任管民正官、1名任場務官。由此可見,高層衙門吏員、管民正官、首領官是諸路首領官選任與遷轉(zhuǎn)的主要途徑。

表1 江浙行省諸路經(jīng)歷銓選表

表2 江浙行省諸路知事銓選表

表3 江浙行省諸路照磨銓選表
高層衙門吏員是指中書省、行中書省、宣慰司、肅政廉訪司等衙門的案牘吏員。在諸路首領官的前職與遷轉(zhuǎn)職中,高層衙門吏員占有很高的比例。從世祖朝開始,中書省、行中書省等高層衙門的吏員就可以直接從文資職官中選取。(38)陳高華等點校:《元典章》卷12《吏部六·儒吏·隨路歲貢儒吏》,第424頁。不少高層衙門的吏員來自有資品的官員。例如,中書省掾,正、從七品文資流官內(nèi)選取;行省令史,正、從八品文資流官內(nèi)選取;宣慰司令史,正、從九品文資流官內(nèi)選取。(39)陳高華等點校:《元典章》卷12《吏部六·職官吏員·職官補充吏員、選取職官令史》,第446—449頁。
諸路經(jīng)歷的來源,下縣的縣尹占有一定比例。下縣的縣尹和路經(jīng)歷雖均為從七品,但下縣縣尹遷轉(zhuǎn)為路經(jīng)歷,而路經(jīng)歷可以遷轉(zhuǎn)為正七品的中縣縣尹。(40)縣尹的品級,參見《元史》卷91《百官志七》,第2318頁。例如,元代中期左祥先后擔任廣州路香山縣尹、潮州路經(jīng)歷、廣州路增城縣尹。香山縣為下縣,增城縣為中縣。(41)揭傒斯著、李夢生標校:《揭傒斯全集·文集》卷5《增城三皇廟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52頁;《元史》卷62《地理志五》,第1515頁。因此,路經(jīng)歷的地位大致介于下縣縣尹與中縣縣尹之間。
首領官系統(tǒng)內(nèi)的遷轉(zhuǎn)可以橫跨不同類別的衙署,并不局限于牧民官府。根據(jù)筆者的統(tǒng)計來看,行省、宣慰司、肅政廉訪司、都轉(zhuǎn)運司、萬戶府等衙署的首領官均可以與路首領官互相遷轉(zhuǎn)。少數(shù)儒學教官、場務官也可與諸路首領官互相遷轉(zhuǎn)。儒學教官通過擔任諸路首領官可以進入管民官序列,有利于牧民官府官員素質(zhì)的提高。需要注意的是,可以與諸路首領官互相遷轉(zhuǎn)的場務官雖是雜職官,但一般并非雜職出身。諸路首領官屬于流官序列(42)馬祖常著、王媛校點:《馬祖常集》卷7《建白一十五事》,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70頁。,場務官、倉庫官等出身的雜職官一般不能夠擔任流官,流官卻可以出任雜職,任回,可以繼續(xù)在流官系統(tǒng)內(nèi)遷轉(zhuǎn)。(43)關于元代的雜職官,可參閱關樹東:《金代的雜班官與元代的雜職官》,《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62—278頁。
綜上,諸路首領官的前職與遷轉(zhuǎn)職涉及到高層衙門吏員、管民正官、首領官、儒學教官、場務官等多個系統(tǒng),說明首領官是不同類別衙署官吏互相遷轉(zhuǎn)的一個重要媒介。
四、首領官與路級官府運作
李治安將首領官在路級官府中的獨特作用,歸納為擬寫案牘、參與“圓議”、越級申訴等三個方面。同時,經(jīng)歷之所以處于路總管府運作的樞要地位,與路總管府官員多而又集體決策有關。(44)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第636—637、643—644頁。以下擬以黑水城出土元代亦集乃路漢文文獻為基礎,對首領官在路級官府運作中的地位做進一步的分析。
目前所見元代黑水城漢文文獻中有一部分是亦集乃路吏員和首領官共同押署的文書,日本學者赤木崇敏將其歸為“案呈”類文書,并認為“至少在元代的地方官府中,所謂‘案呈’,就是胥吏收到其他官府或官員發(fā)來的文書后,經(jīng)過調(diào)查,然后將應該采取的措施及需要文書行移的相關官府、相關人員開列出來,然后送至上司的文書草案”。(45)[日]赤木崇敏:《黑水城漢文文書所見的元代公文書的事務處理程序》,黃正建主編:《中國古文書學研究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43、237頁。對此類文書的理解,筆者略有不同看法,文書最后的押署是三名首領官,當是首領官呈送給路級官府的公文,而非吏員呈送,首領官也并非僅僅是“要確認文書程序是否符合規(guī)定,并作為責任者署名”。(46)[日]赤木崇敏:《黑水城漢文文書所見的元代公文書的事務處理程序》,黃正建主編:《中國古文書學研究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43、237頁。從首領官與路級官府運作的角度,還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對此類文書做進一步的解讀。
首先,首領官呈送的草案是路級官府運作的必要環(huán)節(jié)。《至順鎮(zhèn)江志》載,元代諸路政務“事無巨細,承吏率先抱案,以白首領官詳閱,義可,然后書擬,路官乃署押施行。”(47)楊積慶、賈秀英、蔣文野、笪遠毅校點:《至順鎮(zhèn)江志》卷15《參佐》,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04頁。據(jù)此,路級案牘的處理程序如下:第一步吏員送案牘給首領官“詳閱”;第二步首領官審議案牘;第三步吏員根據(jù)首領官的意見“書擬”案牘;第四步正官“署押”。黑水城文書中由首領官吏押署的“案呈”類文書當是上述路級案牘處理程序中的第三個環(huán)節(jié)。
元代黑水城“案呈”類文書說明首領官處理的案牘草案也需要存檔,隨時接受監(jiān)察機構的核查即“照刷”。例如,黑水城《大德四年軍用錢糧文卷》由兩部分組成,第1到32行的兩張紙為文卷本體,第33行以后為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司的刷尾紙。(48)孫繼民:《黑水城文獻所見元代肅政廉訪司“刷尾”工作流程》,《南京師大學報》2012年第5期;杜立暉、陳瑞青、朱建路:《黑水城元代漢文軍政文書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64—165頁。文卷本體部分的最后由府吏、提控案牘、知事、經(jīng)歷分別押署,第二部分的最后有“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司刷訖”長條形墨印以及“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司分司印”方形朱印。(49)錄文參見杜立暉、陳瑞青、朱建路:《黑水城元代漢文軍政文書研究》,第159—174頁;圖版參見塔拉、杜建錄、高國祥主編:《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版,第397—401頁。另一則由首領官吏押署的《至順元年河渠司官為糜粟蠶麥收成事呈狀》也能說明問題(50)錄文參見[日]赤木崇敏:《黑水城漢文文書所見的元代公文書的事務處理程序》,黃正建主編:《中國古文書學研究初編》,第233—235頁;圖版參見《俄藏黑水城文獻》(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16—318頁。,文書背部有“至順元年/辰字貳號”字樣,張國旺認為此當為一份檔案,以辰字貳號來編號保存。(51)張國旺:《黑水城出土〈至順元年亦集乃路總管府辰字貳號文卷為蠶麥秋田收成事〉釋補》,黃正建主編:《中國古文書學研究初編》,第225頁。
路級正官處理案牘時需要參考首領官的“案呈”意見。早在元世祖朝,諸路首領官就被賦予了越過正官,直申省部的權力。按至元五年中書省札付,“今后隨路總管府凡有一切所行公事,若有府官所見不同,處決偏枉,如經(jīng)歷、知事從正執(zhí)復,三次不從,令經(jīng)歷司官具由直行申部,詳究定奪。”(52)陳高華等點校:《元典章》卷13《吏部七·公事·首領官執(zhí)復不從許直申部》,第509頁。《至順鎮(zhèn)江志》在談及諸路首領官職掌時也有類似記載:“路官所見或異,則聽首領官。庭口再三弗從,則又許疏其事,申之省幕若部。”(53)楊積慶、賈秀英、蔣文野、笪遠毅校點:《至順鎮(zhèn)江志》卷15《參佐》,第604頁。
其次,從黑水城“案呈”類文書可以看出,三名首領官都需要押署。與路級正官共同署事相類似,首領官群體也要共議案牘。照磨地位最低,但卻是首領官審議案牘的第一個環(huán)節(jié),“令甲凡在外,諸司署牘皆自下而上。故一路之事必自照磨始,照磨以為可,則署而呈之府,然后行之州縣。照磨以為不可,則格不得行。故一郡之休戚,眾務之得失,在于照磨一署之頃。”(54)鄭玉:《師山集》卷3《送鄭照磨之南安序》,《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7冊,第23頁。知事是首領官審議案牘的第二個環(huán)節(jié),譚清叔為平江路知事,“于幕員在經(jīng)歷左,然吏抱牘進,不涉其筆,長不敢先事。故府中事無巨細,得持可否。”(55)楊維楨:《東維子文集》卷3《送譚知事赴河南省掾序》。經(jīng)歷則對呈送給長貳正官的案牘處理意見有最后的審定權,“贊協(xié)治體,責任非輕”。大德十年,中書省吏部建議將路經(jīng)歷的品級提升到正七品,雖最終未被采納,卻反映出吏部對路經(jīng)歷的重視。(56)陳高華等點校:《元典章》卷9《吏部三·首領官·敕牒提控案牘》,第 358—359頁。
路級官府首領官在處理案牘過程中,首先會對案牘處理進行協(xié)商,達成一致意見,而后由吏員草擬正式的草案,首領官吏再依次押署。正如《至順鎮(zhèn)江志》所載,“承吏率先抱案,以白首領官詳閱,義可,然后書擬。”黑水城“案呈”類文書實際上是首領官層級處理案牘的正式文書,《至元五年軍政文卷》是由首領官吏押署的“案呈”類文書(57)孫繼民等:《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746—748頁;[日]赤木崇敏:《黑水城漢文文書所見的元代公文書的事務處理程序》,黃正建主編:《中國古文書學研究初編》,第239頁;塔拉、杜建錄、高國祥主編:《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五),第1005—1008頁。,公文第18行“廿九日”上所鈐朱印為“亦集乃路總管府印”(58)照那斯圖、薛磊:《元國書官印匯釋》,遼寧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192—193頁。,由此也可以看出此為官府正式存檔文書。
余 論
不同于宋代諸路監(jiān)司分割事權、互相牽制,元代路級官府則是事權較為完整、集體負責。元代首領官地位提高,使得路級流內(nèi)品官的數(shù)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行政效率,即便是地位最低的照磨,對路級事務都有一定程度的決定權。元代首領官之所以受到重視,與蒙元朝廷重視案牘官的傳統(tǒng)有關,正如元人戴良所言,“國家置官,內(nèi)而朝廷,外而方面,皆為之設幕府以廣其贊助。”(59)戴良著,李軍、施賢明校點:《九靈山房集》卷13《送馮員外序》,《戴良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44頁。
元廷強化諸路首領官的作用當是為了集思廣益,防范正官擅權。但在路級官府的實際運作中,首領官制衡正官的作用亦不應被夸大。由于品級有別,首領官主動迎合正官意見,是雙方關系的常態(tài)。首領官與正官分庭抗禮的少數(shù)個案,正因為其特殊性才被文獻記錄。例如,元代中期寶慶路知事陳恕可“惟執(zhí)律令治文書,不阿上官,人服其操”。(60)陳旅:《安雅堂集》卷12《陳如心墓志銘》,《元代珍本文集匯刊》本,第526頁。對此,元朝后期士人楊維楨亦有評論,“余閱郡經(jīng)歷凡若干人,往往陷于隨而不立”。(61)楊維楨:《東維子文集》卷4《李經(jīng)歷治績序》。
元廷重視路首領官的銓選,尤其是經(jīng)歷選任的重要性類似于縣令,“方今親民與參佐官,莫縣令、經(jīng)歷為重。縣令乃百姓師帥,師帥賢則德澤宣;參署為一路紀綱,紀綱振則政務舉。”(62)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35《上世祖皇帝論政事書》,《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1冊,第486頁。正因為此,諸路首領官的整體素質(zhì)亦較高,“今天子,既申明守令之制,而尤重幕元僚之選,選必以廉靖有風才者居之。……奔競者往往爭入其選以利轉(zhuǎn)階之速,而不知司選者其如此,才而賢者升,而不才不賢者其黜多矣。”(63)楊維楨:《東維子文集》卷4《送孔漢臣之邵武經(jīng)歷序》。
元代中期大臣馬祖常認為,“行省所差府州司縣提控案牘、都吏、吏目、典史之徒,往往恃其名役之細微,縱其奸猾,舞文弄法,操制官長,傾詐庶民”,建議朝廷廢罷府州縣以及錄事司的首領官,改由正官兼領案牘。在馬祖常看來,被納入朝廷流內(nèi)品官系統(tǒng)的諸路首領官可以繼續(xù)保留。(64)馬祖常著、王媛校點:《馬祖常集》卷7《建白一十五事》,第170頁。
元朝后期為加強對漢地民眾的防范,朝廷甚至出臺了只能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擔任重要衙署“幕官之長”的詔令。元順帝至元三年四月詔:“省、院、臺、部、宣慰司、廉訪司及郡府幕官之長,并用蒙古、色目人”(65)《元史》卷39《順帝本紀二》,第839頁。,此處“郡府幕官之長”指的是路經(jīng)歷。這一詔令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幕職官的重要性。
明代府級官府沿襲了元代諸路首領官的建置(66)《明史》卷75《職官志四》,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849頁。,明代前期諸府首領官亦可與正官分庭抗禮。(67)陶安:《陶學士集》卷12《送經(jīng)歷張景中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5冊,第728頁。由于缺乏長官的信任以及科舉制下幕職威權的下降,明代幕屬官(首領官)地位逐漸下降,職責漸為長官私人聘請的幕賓所取代。(68)陳寶良:《明代幕官制度初探》,《中州學刊》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