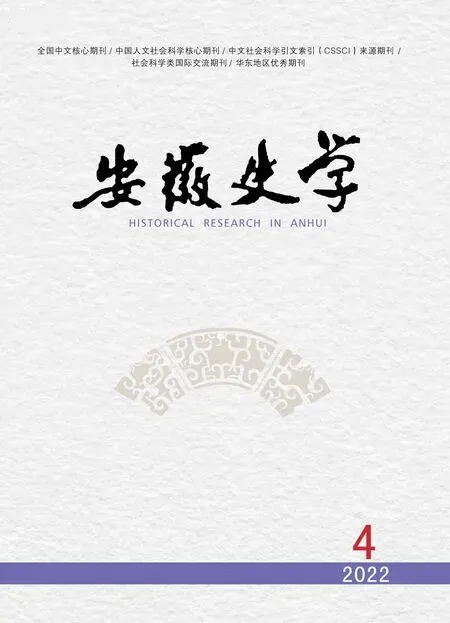清代錢價(jià)奏報(bào)考論
趙士第
(武漢大學(xué) 歷史學(xué)院,湖北 武漢 430072)
明清易代后,清廷著力恢復(fù)失序混亂的錢法制度,在清中葉重整銅錢體制(1)參見邱永志、張國坤:《明清銅錢流通體制的式微與重整》,《重慶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21年第1期。,已成為學(xué)界公認(rèn)的事實(shí)。從銅錢鑄造層面講,清朝積極進(jìn)口洋銅并開發(fā)西南礦業(yè),各省逐開鑄局,極大增加了鑄錢量。從貨幣流通層面講,清朝行錢之地較明代大大擴(kuò)展,良幣在市場行用較充足,并出現(xiàn)“良幣驅(qū)逐劣幣”現(xiàn)象。(2)可參見劉朝輝:《清代制錢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tài)》2008年第7期;王德泰:《清代前期錢幣制度形態(tài)研究》,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13年版;張寧:《15—19世紀(jì)中國貨幣流通變革研究》,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18年版。清朝錢法比起前代更為完善,中央通過掌握地方“錢價(jià)”(3)在一些奏報(bào)中也稱銀價(jià)奏報(bào),實(shí)則就是銀錢比價(jià),為方便起見,本文統(tǒng)稱為錢價(jià)。信息,制定相應(yīng)的貨幣政策。
清代奏折制度的產(chǎn)生使得皇帝更能迅速控制和了解地方,其肇始于康熙,發(fā)展于雍正,成熟于乾隆,清末還發(fā)揮著相應(yīng)的作用。而錢價(jià)奏報(bào),也伴隨著奏折制度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而來,卻多被學(xué)界所忽視。學(xué)術(shù)界關(guān)于清代奏報(bào)的研究,除錢糧稅收奏報(bào)外,多致力于糧價(jià)、雨澤和災(zāi)害奏報(bào)的研究(4)可參見朱琳:《回顧與思考:清代糧價(jià)問題研究綜述》,《農(nóng)業(yè)考古》2013年第4期;劉炳濤:《清代雨澤奏報(bào)制度》,《歷史檔案》2017年第2期;李伯重:《信息收集與國家治理:清代的荒政信息收集系統(tǒng)》,《首都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22年第1期。,本文擬以清代檔案、省例等資料為基礎(chǔ),對清代錢價(jià)奏報(bào)做一考證,不足之處,請方家指教。
一、清代錢價(jià)奏報(bào)的形成、發(fā)展與定型
(一)錢價(jià)奏報(bào)的形成
“錢價(jià)”即一兩白銀兌換銅錢的價(jià)格。明中期以降,已經(jīng)形成“銀錢并行”的貨幣流通格局,為明確各地銀錢比價(jià),開始出現(xiàn)陳報(bào)錢價(jià)信息。如成化十五年六月,戴瑤陳言:“南京錢價(jià),每銀一錢止易七十余文”。(5)《明憲宗實(shí)錄》卷191,成化十五年六月辛卯,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3394頁。萬歷以后,幾乎每年皆有內(nèi)閣成員、戶部官員甚至平民陳報(bào)京師錢價(jià)。(6)參見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pp.106-109.但明代對錢價(jià)的陳報(bào)未形成定制,陳報(bào)者的身份不定,所陳地區(qū)以人口眾多和經(jīng)濟(jì)、稅收發(fā)達(dá)的兩京及各鈔關(guān)為主,未遍及全國范圍。
清朝立國以來,著力恢復(fù)錢法。由于前代舊錢、民間私鑄小錢過多,加上白銀流入量的減少,順治時(shí)期出現(xiàn)“銀貴錢賤”狀態(tài)。與此同時(shí),零星的錢價(jià)奏報(bào)也已出現(xiàn),如順治八年戶部尚書巴哈納指出:“街市使錢,每銀一錢至一百四十文以外,殊屬違制……今錢價(jià)日賤,制錢日壅”。(7)《巴哈納題疏通錢法事本》,順治八年正月二十七日,《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7輯,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69—170頁。但此時(shí)的錢價(jià)奏報(bào)多是根據(jù)實(shí)際需求上報(bào),而非一種常規(guī)。
康熙初年官錢質(zhì)量得到改善(8)葉夢珠提到康熙通寶“體重工良”,葉夢珠:《閱世編》卷7《錢法》,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94頁。,“錢用日廣,錢價(jià)漸昂”(9)《清朝續(xù)文獻(xiàn)通考》卷20《錢幣二》,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36年版,第7696頁。,市場急需質(zhì)量好的銅錢,但隨著臺灣鄭氏集團(tuán)對東南地區(qū)的侵?jǐn)_阻礙洋銅進(jìn)口及吳三桂占據(jù)云南阻止滇銅開發(fā),使得銅料供應(yīng)短缺,嚴(yán)重影響了銅錢的鼓鑄,優(yōu)質(zhì)銅錢供應(yīng)不足,呈現(xiàn) “錢貴銀賤”現(xiàn)象。康熙中期制錢流通的問題日益暴露,如康熙二十三年管理錢法侍郎陳廷敬等疏言:“錢日少而貴者,皆由奸宄不法之徒毀錢作銅牟利所致。”(10)《清圣祖實(shí)錄》卷116,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丙寅,《清實(shí)錄》第5冊,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13頁。皇帝需要了解全國各地尤其是重要城市的錢價(jià),以便及時(shí)采取措施,維持社會穩(wěn)定。
同時(shí),奏折制度的產(chǎn)生,為皇帝及時(shí)掌握地方實(shí)情提供了便利。隨著雨雪糧價(jià)奏報(bào)制度的確立,錢價(jià)也基本上附于雨雪糧價(jià)之后奏報(bào),如康熙四十五年江西巡撫郎廷極在奏陳雨雪糧價(jià)后提及錢法一項(xiàng),“江西民間行使俱系局鑄官錢,每錢一千文值銀一兩,并無私錢攙和,亦無低價(jià)病民”。(11)《奏報(bào)江西省收成米價(jià)并民間使用錢幣系局鑄官錢無私錢攙和事》,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六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折件(以下簡稱“宮中檔”),文獻(xiàn)編號:401001995。最典型的當(dāng)屬杭州織造孫文成康熙四十五年、四十七年的奏報(bào),現(xiàn)舉一例:
直隸地方(糧價(jià)信息省略,下同)……一兩銀兌換寶泉錢……
山東地方……一兩銀可兌寶泉錢……
江寧地方……一兩銀可兌寶泉錢……
浙江地方……一兩四分銀可兌寶泉錢……(12)《奏報(bào)糧價(jià)并收成分?jǐn)?shù)折》,康熙四十五年七月十二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96年版,第439頁。
可見,此時(shí)的錢價(jià)奏報(bào)已有一定的格式。基本可以確定,康熙中后期,錢價(jià)奏報(bào)已成雛形,但具體的奏報(bào)章程還未固定。首先,具奏人身份可以是皇帝的心腹,也可以是地方督撫,甚至是皇室成員。(13)如皇子胤祉在巡訪后所上請安折內(nèi)奏報(bào)了高郵州、蘇州府、鎮(zhèn)江府糧價(jià)和錢價(jià)情形,參見《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第504頁。其次,奏報(bào)錢價(jià)涉及的范圍沒有統(tǒng)一的標(biāo)準(zhǔn),有的僅奏報(bào)通省錢價(jià),有的只奏報(bào)省城錢價(jià),有的奏報(bào)某一府的錢價(jià),有的甚至只談?wù)撳X價(jià)的貴賤卻不指出具體的地點(diǎn)和數(shù)目,形式也較為簡單。再次,錢價(jià)奏報(bào)并未形成旬報(bào)、月報(bào)、季報(bào)、年報(bào)之類的慣例。
(二)錢價(jià)奏報(bào)的發(fā)展與定型
雍正時(shí)期私銷制錢取銅十分嚴(yán)重,鋪戶、富戶、牙行等也大量囤積制錢獲利,如京師“錢牙經(jīng)紀(jì)或任意作奸,米鋪、茶行、雜貨等鋪囤錢不出”(14)《題請令戶部發(fā)給八旗五城錢局制錢收兌銀兩以平錢價(jià)事》,雍正九年四月十三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內(nèi)閣六科史書·戶科》第79冊,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7年版,第208頁。,從而導(dǎo)致市面錢價(jià)昂貴。為此,雍正朝施行最為嚴(yán)厲的銅禁政策的同時(shí),還積極開發(fā)滇銅鼓鑄。“改土歸流”后,滇銅開發(fā)提上日程,年產(chǎn)量達(dá)400萬斤。雍正七年以后,全國各省鑄局紛紛開爐,除京局外,共開設(shè)18個鑄局,許多以往不鑄錢的省份在雍正末期也開始鑄錢,鑄局?jǐn)?shù)量和鑄錢量遠(yuǎn)超康熙時(shí)期。
面對此種情形,清代的錢價(jià)奏報(bào)也繼續(xù)發(fā)展,并進(jìn)一步規(guī)范和完善。第一,奏報(bào)格式有一定的規(guī)范。除繼承康熙時(shí)期附在雨雪糧價(jià)后奏報(bào)外,書寫格式也開始統(tǒng)一,即需清晰羅列各府錢價(jià)的具體數(shù)目。如雍正二年翰林院修撰于振奉旨赴河南主持鄉(xiāng)試,有奏報(bào)所見地方的雨雪、錢價(jià)、糧價(jià)等情,其中錢價(jià)一欄:“一錢價(jià),順德一帶每紋銀一兩換錢一千六百文至一千七百文不等,彰德一帶每紋銀一兩換錢一千八百五十文至一千九百文不等”。(15)《奏報(bào)典試河南途次及在省所見地方雨雪銀價(jià)糧價(jià)等情折》,雍正(二年),《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31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10頁。第二,奏報(bào)日期已有一定的章程。據(jù)現(xiàn)有的資料可知,部分州縣向道府奏報(bào)為月報(bào),如宛平、大興二縣需向順天府每月報(bào)備錢價(jià),“宛大兩縣每月申報(bào)錢價(jià)印文,五月紋銀一兩核錢八百四十文,六月止八百二十文矣”。(16)《奏陳平抑京師錢價(jià)管見折》,雍正元年七月六日,《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1冊,第627頁。部分督撫向皇帝奏報(bào)錢價(jià)多為年報(bào),如陜西巡撫史貽直在雍正十年至十三年連續(xù)四年奏報(bào)陜西當(dāng)?shù)劐X價(jià)情形。(17)《奏報(bào)米價(jià)錢價(jià)平減情形事》,雍正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朱批奏折(以下簡稱“朱批奏折”),檔號:03-0026-011;十一年見朱批奏折,檔號:04-01-30-0037-028;十二年見“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內(nèi)閣大庫檔案,登錄號:020536;十三年見《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24輯,臺北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1982年,第551頁。第三,奏報(bào)地域擴(kuò)展。除鼓鑄基地云南、京師及毗鄰皇城的州縣外,新開爐鼓鑄的省份也需要奏報(bào)錢價(jià)以證明開爐后對當(dāng)?shù)劂y錢比價(jià)的調(diào)控效果。而西北地區(qū)錢價(jià)奏報(bào)頻繁,主要是由于雍正時(shí)期西北大量用兵,兵餉發(fā)放以制錢為主。可見雍正時(shí)期的錢價(jià)奏報(bào)已逐漸趨于常態(tài)化。
乾隆時(shí)期從中央到地方完備的銅錢鼓鑄體系形成,京局和各省鑄局穩(wěn)定,制錢供給大量增加,乾隆朝的鑄幣量直抵1.5億貫,遠(yuǎn)超前代,行錢區(qū)域也不斷擴(kuò)大,很多地區(qū)以銀為單位逐漸轉(zhuǎn)化為以錢為單位,甚至新疆地區(qū)也流通制錢,貨幣流通格局發(fā)生變化。(18)張寧:《15—19世紀(jì)中國貨幣流通變革研究》,第131—132、151—164頁。為了解全國鼓鑄、銀錢比價(jià)和制錢行用等情形,各地錢價(jià)奏報(bào)已經(jīng)發(fā)展成熟,進(jìn)而推動了清代錢價(jià)奏報(bào)的定型和鼎盛。
乾隆五十一年,朝廷核準(zhǔn)復(fù)議督撫奏報(bào):“各省市換錢價(jià),漲落隨時(shí),行令將市換錢價(jià)有無增昂,按月查明,按季報(bào)部”(19)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220《戶部·錢法》,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3冊,第579頁。,但何時(shí)形成系統(tǒng)性尚難明確。《湖南省例成案》記錄的一則材料或可參照:乾隆五年以前湖南各府縣報(bào)雨雪糧價(jià)、錢價(jià)等信息,“有五日一報(bào),半月、十日一報(bào)者,俱不劃一”,而乾隆五年后,得以規(guī)范,“令各州縣仍不時(shí)具折通報(bào)外,其余閑月在州縣似可毋庸具折通報(bào)。……今擬以一月具報(bào)三次,初次定于每月初十日具折;二次、三次定于每月二十、三十日具折。……則司中于次月月半時(shí)可以匯折赍請核奏。”(20)《湖南省例成案·吏律公式》卷5《熱審減等及內(nèi)外結(jié)贓贖侵那銀兩刪繁就簡各條州縣晴雨米價(jià)值藩司匯總冊轉(zhuǎn)報(bào)》,清刻本,日本東京大學(xué)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第28b—29b頁。可見,乾隆初年,已將地方政府錢價(jià)奏報(bào)系統(tǒng)化。而目前可見乾隆時(shí)期最早的督撫定期錢價(jià)奏報(bào)是在乾隆八年。(21)如《呈湖北省武昌等府乾隆本年四月份糧價(jià)單》,乾隆八年閏四月,朱批奏折,檔號:04-01-39-0214-006;《奏報(bào)各屬雨水及晚禾暢茂并米價(jià)錢價(jià)情形事》,乾隆八年七月二十日,朱批奏折,檔號:04-01-22-0016-092。由此確定,清代錢價(jià)自州縣向省再至中央,層層規(guī)范奏報(bào)程序的確立大約在乾隆初期。
二、乾隆朝錢價(jià)奏報(bào)的方式、程序與格式
乾隆時(shí)期的錢價(jià)奏報(bào)方式,可分為常規(guī)奏報(bào)和不規(guī)則奏報(bào)兩種。所謂常規(guī)奏報(bào)是指有一定時(shí)間、一定程序和一定格式的報(bào)告,并且是由各級地方行政官吏層層上報(bào)的,最后由督撫等地方大員奏報(bào)皇帝。不規(guī)則奏報(bào)是指不拘格式、不限時(shí)間,也不限于是否為督撫等地方大員所奏報(bào)。奏報(bào)程序、格式也有一定的要求,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常規(guī)錢價(jià)奏報(bào)
常規(guī)奏報(bào)先由州縣承擔(dān)錢價(jià)奏報(bào)的戶房書吏繕寫。以福建為例,州縣“將應(yīng)辦糧價(jià),設(shè)立專書、專役,依時(shí)開折,務(wù)須確按市價(jià)……每兩銀換錢若干……據(jù)實(shí)開報(bào)”(22)《福建省例》(三),臺北大通書局1984年版,第119頁。,一般分為兩種,即旬報(bào)和月報(bào),折報(bào)有固定的格式要求,錢價(jià)折報(bào)一般附在糧價(jià)之后。福建兩例乾隆六十年的州縣月報(bào)、旬報(bào)折式可供參考:
月報(bào)折式
某府某縣為傳付事:遵將卑邑本年某月……紋銀各價(jià)值開具清折,稟報(bào)憲臺察核。須至稟折者。計(jì)開:
乾隆六十年某月分
……
制錢市銀(市平)(鏡面)(庫平) 每兩易錢若干
核稿某人 經(jīng)承某人 繕寫某人 差役某人(23)《福建省例》(三),第123、124、119、122頁。
旬報(bào)折式
……
乾隆六十年某月分上(中)(下)旬
……
制錢市銀(市平)(鏡面)(庫平) 每兩易錢若干
核稿某人 經(jīng)承某人 繕寫某人 差役某人(24)《福建省例》(三),第123、124、119、122頁。
折報(bào)至府一級,“一面由府(或直隸州)匯造,送司核辦。并令將何役周查,何吏造報(bào),署中何人核稿,何人繕寫,該官是否親閱各緣由稟報(bào)去后。”(25)《福建省例》(三),第123、124、119、122頁。各府除需要匯總各縣匯報(bào)的錢價(jià)信息外,還需要派人查詢匯報(bào)是否符合真實(shí)情形,將匯總情況造單填寫,連同各州縣的月、旬報(bào)等項(xiàng)一齊折報(bào)省布政使司,一般為月報(bào),折式幾乎與縣報(bào)相同。(26)《福建省例》(三),第123、124、119、122頁。
省布政使司將各府每月匯報(bào)的信息整合,匯編成一個綜合性全省錢價(jià)報(bào)告,進(jìn)呈總督及巡撫衙門,最后再由督撫上報(bào)皇帝,督撫陳報(bào)一般為月報(bào),也有旬報(bào)的情況。省一級的奏報(bào)方式更為復(fù)雜,基本存在四種文書格式,即清單、附片(夾片)、雨雪糧價(jià)附錢價(jià)奏報(bào)、單獨(dú)的錢價(jià)奏報(bào),其中屬于常規(guī)奏報(bào)者為錢價(jià)清單和雨雪糧價(jià)附錢價(jià)奏報(bào)。
錢價(jià)清單奏報(bào),是督撫直接以錢價(jià)為主題的奏報(bào),也有一定的格式和時(shí)間要求,以乾隆十七年九月十二日直隸總督所奏直省各府州屬查報(bào)八月下旬錢價(jià)清單為例:
順天府附京各屬每銀一兩換錢……文不等。……
永平府屬每銀一兩換錢……不等。
保定府屬每銀一兩換錢……不等。
河間府屬每銀一兩換錢……不等。……(27)《奏報(bào)直省各府州屬查報(bào)八月下旬錢價(jià)清單》,乾隆十七年九月十二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軍機(jī)處檔折件,文獻(xiàn)編號:009145。
可見,錢價(jià)清單是將每省各府每旬或每月的具體錢價(jià)數(shù)字羅列,格式固定,且內(nèi)容比較詳細(xì),如有特殊情況還應(yīng)具體說明。
而現(xiàn)存錢價(jià)檔案中較多的為雨雪糧價(jià)附錢價(jià)奏報(bào),大部分都有期限和格式要求。如乾隆十七年直隸總督奏折:“省城錢價(jià)每庫平銀一兩易錢九百六十文,庫紋每兩可換八百五十余文,各府州縣俱在八百以上九百數(shù)十文不等,較去冬更為平減。”(28)《奏報(bào)各屬報(bào)明出錢數(shù)錢價(jià)及雨水糧價(jià)折》,乾隆十七年十一月初九日,宮中檔,文獻(xiàn)編號:403002836。雨雪糧價(jià)附錢價(jià)奏報(bào)中,主要奏報(bào)省城錢價(jià),對各府縣錢價(jià)多概數(shù)匯報(bào),還要注明與往時(shí)的差異,當(dāng)然某些省份的奏報(bào)中會涉及各府錢價(jià)信息。(29)乾隆時(shí)期雨雪糧價(jià)附錢價(jià)奏報(bào)中已經(jīng)精確到府的數(shù)據(jù),以湖北最為典型,具體可參見胡岳峰:《清代銀錢比價(jià)波動研究(1644—1911)》,華東師范大學(xué)博士學(xué)位論文,2021年,第173頁。
(二)不規(guī)則錢價(jià)奏報(bào)
現(xiàn)存錢價(jià)奏報(bào)資料并不系統(tǒng),這與雨雪糧價(jià)的系統(tǒng)奏報(bào)差異甚大。彭凱翔認(rèn)為主要原因是“銀錢比價(jià)的上報(bào)并不順利,不少地方都難以及時(shí)獲得行市,或者漏報(bào),或者因循捏報(bào),地方官無力抽樣統(tǒng)計(jì),通常是牙行或經(jīng)紀(jì)提供行市,作為上報(bào)依據(jù),當(dāng)時(shí)多數(shù)地區(qū)銀錢交易尚屬零星、未形成專業(yè)市場。”(30)彭凱翔:《從交易到市場:傳統(tǒng)中國民間經(jīng)濟(jì)脈絡(luò)試探》,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頁。實(shí)際上除此原因外,很多省份的錢價(jià)信息是通過不規(guī)則奏報(bào)完成的,主要有以下五種形式:
一是錢價(jià)附片(夾片)奏報(bào),一般附著在其他奏折中。附片奏報(bào)多是不規(guī)則奏報(bào),乾隆四十三年湖南巡撫報(bào)中晚稻收成時(shí)指出:“附片:糧價(jià)錢價(jià)清單。錢價(jià)元寶銀一兩合制錢九百十七文,較上月少兌八文;俸祿銀一兩合制錢九百九文,較上月少兌八文。”(31)《奏報(bào)中晚稻收成分?jǐn)?shù)》,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軍機(jī)處檔折件,文獻(xiàn)編號:020999。可見,附片奏報(bào)內(nèi)容比較簡略,往往只涉及省城錢價(jià),且多附著在其他事務(wù)奏陳中。
二是單獨(dú)錢價(jià)奏報(bào)。督撫或其他官員專門的錢價(jià)奏報(bào)也是不規(guī)則奏報(bào)。該奏報(bào)內(nèi)容最為詳細(xì),并無固定格式和時(shí)間。就內(nèi)容而言,錢價(jià)信息是次要的,而有關(guān)錢價(jià)高低所引發(fā)的重大社會經(jīng)濟(jì)問題才是重點(diǎn)。如乾隆六年陜甘總督奏報(bào):
邇年來漸次缺少,現(xiàn)在省城每銀一兩易錢七百數(shù)十文,民用頗覺艱難,臣等再四籌畫,若遠(yuǎn)地搬運(yùn)腳價(jià)浩繁……臣等查此項(xiàng)收買銅斤原以供鼓鑄之用……當(dāng)此錢少價(jià)昂之時(shí),若將此銅鼓鑄錢資用以平市價(jià),利民之事莫切于此。(32)《奏為陜省錢價(jià)昂貴酌情動用舊鼓鑄銅錢文事》,乾隆六年七月初四日,朱批奏折,檔號:04-01-35-1232-005。
可見,單獨(dú)奏陳錢價(jià)奏折的內(nèi)容一般包括錢價(jià)情況、導(dǎo)致錢價(jià)不穩(wěn)的因素、擬解決的方案等三個要素,反映出各地督撫秉承上諭嚴(yán)查錢價(jià),重視錢法問題。
三是其他事務(wù)帶報(bào)錢價(jià)。除督撫單獨(dú)錢價(jià)奏報(bào)外,督撫題銷各省局鼓鑄奏銷時(shí)也多附有錢價(jià)記錄,在戶科題本中留存較多。非地方督撫的其他事務(wù)奏報(bào)帶報(bào)錢價(jià)也是錢價(jià)奏報(bào)系統(tǒng)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包括鹽法、河工、災(zāi)荒、俸餉工資、物價(jià)、賦役、鑄局奏銷、物料經(jīng)費(fèi)等內(nèi)容的奏折、題本、奏銷冊等。奏報(bào)者包括戶部官員、大學(xué)士、道御史、旗官、鹽官等,這些奏報(bào)具有明顯的靈活性和實(shí)用性。具體而言,戶部官員掌管全國錢法事宜,而大學(xué)士的奏報(bào)由于其兼理戶部事務(wù),需了解錢價(jià),與皇帝商議制定錢法政策;旗務(wù)官員包括八旗將軍、都統(tǒng)、參領(lǐng)等需要處理八旗俸餉問題,銀錢比價(jià)和八旗生計(jì)密切相關(guān);鹽官因鹽商交鹽稅用銀,百姓買鹽多用錢,故需要密切關(guān)注行鹽區(qū)的銀錢比價(jià),如長蘆、兩淮鹽區(qū)在鹽價(jià)奏報(bào)及處理鹽商問題中常提及行鹽區(qū)的銀錢比價(jià)。(33)如《奏為錢價(jià)平減運(yùn)本不敷懇請酌量加增以紓商力事》,乾隆三十五年三月初十日,朱批奏折,檔號:04-01-35-0464-028。此外,俸祿工資也提及錢價(jià),如乾隆六年貴州道監(jiān)察御史孫灝奏匠役工資時(shí)稱:“惟是民間貿(mào)易每銀一兩僅換錢八百三四十文不等”。(34)《奏請錢局匠役工資仍發(fā)錢文事》,乾隆六年九月初七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jī)處錄副奏折(以下簡稱“錄副奏折”),檔號:03-0769-030。
四是皇帝臨時(shí)委派專員專查錢價(jià)的奏報(bào),典型如刑部尚書多被皇帝臨時(shí)委派監(jiān)察京城錢價(jià)。(35)如刑部尚書英廉查京城錢價(jià),參見《奏報(bào)遵旨查拿倡言抬漲錢價(jià)之奸商事》,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初五日,錄副奏折,檔號:03-1421-007。同時(shí),監(jiān)察御史、給事中等也皆可受委派巡查各地錢價(jià),用于監(jiān)察及核對督撫所奏錢價(jià)情況是否屬實(shí)。
五是官員上任、進(jìn)京、出訪時(shí),需要匯報(bào)沿途或當(dāng)?shù)劐X價(jià)情形。這在乾隆朝時(shí)較為突出,如乾隆九年慧中署理陜西布政使,報(bào)告了赴任途中所見京師至西安主要地區(qū)的錢價(jià)情況。(36)《奏報(bào)自京到陜沿途各地苗情及米價(jià)錢價(jià)事》,乾隆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朱批奏折,檔號:04-01-22-0019-002。
綜上可知,乾隆朝錢價(jià)奏報(bào)有以下特征:第一,錢價(jià)奏報(bào)程序規(guī)范,即由州縣至府,府至布政使司,布政使司呈至督撫,督撫最后上奏皇帝。第二,府州縣錢價(jià)月(旬)報(bào)和清單的格式基本上固定,即詳列某府縣某月(旬)的銀錢兌換情況。第三,督撫奏報(bào)也有一定的規(guī)范,一般會采用錢價(jià)清單、雨雪糧價(jià)附錢價(jià)奏報(bào)的方式,列本省某月(旬)大體錢價(jià)或省城錢價(jià)或詳列本省各府錢價(jià),并指出與上月(上旬)增減變化情況。第四,不規(guī)則奏報(bào)不拘時(shí)間、形式、身份,方式靈活,是常規(guī)奏報(bào)的補(bǔ)充。
三、錢價(jià)奏報(bào)的地域擴(kuò)展及作用
(一)奏報(bào)地域的擴(kuò)展
乾隆時(shí)期錢價(jià)奏報(bào)的地域不斷擴(kuò)展,幾乎囊括全國范圍。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臺北故宮博物院、臺灣“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清代奏折、內(nèi)閣大庫檔案的題名目錄基礎(chǔ)上,以“錢價(jià)”“銀價(jià)”為檢索關(guān)鍵詞,粗略整理出239條錢價(jià)奏報(bào)檔案(37)清代留存錢價(jià)記錄的檔案較多,遠(yuǎn)遠(yuǎn)超出本文所統(tǒng)計(jì),限于條件只能對最典型的錢價(jià)奏報(bào)材料進(jìn)行分析。,繪制乾隆朝錢價(jià)奏報(bào)地域范圍及頻次圖如下:

圖1 乾隆時(shí)期錢價(jià)奏報(bào)頻次圖
可見,在乾隆時(shí)期,除吉林、黑龍江、蒙古、青海、西藏等地外,錢價(jià)奏報(bào)的范圍幾乎遍及全國。
錢價(jià)奏報(bào)頻率也是當(dāng)?shù)刎?cái)政運(yùn)作、經(jīng)濟(jì)發(fā)展甚至軍事情況的反映。如圖,頻率最多的地區(qū)是京畿所在的京師和直隸地區(qū)。其次是清朝賦稅重地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最為發(fā)達(dá)的蘇、浙、閩地區(qū),因當(dāng)時(shí)百姓繳納稅收和日常交易多用銅錢,銀錢比價(jià)直接影響著政府的稅收,所以必須嚴(yán)格掌握其錢價(jià)信息。且這些地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交易頻繁、價(jià)格信息透明,如江蘇“查兌錢雖有經(jīng)紀(jì)名色,出入悉照時(shí)價(jià),不能意為高下”。(38)《清高宗實(shí)錄》卷232,乾隆十年正月辛巳,《清實(shí)錄》第12冊,第4頁。再次是陜甘、新疆等西北地區(qū)及湖北等地。陜甘地區(qū)在乾隆以前是制錢極其匱乏地區(qū),常需要四川、云南等地的協(xié)濟(jì),且戰(zhàn)事較多,在陜西西安、漢中、潼關(guān)及甘肅涼州均有大量八旗駐防,乾隆十九年至二十六年“準(zhǔn)回之役”期間,國家每年需投放大量軍餉,而軍餉發(fā)放又以制錢為主。而新疆在乾隆時(shí)期平定準(zhǔn)噶爾和大小和卓叛亂之后被收復(fù),乾隆二十五年在葉爾羌設(shè)局鑄錢供給葉爾羌、喀什噶爾、和聞三城通用,阿克蘇局錢供“阿克蘇、烏什、庫車、喀喇沙爾、賽里木、拜城等七城所用”(39)宣統(tǒng)《新疆圖志》卷34《食貨三·銅幣二·阿克蘇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26頁。,乾隆三十年撤阿克蘇局改為烏什局,新制錢替代舊錢,錢價(jià)自然備受關(guān)注。而湖北尤其是江漢平原地區(qū)在清前期已成為重要的糧食貿(mào)易區(qū),“居流通過程之中間環(huán)節(jié),承上受川米輸入,啟下出米糧至江浙,具有中轉(zhuǎn)或集散市場的職能”(40)張建民:《“湖廣熟,天下足”述論——兼及明清時(shí)期長江沿岸的米糧流通》,《中國農(nóng)史》1987年第4期。,且荊州也是重要的八旗駐防地,錢價(jià)也受到關(guān)注。次之是湖南、江西、四川、山東、河南、廣西等地,這些地區(qū)大多在雍正后期才逐漸形成銅錢鼓鑄定額,市場上用銀較多,大多數(shù)地區(qū)難以形成錢市,如廣西“并無錢市,亦未設(shè)有經(jīng)紀(jì)……粵西鋪戶收買,俱系用銀,鄉(xiāng)民肩挑來城者,賣錢有限”。(41)《清高宗實(shí)錄》卷251,乾隆十年十月丁卯,《清實(shí)錄》第12冊,第248頁。最后是云貴和廣東地區(qū)。由于乾隆時(shí)期滇銅黔鉛的開發(fā),滇銅等幣材通過長江、運(yùn)河等運(yùn)往各地用于鼓鑄,全國制錢供給已不完全依賴云南,錢價(jià)奏報(bào)的重要性較康雍時(shí)期減弱,而廣東地區(qū)在乾隆時(shí)期已多行洋錢(42)《清文獻(xiàn)通考》卷16《錢幣四》,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36年版,第5002頁。,逐漸減少了對制錢的需求。而東北、蒙古、西藏、青海等邊疆地區(qū),人口稀少,開發(fā)程度低,也沒有鑄局提供制錢,貨幣以白銀為主,甚至如青海、西藏、蒙古等地仍以茶磚、毛皮等實(shí)物交易為主,故幾乎不見錢價(jià)奏報(bào)。
(二)錢價(jià)奏報(bào)的作用
錢價(jià)奏報(bào)對清朝的財(cái)政、錢法等起到了重要作用,掌握錢價(jià)信息有利于中央政府處理相關(guān)經(jīng)濟(jì)問題,突出表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
其一調(diào)整鼓鑄數(shù)量。錢價(jià)信息幫助國家調(diào)整鼓鑄政策。當(dāng)錢價(jià)昂貴時(shí),多采取增加鼓鑄的方法。如山東錢價(jià)昂貴,“唯有開爐鼓鑄使錢文增廣則利用便民,功效最速”(43)《奏為東省錢價(jià)昂貴懇恩開爐鼓鑄》,乾隆(無年份),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軍機(jī)處檔折件,文獻(xiàn)編號:003057。;再如福建錢價(jià)昂貴,百姓受苦,閩浙總督“奏請留浙省補(bǔ)辦洋銅于本省開局鼓鑄”。
而當(dāng)錢價(jià)低迷或平穩(wěn)時(shí),則需要酌情減爐。如乾隆二十三年山西共有錢爐11座,每年鑄錢40900余串,錢價(jià)平穩(wěn)的情況下,“酌減從前加增五爐,止留原舊六爐,歲可鑄錢二萬二千余串”。(44)《奏為錢價(jià)平減酌減鼓鑄事》,乾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朱批奏折,檔號:04-01-30-0481-009。再如廣西錢價(jià)平減,“現(xiàn)爐十三座,歲鑄錢六萬余串,已供遞年支放……復(fù)爐增鑄,所有余錢亦必仍歸壅積”(45)《奏為錢價(jià)尚平仍請暫緩增爐事》,乾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朱批奏折,檔號:04-01-35-1287-007。,減爐以防止制錢壅滯。
其二調(diào)節(jié)銅錢庫存。政府查訪錢價(jià),也可為本地庫存錢文出易或貯存平抑錢價(jià)做準(zhǔn)備。清政府依照“錢多則價(jià)賤,錢少則價(jià)增”(46)《清文獻(xiàn)通考》卷32《市糴一》,第 5146 頁。的原則,通過增減貨幣供給來調(diào)節(jié)并穩(wěn)定社會經(jīng)濟(jì)。如乾隆四十三年二月底,陜西共存錢80315串,除一部分協(xié)濟(jì)甘肅外,為調(diào)劑錢價(jià),“在局內(nèi)設(shè)廠出易,每錢一串扣除底錢二文,每制錢九百五十文易庫平銀一兩……于民生日用大有裨益”。(47)《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42輯,臺北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1982年,第614頁。再如乾隆五十六年江蘇的例子,當(dāng)錢價(jià)高昂時(shí),存積“制錢十四萬一千七百五十八串,例應(yīng)隨時(shí)出易以平市價(jià)”,而當(dāng)錢價(jià)低迷時(shí),“商民陽受錢價(jià)平賤之名,陰受物價(jià)增昂之實(shí),若不量為節(jié)制則錢愈賤貨愈貴,商民均無裨益”(48)《奏為調(diào)劑市集錢價(jià)請以存貯局錢搭放兵餉及收買小錢事》,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初四日,朱批奏折,檔號:04-01-35-1334-016。,則需要積極貯存制錢并節(jié)制使用,以防止錢價(jià)過賤而物價(jià)增昂。
查訪錢價(jià),勒令銀錢兼用,從而維持市場比價(jià)。有些地區(qū)用錢明顯多于用銀,需錢增加會使錢價(jià)上升。如乾隆十八年五月山東巡撫楊應(yīng)琚奏山東地區(qū)用錢趨勢增加,錢價(jià)難平,“東省民間多系零星交易,其在三十兩以上者素不多見,應(yīng)酌量減輕,一二十兩為率”,故規(guī)定“凡民間交易在二十兩以上者,不準(zhǔn)用錢,如有違犯,將錢文按搭放兵餉例,以銀一兩換錢一千,官為易換,仍倍罰稅銀充公”。(49)《奏復(fù)令民間交易銀錢并用富戶出易余錢以至錢價(jià)平減事》,乾隆十八年五月初二日,錄副奏折,檔號:03-0771-034。
其三災(zāi)時(shí)實(shí)施錢賑。清代在災(zāi)荒發(fā)生時(shí),除米賑、銀賑外,尚有錢賑的情況。災(zāi)難發(fā)生時(shí),受災(zāi)最多的是廣大農(nóng)村地區(qū)的民眾,而農(nóng)村無論收支、交易、納稅多以制錢為本位,制錢賑濟(jì)顯得尤為重要,在乾隆時(shí)期錢賑已提上日程。(50)參見韓祥:《被遮蔽的“錢賑”:清代災(zāi)賑中的貨幣流通初探》,《清史研究》2017年第1期。
當(dāng)災(zāi)荒發(fā)生時(shí),錢價(jià)信息是重要的錢賑指標(biāo)。如乾隆二年永定河水災(zāi)便已有表現(xiàn),策楞奏稱一定要嚴(yán)查災(zāi)區(qū)錢價(jià),按價(jià)換錢,防止奸商等取利。(51)《奏報(bào)將賑銀易錢散發(fā)事》,乾隆二年七月初七日,朱批奏折,檔號:04-01-35-1227-012。而乾隆七年福建遭遇旱災(zāi),開倉減價(jià)平糶也要考慮錢價(jià)情況,當(dāng)錢價(jià)平減時(shí),則對百姓有利。(52)《奏陳開倉減價(jià)平糶并錢價(jià)漸減情形事》,乾隆七年五月初八日,錄副奏折,檔號:03-0739-027。可見災(zāi)荒發(fā)生時(shí),查明和控制錢價(jià)是防止鋪戶、奸商盤剝百姓、影響救災(zāi)的重要手段,而錢價(jià)奏報(bào)又是國家災(zāi)時(shí)實(shí)施錢賑的重要依據(jù)。
其四維持兵丁生計(jì)。八旗、綠營兵丁的軍餉,大部分以制錢搭放,而錢價(jià)的高低直接影響其收入的多寡。總督、將軍、提督等官員往往根據(jù)市價(jià)對兵餉的數(shù)量進(jìn)行增減調(diào)整。如嘉慶六年托津等奏葉爾羌市集錢價(jià)漸貴,“入冬以來,每銀一兩換錢二百一二十文不等,若將兵丁鹽菜每兩二百五十文折給,較之市價(jià)即多支錢二三十文……兵丁鹽菜向系錢款支放,以銀易錢者甚少,今八城畫一未便照依一城情形定擬……今各城錢價(jià)均在二百一二十文之?dāng)?shù),可否兵丁鹽菜定以每兩二百文或二百一二十文……原放數(shù)目每兩加至五六十文,兵丁等自不必拮據(jù)。”(53)《宮中檔嘉慶朝奏折》第9輯,臺北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1985年,第685頁。戶部、軍機(jī)處議定,最終同意了該建議。(54)《宮中檔嘉慶朝奏折》第14輯,第858頁。可見,政府通對錢價(jià)信息的掌握,及時(shí)調(diào)配八旗俸餉,有利于維護(hù)兵丁生計(jì),穩(wěn)定軍心。
嘉慶時(shí)期錢價(jià)奏報(bào)依然發(fā)揮作用,但自道光以來,行政效率低下,“因循疲玩”的政風(fēng)在處理財(cái)政問題上日益蔓延,錢價(jià)延遲奏報(bào)、漏報(bào)、虛假奏報(bào)的現(xiàn)象頻出。乾隆時(shí)期督撫奏報(bào)除月報(bào)外,多有旬報(bào),至晚清鮮有旬報(bào),馮桂芬指出:“各處市價(jià)準(zhǔn)雨水糧價(jià)之例,而加詳焉,分朔望兩期,督撫按月報(bào)聞”。(55)馮桂芬:《顯志堂稿》卷11,《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xù)編》第79冊,臺灣文海出版社1981 年版,第1048頁。有的地方常存在稽延奏報(bào)的情形,如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江蘇巡撫趙舒翹奏報(bào)江蘇八月份的銀錢比價(jià)(56)《奏報(bào)本年八月各州縣銀價(jià)事》,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錄副奏折,檔號:03-6638-083。,晚了整整一個多月,更有晚了三至四個月奏報(bào)的情形,時(shí)間的稽延使得錢價(jià)奏報(bào)失去了其應(yīng)有的價(jià)值和作用。實(shí)際上,自晚清以來,官員為獲得灰色收入,官報(bào)的制錢市價(jià)往往會略高于實(shí)際市價(jià),從而增加地方政府的套利空間(57)參見羅玉東:《中國厘金史》,商務(wù)印書館2010年版,第152頁。,因此錢價(jià)也多有不確之處。至清末,各省為盈利紛紛鑄造銅元,制錢已走向崩潰邊緣,錢價(jià)奏報(bào)的意義已不明顯。
綜上,清代的錢價(jià)奏報(bào)是對前代錢法管理的傳承和創(chuàng)新,肇始于康熙,發(fā)展于雍正,成熟于乾隆,在清中葉以后還發(fā)揮著一定的效用。其采用獨(dú)具清朝特色的奏折作為呈報(bào)內(nèi)容的載體,程序嚴(yán)密、格式統(tǒng)一、形式多樣。清代經(jīng)過不斷調(diào)整、完善使錢價(jià)奏報(bào)成為一項(xiàng)重要的、常規(guī)化的奏報(bào)方式,在國家調(diào)整貨幣數(shù)量、維持市場穩(wěn)定、災(zāi)時(shí)實(shí)施錢賑、維持兵丁生計(jì)等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錢價(jià)奏報(bào)的運(yùn)行也成為清代錢法積極有為的重要標(biāo)志,其最大限度的控制銀錢比價(jià),從而維護(hù)社會經(jīng)濟(jì)的穩(wěn)定發(fā)展。乾隆時(shí)期,錢價(jià)奏報(bào)幾乎在全國施行,大大加強(qiáng)了皇帝及中央對地方市場信息的了解。錢價(jià)奏報(bào)是清廷為了適應(yīng)社會經(jīng)濟(jì)日益市場化而推出的管理方式,并因此種市場化而做出政策調(diào)適,體現(xiàn)了中國王朝管理體制的創(chuàng)新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