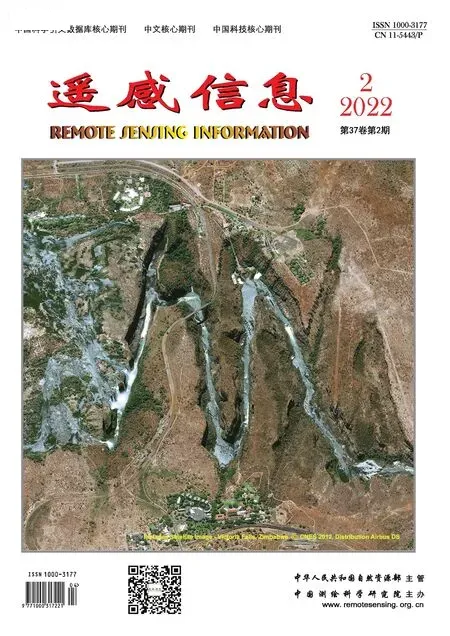北京植被物候時空變化及其對城市化的響應
卜亞勤,丁海勇
(1.南京信息工程大學 地理科學學院,南京 210044;2.南京信息工程大學 遙感與測繪工程學院,南京 210044)
0 引言
植被物候是指植被在生長過程中受人類活動和環(huán)境因素影響而發(fā)生的發(fā)芽、展葉、開花、結實、落葉等現(xiàn)象[1],反映植被不斷適應環(huán)境季節(jié)性變化的生長發(fā)育規(guī)律。植被物候既是氣候變化的重要指示器[2],也是外界環(huán)境變化的感應器[3]。近年來,隨著遙感技術的進步,基于遙感影像的植被物候監(jiān)測方法得到快速發(fā)展,相比于傳統(tǒng)的地面實測法,其不受時空限制,實現(xiàn)由小尺度向中大尺度的轉換。當前,常用的遙感監(jiān)測數(shù)據(jù)主要有AVHRR、SPOT、MODIS和Landsat數(shù)據(jù),其中,MODIS數(shù)據(jù)空間分辨率適宜,且具有穩(wěn)定的植被指數(shù)數(shù)據(jù),被廣泛應用于植被物候的研究中[4-7]。
城市是人類活動改變外界環(huán)境最明顯的場所,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由城市熱島所引起的局地小氣候的改變,對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格局、過程和功能產(chǎn)生影響[8]。同時,城市景觀格局的改變,影響著景觀系統(tǒng)內的物質循環(huán)和能量流動,這些都對城市植被的物候期產(chǎn)生影響。不少學者發(fā)現(xiàn)城市化導致城-鄉(xiāng)梯度上的物候差異,相對于農(nóng)村地區(qū),城區(qū)植被生長季開始期更早、結束期更遲和長度更長[9-10];Qiu等[11]采用不透水層百分比表示城市化水平,發(fā)現(xiàn)不透水層的增加導致植被生長季開始期提前、結束期推遲;Jeong等[12]發(fā)現(xiàn)韓國首爾地區(qū)人口密度的增加與春秋季物候期相關,導致該地區(qū)春季物候期提前、秋季物候期推遲。植被物候的改變對碳固定[13]、鳥類的遷徙[14]、花粉過敏人群的健康[15]等產(chǎn)生影響,因此,研究城市化發(fā)展對植被物候的影響,對北京建設生態(tài)文明城市、保護生物多樣性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本研究利用2001—2019年的MODIS EVI數(shù)據(jù),提取北京的植被物候參數(shù),即植被生長季開始期(start of season,SOS)、生長季結束期(end of season,EOS)和生長季長度(length of season,LOS),分析植被物候的時空變化特征及其對城市化的響應。
1 研究區(qū)及數(shù)據(jù)
1.1 研究區(qū)概況
北京位于我國華北平原西北邊緣,在39.5°N~41°N,115.4°E~117.5°E之間,背靠太行山余脈和燕山山脈,面向華北平原,東南距渤海150 km,土地面積為16 410.54 km2,2019年常住人口為2 153.6萬人。北京以山地和平原為主,地勢總體上西北高、東南低,屬于暖溫帶半濕潤大陸性季風氣候,四季分明,夏季高溫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年平均溫度為10~12 ℃,年降水量為600 mm,夏季盛行東南風,冬季盛行西北風,其自然植被類型包含落葉林、混交林、灌叢、草地等(圖1)。作為全國最發(fā)達的城市之一,北京城市熱島效應明顯、景觀格局變化顯著,這些變化改變了植被的生長環(huán)境,進而影響著其植被物候。

圖1 研究區(qū)
1.2 數(shù)據(jù)源
本研究使用的遙感數(shù)據(jù)為MODIS EVI數(shù)據(jù)(MOD13Q1)和土地利用數(shù)據(jù)。MOD13Q1數(shù)據(jù)集的時間跨度為2001—2019年,從美國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數(shù)據(jù)共享平臺(http://reverb.echo.nasa.gov/)獲取,其時間分辨率為16 d,空間分辨率為250 m,包含NDVI和EVI數(shù)據(jù)集。與NDVI相比,EVI能夠減弱大氣和地面反射率的影響以及弱化植被冠層背景變化的影響[16-17],被認為更適用于監(jiān)測稀疏植被覆蓋的城市植被動態(tài)[18-19]。北京建筑物密集,植被相對較為稀疏,因而本研究選擇EVI提取城市植被物候信息。土地利用數(shù)據(jù)為中國科學院資源環(huán)境科學與數(shù)據(jù)中心(http://www.resdc.cn)提供的2000、2005、2010、2015和2018年的土地利用/覆蓋數(shù)據(jù),用來提取城市建成區(qū),其空間分辨率為1 000 m。該數(shù)據(jù)集以Landsat TM/ETM遙感影像為主要數(shù)據(jù)源,經(jīng)人工目視解譯生成,是當前我國精度最高的土地利用遙感監(jiān)測數(shù)據(jù)產(chǎn)品,在國家水文、生態(tài)、土地資源調查研究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來源于《北京市統(tǒng)計年鑒》,包含人口密度、人均GDP和建成區(qū)面積。
2 研究方法
2.1 時間序列重建
雖然MODIS EVI數(shù)據(jù)集經(jīng)過標準化大氣糾正處理,但仍不能有效去除氣溶膠、云與地物雙向性反射引起的噪聲[20],因此需對時序數(shù)據(jù)進行擬合重建,剔除云層、大氣的干擾。本研究選用Savizky-Glolay(S-G)濾波法對EVI時間序列數(shù)據(jù)進行擬合,該方法有效地保留了原始植被的特征,且更加適用于人類活動干擾更強的區(qū)域[21]。
S-G濾波法通過局部多項式回歸模型來實現(xiàn)平滑時序數(shù)據(jù)[22],其基本思想是:基于高階多項式,利用最小二乘法對滑動窗口內數(shù)據(jù)進行最佳擬合。
2.2 植被物候參數(shù)提取
當前常用的植被物候提取法有導數(shù)法、閾值法和滑動平均法[23]。其中,閾值法操作簡單,使用靈活,包含固定閾值法和動態(tài)閾值法。相對于固定閾值法,動態(tài)閾值法可消除因土壤背景值和植被類型差異帶來的影響,故本研究使用該方法提取植被物候參數(shù)。動態(tài)閾值法是根據(jù)植被的生理特征,將植被指數(shù)曲線在上升和下降階段達到曲線振幅一定比例的時間作為植被的生長季開始期和結束期。Zhou等[24]在研究中國32個城市時,選擇0.2作為閾值提取植被物候;胡召玲等[25]在研究中國東北城市的植被物候時,選擇0.25作為閾值。本研究經(jīng)過嘗試,參考相關文獻并結合實際情況,將提取生長季開始期的閾值設置為0.2,提取生長季結束期的閾值設置為0.25(式(1)、式(2))。
λSOS=(EMAX-EMIN1)0.2
(1)
λEOS=(EMAX-EMIN2)0.25
(2)
式中:λSOS表示提取生長季開始期的EVI閾值;EMAX表示EVI最大值;EMIN1表示曲線上升階段EVI最小值;λEOS表示提取生長季結束期的EVI閾值;EMIN2表示曲線下降階段EVI最小值。
2.3 建成區(qū)及緩沖區(qū)
根據(jù)中國縣級行政區(qū)劃圖,利用土地利用/覆蓋數(shù)據(jù)提取北京主城區(qū)建成區(qū),其中,2000、2005、2010、2015和2018年分別代表2001—2002年、2003—2007年、2008—2012年、2013—2017年、2018—2019年[26]。文獻[27-28]在研究北美東部與中國城市化對植被物候的影響中,估算城市化對植被物候的影響足跡距城市周邊不到20 km,據(jù)此,本研究選擇城區(qū)外20 km范圍作為郊區(qū),并利用ArcGIS沿城區(qū)邊界向外延伸作0~1 km、1~2 km、2~5 km、5~10 km、10~15 km和15~20 km的緩沖區(qū),得到圖2,并計算城區(qū)和郊區(qū)以及各緩沖區(qū)內植被物候的平均值。

圖2 城區(qū)及緩沖區(qū)
3 結果與分析
3.1 植被物候空間分布
基于連續(xù)的MODIS EVI產(chǎn)品數(shù)據(jù),使用動態(tài)閾值法提取北京的植被物候期(生長季開始期、生長季結束期和生長季長度),得到北京植被物候期的空間分布圖(圖3)。生長季開始期空間分布圖(圖3(a))中,植被生長季開始期多集中在90~105 d,整體從東南向西北推遲,與海拔有一定關系,其中,城區(qū)植被的生長季開始期最早,集中在75~90 d,城區(qū)周邊植被生長季開始期較晚,多在90~105 d之間。生長季結束期空間分布圖(圖3(b))中,植被生長季結束期多集中在290~300 d,東南部向西北部逐漸提前,其中,城區(qū)植被生長季結束期最晚,集中在300~320 d,城區(qū)周邊植被生長季結束期較早,多在290~300 d之間。生長季長度空間分布圖(圖3(c))中,植被生長季長度多集中在190~210 d,且分布規(guī)律與生長季開始期和結束期相同,東南向西北遞減,同時,城區(qū)植被生長季長度最長,周邊稍短,分別集中在210~230 d和190~210 d。

圖3 北京植被物候期多年平均值
3.2 植被物候年際變化
以年份為自變量,以北京每年生長季開始期、結束期和長度的平均值為因變量,引入一元線性回歸方程擬合北京2001—2019年植被物候參數(shù)的變化趨勢(圖4)。由圖4發(fā)現(xiàn),北京出現(xiàn)植被生長季開始期提前、結束期推遲和長度延長的現(xiàn)象,平均植被生長季開始期、結束期和長度分別為96.2、295.5和199 d。圖4(a)~圖4(c)中,生長季開始期平均每年提前0.69 d,波動幅度較大,其中,2006年的生長季開始期最晚,超過110 d,2017年的生長季開始期最早,小于90 d;生長季結束期平均每年延遲0.71 d,波動幅度相對較為穩(wěn)定;生長季長度平均每年延長1.4 d,其中,2006年生長季長度最短,2017年最長。由生長季開始期和結束期的波動幅度差異發(fā)現(xiàn),生長季開始期對外界環(huán)境的變化更為敏感。

圖4 北京植被物候期年際變化趨勢
圖5為城區(qū)和郊區(qū)的植被物候期變化趨勢。相比于郊區(qū)的植被物候期,每年城區(qū)都表現(xiàn)出更早的生長季開始期、更晚的生長季結束期和更長的生長季長度。由圖5(a)可見,2001—2019年,城區(qū)和郊區(qū)的植被生長季開始期均呈現(xiàn)提前趨勢,但提前速度有所差異,城區(qū)植被的生長季開始期平均每年提前0.23 d,郊區(qū)提前速度較快,為0.68 d/a;圖5(b)中,城區(qū)與郊區(qū)均表現(xiàn)出植被生長季結束期推遲的現(xiàn)象,城區(qū)的推遲速度較慢,平均每年推遲0.16 d,郊區(qū)較快,以平均每年0.72 d的速度推遲;圖5(c)中,城區(qū)和郊區(qū)的生長季長度都呈延長趨勢,平均每年分別延長0.42、1.42 d。整體來看,城區(qū)和郊區(qū)的植被物候期均呈現(xiàn)出相同的變化趨勢,但變化速度不同,郊區(qū)的植被物候期變化速度明顯快于城區(qū)。

圖5 北京城區(qū)和郊區(qū)植被物候期年際變化趨勢
3.3 城市化梯度上的植被物候變化
北京的植被物候期在城郊方向上表現(xiàn)出明顯的梯度現(xiàn)象(圖6)。由圖6可見,2001—2019年間,植被物候期與距城區(qū)的距離呈顯著的對數(shù)關系,城區(qū)的植被生長季開始期最早、結束期最晚和長度最長,分別為86.6 d、309.3 d和222 d。隨著距城區(qū)距離的增加,植被生長季開始期逐漸變晚、結束期逐漸提前、生長季長度逐漸縮短,同時,距離城區(qū)越遠,植被物候期的變化幅度越小。總體來看,植被生長季開始期、結束期和長度均在0~2 km范圍內變化明顯,這歸因于城市近郊區(qū)的熱島強度和不透水層覆蓋率遠大于遠郊區(qū),人類活動頻繁,城市化對植被物候期影響顯著。隨著距城區(qū)距離的增加,植被物候期變化的幅度越小,10 km以外的物候期變化趨勢趨于平緩,這表明該范圍外的植被物候期受城市化影響明顯減弱。

圖6 城郊梯度上的植被物候期變化趨勢
3.4 城市化特征分析
城市化也稱城鎮(zhèn)化,是一個復雜的進程,是社會由以農(nóng)業(yè)為主向以工業(yè)和服務業(yè)為主逐漸轉變的過程,包括人口城市化、經(jīng)濟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本研究選擇人口密度表示人口城市化、人均GDP表示經(jīng)濟城市化、建成區(qū)面積占比表示土地城市化,以這三個指標定義城市化進程。2001—2019年北京的人口密度、人均GDP和建成區(qū)面積占比的年際變化趨勢如圖7所示。圖7(a)中,2001—2019年北京人口密度整體呈增長趨勢,由2001年的824人/km2增長至2019年的1 312人/km2,其年均增長率為2.6%,其中,2001—2014年人口密度增速較快,年均增長率為3.6%,2014—2017年趨于平穩(wěn),因2017年后北京開始整頓低端產(chǎn)業(yè),人口稍有下降。2001—2019年人均GDP以10.3%的年均增長率穩(wěn)步增長,由2001年的28 097元增長至2019年的165 220元,見圖7(b),其中,2015年后增速最快。建成區(qū)面積占比呈波動增長趨勢,見圖7(c),年均增長率為3.5%,2009—2010年建成區(qū)面積占比有所下降,其他時間段均在增長。整體而言,北京的城市化進程明顯,其人口密度、人均GDP和建成區(qū)面積占比均呈現(xiàn)增長趨勢。

圖7 城市化指標年際變化趨勢
3.5 城市化對植被物候的影響
對北京城區(qū)和郊區(qū)的植被物候期與人口密度、人均GDP和建成區(qū)面積占比進行皮爾遜(Pearson)相關性分析,得到表1。就城區(qū)來看,植被生長季開始期與城市化的三個指標均無明顯相關關系(P>0.05),植被生長季結束期和長度均與人均GDP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P<0.05),人均GDP的增長對植被生長季結束期推遲和長度延長有重要作用。而郊區(qū)的植被物候期均與人口密度、人均GDP和建成區(qū)面積存在顯著關系,其中,生長季開始期與人口密度(P<0.05)、人均GDP(P<0.01)和建成區(qū)面積占比(P<0.05)均顯著負相關,生長季結束期、生長季長度與人口密度、人均GDP和建成區(qū)面積占比均極顯著正相關(P<0.01),城市化進程對郊區(qū)的植被物候的影響顯著。由城區(qū)和郊區(qū)的植被物候期與各城市化因子的相關關系可以發(fā)現(xiàn),郊區(qū)植被物候期受城市化影響更為劇烈,這可能因為城市化進程中,北京城市擴張明顯,郊區(qū)建筑物快速增加,且大型工廠多在郊區(qū),這些都導致郊區(qū)水熱環(huán)境變化顯著,深刻影響到植被物候。

表1 植被物候期與人口密度、人均GDP和建成區(qū)面積占比的皮爾遜相關系數(shù)
4 討論
本研究使用人口密度、人均GDP和建成區(qū)面積占比表示城市化進程,探討城市化進程對植被物候的影響,發(fā)現(xiàn)植被物候期與城市化進程相關性明顯,這與文獻[11]、文獻[12]的研究結果相一致。此外,植被物候期除受人類活動影響外,還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文獻[29]根據(jù)研究青藏高原東北部牧草物候發(fā)現(xiàn),影響牧草物候期的主要因素是溫度,降水次之;文獻[11]對中緯度大城市的植被物候進行研究,發(fā)現(xiàn)在大部分氣候區(qū),不透水層的增加對植被生長季開始期提前、結束期推遲有重要作用,同時,氣候因素對植被物候變化起主導作用;Yuan等[30]發(fā)現(xiàn)黃河流域植被返青期受季前日最低溫度影響更大,且城市熱島造成城鄉(xiāng)植被物候的差異。
城區(qū)與郊區(qū)的植被物候變化程度有所不同,郊區(qū)的植被物候變化更為劇烈,這可能與北京城區(qū)人口流出、郊區(qū)人口暴增、郊區(qū)發(fā)展迅速有關。2010—2019年間,北京主城區(qū)(東城區(qū)、西城區(qū)、朝陽區(qū)、豐臺區(qū)、石景山區(qū)、海淀區(qū))人口增加445萬人,而近郊區(qū)(房山區(qū)、通州區(qū)、順義區(qū)、昌平區(qū)、大興區(qū)、門頭溝區(qū))人口增加546萬人。其中,2000—2019年,主城區(qū)流出48萬人,近郊區(qū)暴增約223萬人,郊區(qū)人口增長更加明顯,同時,北京城市化發(fā)展不斷向郊區(qū)擴張,這些導致郊區(qū)植被生長的外部環(huán)境變化顯著,植被物候變化劇烈。
5 結束語
本研究基于2001—2019年MOD13Q1植被指數(shù)產(chǎn)品,利用S-G濾波算法和動態(tài)閾值法提取了北京的植被生長季開始期、結束期和長度,研究其植被物候期的時間變化趨勢和空間分布特征,并探究城市化對城區(qū)和郊區(qū)植被物候的影響,研究結論如下。
1)北京出現(xiàn)植被生長季開始期提前、結束期推遲和長度延長的現(xiàn)象。分區(qū)域看,城區(qū)和郊區(qū)也均表現(xiàn)相同的現(xiàn)象,但城區(qū)和郊區(qū)的植被物候期變化速度有所差異,郊區(qū)植被物候變化更為明顯。
2)植被物候期在城郊梯度上表現(xiàn)出明顯的空間異質性,且植被物候期與距城區(qū)的距離呈顯著的對數(shù)關系,城區(qū)的生長季開始期最早、結束期最遲、長度最長。
3)植被物候期與城市化進程相關性明顯。分區(qū)域看,郊區(qū)的植被物候期與城市化因子(人口密度、人均GDP和建成區(qū)面積占比)相關性更強,城區(qū)稍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