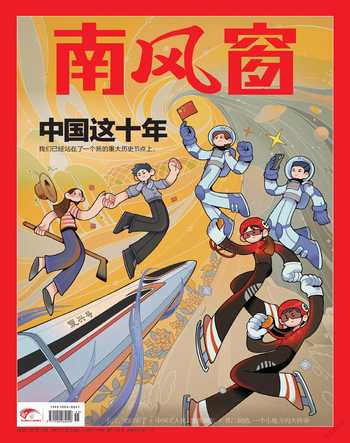“歷史熱”需要冷思考
何國勝

歷史學(xué)熱了起來,各個知識付費(fèi)平臺上,歷史知識的課程總在“熱門”版塊。同時,一些老學(xué)者也再次走進(jìn)大家的視野,廣受歡迎。人們企圖從他們豐富的歷史經(jīng)驗(yàn)中找到當(dāng)下問題的答案。
這種感受的出現(xiàn),很難與新冠疫情脫開關(guān)系。一種現(xiàn)實(shí)的聲音頻頻在朋友間和社交媒體上出現(xiàn):我們見證并經(jīng)歷了歷史。可這種經(jīng)歷意味著什么?未來又該往何處去?普遍迷茫中,自然生發(fā)了從歷史中找尋種種經(jīng)驗(yàn)的需要。
重新閱讀歷史,我們發(fā)現(xiàn),過往不曾被注意的很多細(xì)節(jié)和面向,很長時間以來被忽視了、遮蔽了。
那么,此時此地、此情此景,我們應(yīng)該讀什么樣的歷史,又應(yīng)該怎樣進(jìn)入歷史?借助歷史的視角觀之,當(dāng)下發(fā)生的一切對普通人意味著什么?帶著這些問題,南風(fēng)窗記者與復(fù)旦大學(xué)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員段志強(qiáng)展開了一場對話。
沒有遺忘就沒有歷史
南風(fēng)窗:疫情來臨后,有人感慨,以前讀歷史忽視了瘟疫對人類歷史的影響和改變,為什么我們過去讀的歷史好像不太關(guān)心這一塊?
段志強(qiáng):傳統(tǒng)的歷史學(xué)都以政治、軍事及大人物的行動為中心,不是特別關(guān)心瘟疫、環(huán)境、氣候這些問題。我們現(xiàn)在總覺得歷史學(xué)是記錄過去的,但其實(shí)在古代,歷史學(xué)的主要功能往往并非如實(shí)記錄過去,而是反映興衰或是強(qiáng)調(diào)某些道德、樹立某些人格榜樣。瘟疫等問題和上述“歷史主體”沒有太大的關(guān)系,所以過去歷史學(xué)對這一塊比較忽視。
第二個原因是,盡管在五六十年前學(xué)界就已出現(xiàn)了很好的關(guān)于瘟疫的歷史研究著作,但它似乎一直缺乏一個契機(jī)進(jìn)入大眾層面。大眾心目中關(guān)注的歷史熱點(diǎn)跟學(xué)界有很大不同,這次新冠疫情就提供了一個契機(jī),使大家忽然發(fā)現(xiàn),原來歷史學(xué)家早已研究過不少關(guān)于瘟疫的歷史。
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原因:瘟疫在歷史上曾造成非常大的損害,但似乎瘟疫過去之后,大家就不愿意再提起了。有學(xué)者說,這可能是人類社會修復(fù)心理創(chuàng)傷的一種手段。
我們今天總覺得了解過去的瘟疫,可以幫我們更好地處理現(xiàn)在的事情,預(yù)防未來的問題。但在公共衛(wèi)生體系建立之前,這一套愿景根本不存在。這種情況下,你再了解瘟疫也見效不大,所以古人不太會反復(fù)提及過去的瘟疫。
南風(fēng)窗:現(xiàn)在經(jīng)常能看到人們講,“我們正在見證和經(jīng)歷著歷史”,對普通人而言,這意味著什么,我們怎么去面對和記錄這些?
段志強(qiáng):我也經(jīng)常聽朋友這樣說。有一個問題是,為什么說我們現(xiàn)在見證了歷史,我們過去難道就沒有見證歷史嗎?我們之前過的那種日子難道就沒有資格被稱為歷史嗎?我覺得這其中至少有兩個層面的關(guān)系。
一是“變”與“常”的關(guān)系,就是我們覺得好像常態(tài)不是歷史,生活發(fā)生了改變才是歷史。另外一個層面是“主動”和“被動”的關(guān)系。能掌控的生活,我們不覺得那是歷史,而當(dāng)我們被動地裹挾到一些事情中,我們會覺得這是歷史。
我覺得我們對歷史的定義產(chǎn)生了誤解,當(dāng)然這個誤解首先是歷史學(xué)家造成的。在過去的歷史觀念當(dāng)中,似乎只有那些變化的、特別是我們難以控制的劇烈變化、那些外在于我們的東西,才是歷史。
我能理解為什么我們現(xiàn)在會說自己在見證歷史,但我也想提醒一下,我們每天都是在見證歷史,并不是說只有這種大事發(fā)生了,我們才見證歷史。反而那些我們能掌控的日常歲月,正是我們創(chuàng)造歷史的時候,這些突變的日子,是我們被裹挾的時候。
當(dāng)然,我不是說這些變化不重要了,但它的重要性是通過未來的發(fā)展來體現(xiàn)的,也就是說,今天到底重不重要是由以后來決定的。
南風(fēng)窗:那我們應(yīng)該怎么記述這段歷史?
段志強(qiáng):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這個“我們”是誰?這段歷史總是會被記錄下來,那到底以誰的立場,以誰的視角來記錄?
官方有官方的記法,個體也有自己的記法。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今天或許正是一個很好的契機(jī),可能是人類歷史上,至少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讓大量的普通人有機(jī)會、有能力也有愿望記錄下自己正在經(jīng)歷的歷史的契機(jī)。
智能手機(jī)普及后,我們有了最方便的記錄媒介。不管網(wǎng)絡(luò)的表達(dá)空間有多小,你總能找到留下你這一記錄的角落。你可以隨意記述幾句,或者就拍照片,拍照片本身就是一種記錄。
不用想著同歷史學(xué)家一樣試圖把這段經(jīng)歷完整記錄下來,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就算你記錄了片段,你的手機(jī)相冊可能以后也不會打開,或者你手機(jī)壞了、丟了,這都是很正常的。只不過當(dāng)記錄的人基數(shù)足夠大的時候,總有一些會留下來,也總有一些會被看到。
沒有遺忘就沒有歷史,如果我們把所有的事情都記下來,那么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歷史這種東西。
南風(fēng)窗:但在當(dāng)下這種熱點(diǎn)不過夜的時代,人們更容易遺忘和被緊接而來的熱點(diǎn)淹沒。很多事情重復(fù)發(fā)生,似乎也一再表明,人們從歷史中學(xué)到的唯一教訓(xùn)就是不吸取教訓(xùn)。
段志強(qiáng):我覺得,遺忘是天賜給人類的禮物,如果沒有遺忘的話,我們每個人都活不下去。
網(wǎng)上的熱點(diǎn)一個蓋一個,這是大家薄幸寡恩嗎?不是,因?yàn)槿四X承載不了那么多信息,尤其是承載不了那么多負(fù)面信息。其實(shí)歷史也是這樣,沒有遺忘就沒有歷史,如果我們把所有的事情都記下來,那么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歷史這種東西。就像你無法畫一幅1∶1比例的地圖一樣,如果你畫出1∶1比例的地圖,所有人都不要生活了,干脆住到地圖里。
你提到的人類不從歷史中吸取教訓(xùn)這事其實(shí)比較復(fù)雜。什么叫不吸取教訓(xùn)?有些錯誤我們持續(xù)地再犯,比如今天我要勵志減肥,但是過兩天我又胡吃海喝,這是很多人的狀態(tài)。這是不是遺忘導(dǎo)致的不吸取教訓(xùn)呢?恐怕不是,這可能更和人的本性有關(guān)。
擴(kuò)展到社會來說就更復(fù)雜。如果我們把這些歷史都研究得很透徹,是不是就不會重蹈覆轍?我覺得這忽略了人類社會的復(fù)雜性。我們每次面臨的問題都和它的具體環(huán)境有關(guān),而這些具體環(huán)境總是在千變?nèi)f化。但我們可以避免一些人為的陷阱,由那些人為的遺忘造成的人為的陷阱。
要看到多元的視角
南風(fēng)窗:我們剛開始聊了瘟疫,除此之外,我們還有哪些可以重新發(fā)現(xiàn)歷史的視角?
段志強(qiáng):我說一句“暴言”:所有的事物都是視角。在歷史學(xué)界研究比較多的,除了我們剛才講的瘟疫,還有氣候和環(huán)境。也有人關(guān)注一些物質(zhì)條件,比如說從地理的視角、從水的視角、從風(fēng)的視角,比如有一些學(xué)者就在推動一個叫季風(fēng)亞洲的研究計(jì)劃,因?yàn)榧撅L(fēng)和航海、氣候都有直接關(guān)聯(lián)。
還有很多別的,人們生活中的各種各樣的物、精神和社會的元素都是視角。從人來說,每個人都構(gòu)成一種視角,每個群體也都構(gòu)成一種視角。我一直主張每個人都要有自己的視角,而且這個視角是不可取代的。也許最后沒有人注意你,但是你的視角就是你生活的全部。
我最擔(dān)心的就是,我們每個人的視角最后被磨平了,因?yàn)榭傆腥讼肽テ轿覀兊囊暯牵芏鄷r候我們還會主動配合這種磨平。磨到最后,大家看到的都是一樣的東西。可現(xiàn)實(shí)并非這樣。
所以,歷史的多元視角非常重要。當(dāng)我們從不同的視角去看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們會看到這個世界是立體的。
南風(fēng)窗:人的歷史,有的時候講交流和共同的部分,有的時候講分化和沖突,我們現(xiàn)在好像到了一個既在講共同,又在講不同的時候,有點(diǎn)茫然無措,你覺得此刻我們應(yīng)該著重講什么?
段志強(qiáng):我覺得不是我們要講什么,而是我們怎么講,這一點(diǎn)很重要。不管是交流融合還是分化沖突,都是歷史的組成部分。
一種常見的誤區(qū)是:我們強(qiáng)調(diào)人和人不一樣的時候,會忘記其實(shí)大家差別沒有那么大,很多東西是通過人和人之間的交換和互相啟發(fā)后才出現(xiàn)的。但當(dāng)我們強(qiáng)調(diào)互相交流的時候,我們也忘了人和人為什么會分化,好像我們覺得人和人的分化、沖突是不正當(dāng)?shù)摹?/p>
這還是我們說的歷史的多元視角問題。交流融合和分化沖突其實(shí)都是同時存在的,在任何時代都是。我們或許應(yīng)該意識到它們各自有各自的動力、原因,我們可能不喜歡沖突,覺得大家和和美美的挺好,但是這個愿望本身并不能取消那些摩擦。同樣,那些沖突甚至戰(zhàn)爭也沒法取消人與人之間的共通之處。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我們的歷史表述過于單一了,產(chǎn)生一種天真的想象。
其實(shí),人類社會本身的運(yùn)行軌跡,就是什么樣的都有,多元歧出。交流融合當(dāng)然好,分化沖突也不一定就是壞。沒有分化,就沒有豐富多彩的人類文化。所以,歷史學(xué)應(yīng)該揭示這些邏輯的復(fù)雜性。同樣一個事情,我們要看到它在不同層次、不同的時段上有不同的意義。
中國文明相比于世界其他文明來說有一個鮮明的特點(diǎn)—文明核心的地理區(qū)域一直沒變,一直在黃河中下游地區(qū)。但這會帶來一個誤解,好像我們覺得地理區(qū)域沒變,那么人也沒變,文化也沒變,其實(shí)不是。
南風(fēng)窗:中國歷史上也有過大規(guī)模的人口遷徙和移民,這促進(jìn)了互相的友好交流。比如你在《從中國出發(fā)的全球史》里講到的,江南是移民的產(chǎn)物,其實(shí)中國的西北也是移民的產(chǎn)物。中國的歷史,不停地在各民族、各地區(qū)人民之間的互動中形成。
段志強(qiáng):不但江南、西北是移民的產(chǎn)物,中原地區(qū)也是移民的產(chǎn)物。我們不能想象似乎有一個不變的中心地帶,然后邊緣都是通過中心地帶的擴(kuò)張或是人口輸出形成的。
并非這樣。即使是傳統(tǒng)上被認(rèn)為是華夏地區(qū)的地方,也是有人遷進(jìn)、遷出,這是常態(tài)。中國文明相比于世界其他文明來說有一個鮮明的特點(diǎn)—文明核心的地理區(qū)域一直沒變,一直在黃河中下游地區(qū)。但這會帶來一個誤解,好像我們覺得地理區(qū)域沒變,那么人也沒變,文化也沒變,其實(shí)不是。
地理雖然沒變,但是人口、血緣、文化一直都在變,當(dāng)然具體歷程是非常復(fù)雜的。這是首先要說明的一個問題。另一個問題是,國家一直都有限制流動的作用。今天我們遇到了一些新問題—國界變得越來越堅(jiān)硬了。過去雖然也有國家,有邊疆地區(qū),但是國界相對而言是比較柔性的。
國界越來越堅(jiān)硬之后,很多原本并不一定以國界劃分的事情,現(xiàn)在變得越來越以國界劃分,比如說語言、文化、飲食、信仰,甚至植被、地貌等等。這也意味著國家對于人的生活越來越重要了,我們的思考被國家視角主導(dǎo)。
國家視角會遮蔽掉一些東西。比如說飲食。中國國家范圍內(nèi)有各種食物,北方草原、西北戈壁、青藏高原、西南山區(qū)都有很特別的飲食,但我們想象中的“中餐”仍然主要是漢族的飲食習(xí)慣。這就是國家與文化的一種錯位。當(dāng)然,以國家為本位思考問題,本身沒有錯,不過我們也不要忘記了其他視角。
舉個例子。我父親年輕的時候彈棉花,那種傳統(tǒng)的彈花弓,像弓箭一樣。后來我看一幅幾百年前的意大利油畫,畫的就是一個彈棉花的人,那人背的弓跟我小時候見過的一模一樣。我當(dāng)時想,若沒有語言的障礙,他和我爸爸肯定能聊到一塊去。但讓我爸爸和一個中國的皇帝坐在一起聊,他們能不能聊到一起?我看夠嗆。
歷史學(xué)受歡迎不是什么好事
南風(fēng)窗:感覺近來歷史熱了起來,比如關(guān)于歷史的知識付費(fèi)課程多了起來,出現(xiàn)在大眾面前并受到大家的喜愛,這意味著什么?
段志強(qiáng):直截了當(dāng)?shù)卣f,我認(rèn)為歷史學(xué)受歡迎不是什么好事。我每次聽別人說你們這一行又熱起來了,我都非常沮喪,為什么?
我覺得一個理想的狀況應(yīng)該是大家都去關(guān)心未來,或者至少是關(guān)心現(xiàn)在。比如在影視劇當(dāng)中,我認(rèn)為最好是有很多科幻的作品,想象未來是什么樣的。也應(yīng)有很多剖析現(xiàn)實(shí)、表現(xiàn)現(xiàn)實(shí)生活的作品,有少部分講過去的,大家娛樂一下就可以了。但現(xiàn)在剛好反過來,我們是講過去最多,現(xiàn)實(shí)的家長里短的還有一點(diǎn),講未來的很少,甚至出現(xiàn)一些既不講過去、又不講現(xiàn)實(shí)、還不講未來的題材。
南風(fēng)窗:是不是現(xiàn)在大家有些想不清的問題,在向過去要答案?
段志強(qiáng):是的,這是問道于過去,人都是在迷茫的時候會問道于過去,當(dāng)你遇到一些不知道怎么辦的事情,你可能會找老人來問一問。
對過去充滿興趣,不是一定不好,而是要看對什么樣的過去充滿興趣。如果你看到的過去都是像宮斗劇那樣,勾心斗角,大家爭來爭去的內(nèi)容,就有問題了。中國歷史也好,人類歷史也罷,爭斗、權(quán)謀只是一小部分,還有無數(shù)的人在創(chuàng)造、勞動,他們用盡聰明才智,發(fā)明一些技術(shù)、工具、制度、文化,然后讓社會延續(xù)了這么長時間。我們?yōu)槭裁床槐憩F(xiàn)那些呢?
也可能因?yàn)槲覀兊纳鐣旧砭褪且粋€高度競爭性的社會,所以我們看過去時看到的也是過去的人在如何競爭。小到宮斗這樣的競爭,大到文明之間的戰(zhàn)爭。
宋代偉大的思想家朱熹,他有一句話我覺得非常適合現(xiàn)在。他說歷史書有什么好看的,歷史書就是“相斫書”,你砍我我砍你。朱熹告誡他的學(xué)生們不用看太多歷史。
歷史學(xué)家不容易被欺騙,但是歷史學(xué)家很容易去騙人。我們接受采訪或者聊天時,經(jīng)常會鼓吹歷史學(xué)的價值,但說這個話的時候我相當(dāng)心虛。因?yàn)椴⒉皇撬械臍v史學(xué)作品都符合我們剛才說的那些價值,也并不都是我們想要的那種歷史學(xué)。
宋代偉大的思想家朱熹,他有一句話我覺得非常適合現(xiàn)在。他說歷史書有什么好看的,歷史書就是“相斫書”,你砍我我砍你。朱熹告誡他的學(xué)生們不用看太多歷史。
就以我熟悉的中國歷史學(xué)來說,特別是大眾所了解的歷史學(xué),整體上還是自上而下的視角,站在國家、士大夫精英文人的立場上來看待這個社會。當(dāng)然,這樣視角不是說不對,只是說它是視角之一,不能遮蔽別的視角,比如自下而上的視角。
南風(fēng)窗:尋找人類社會的規(guī)律,建立因果性,是社會科學(xué)的執(zhí)著追求之一,怎么樣才能既不迷失于浩如煙海的細(xì)節(jié)和事實(shí)之中,又能掌握理論的能力,而不執(zhí)迷于一家之言?
段志強(qiáng):我覺得細(xì)節(jié)和事實(shí)才是真的歷史,而理論正是一家之言。所以掌握理論的能力就等于執(zhí)迷于一家之言。有句話叫“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我的理解不一樣,我覺得生活是灰色的,而理論之樹長青。
生活本身是多樣的、混雜的、模糊的,是灰色的,而理論之樹永遠(yuǎn)有新的東西。今天有人提這個理論,明天又有新的。如果我們想象會有一些宏觀的理論能讓我們把握歷史趨勢,這本身是一種迷思。理論是不斷被否定的,所以它總是在不斷變化,不存在一種終極理論可以解釋歷史、把握歷史。但是理論更是多元共存的,理論不是答案,理論也是一種視角。
其實(shí)你這個問題有點(diǎn)接近另一個問題—我們怎樣避免歷史的碎片化?好像我們接觸到碎片的歷史,就覺得有一種不滿足,像是掉進(jìn)了一個汪洋大海里,找不到岸邊。
但我要提醒的是,碎片是歷史的本質(zhì)。這和我們剛才談的遺忘的問題有關(guān)。有遺忘才有歷史,拋去那些被遺忘的大多數(shù),記住的這些比較少的東西,就是歷史的碎片。歷史本來就是在這些碎片當(dāng)中,如果你能接觸到各種各樣的浩如煙海的細(xì)節(jié)和事實(shí),我覺得是一件比較幸福的事。
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細(xì)節(jié)和事實(shí)當(dāng)中,而不是生活在理論當(dāng)中。所以為什么要害怕細(xì)節(jié)和事實(shí)?那就是生活本身。
但另一方面,理論的一個作用是讓我們看到特定的細(xì)節(jié)和事實(shí),如果沒有理論,有些事實(shí)你可能永遠(yuǎn)不會注意到。比如說瘟疫,如果沒有今天人們對于瘟疫和歷史關(guān)系的理論化理解,那么我們今天可能不會看到那么多歷史上的關(guān)于瘟疫的信息,這是理論的意義。可我們不能反過來,不能把細(xì)節(jié)和事實(shí)看成手段,而把理論看成目的。我們應(yīng)該把理論看成手段,把事實(shí)看成目的。這可能是歷史學(xué)和其他社會科學(xué)不一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