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學家改寫了描述無序性的基本定律
編譯 王曉濤

對熵增過程的理解,只要利用簡單的概率學原理就可以了嗎?我們是否可以引入量子力學的公理來解釋熵增?
在所有物理定律中,最神圣的原則莫過于熱力學第二定律——熵,一種表征無序性的量,始終保持增加或不變。英國天體物理學家亞瑟?愛丁頓(Arthur Eddington)在他1928年出版的《物理世界的本質》一書中寫道:“如果有人告訴你,你最喜歡的理論與麥克斯韋方程組不一致——那么你可以說,麥克斯韋方程組出了問題。如果你的理論與觀測現象相矛盾——好吧,做實驗的人有時確實會把事情搞砸。但如果你的理論違反了熱力學第二定律,那我就沒辦法給你圓場了。你恐怕只能在深深的屈辱感中逐漸崩潰。”我們從未觀察到過任何違反這一定律的現象,也從不會預言這種事件的發生。
但是,對于熱力學第二定律,物理學家依然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有人懷疑,這一定律的理論基礎可能并不牢固,我們對它的解釋也可能并不合理。雖然它被稱為定律,但我們通常認為,它只是在描述一種概率性的現象: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任何過程的結果都是最可能發生的那一種。也就是說,即使考慮到所有可能,那個唯一的結果也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物理學家并不滿足于只是描述可能發生的事情。“我們喜歡精確的物理定律。”牛津大學的物理學家基亞拉?馬萊托(Chiara Marletto)說。除了作為對可能發生事件的描述,熱力學第二定律還能否表示為其他形式?
許多獨立的研究小組似乎正在向這樣的方向努力。他們打算從量子力學的基本原理中推演出熱力學第二定律——有人相信,量子力學在更深的層次上具有方向性和不可逆性。根據這種觀點,熱力學第二定律的出現不是因為經典的概率論,而是因為量子糾纏等效應。它起源于量子系統共享信息的方式,以及起到決定性作用的量子論基本原理。由此可見,熵的增加不僅僅是各種變化中最可能的結果,還是我們所知道的最基本架構——信息的量子架構——的邏輯結果。
量子必然性
19世紀初,熱力學誕生,人們用它來描述熱量的流動和功的產生。在蒸汽動力機器推動工業革命的過程中,人們迫切需要理論以使得設備盡可能高效。
雖然熱力學對制造更好的發動機和機械設備并沒有多大的幫助,但它卻成了現代物理學的核心支柱之一,并提供了描述各種變化過程的標準原則。

牛津大學物理學家基亞拉?馬萊托
經典熱力學只有少數幾條定律,其中最基本的是第一條和第二條。熱力學第一定律表明,能量總是守恒的。熱力學第二定律表明,熱量總是從高溫物體流向低溫物體。我們通常利用熵的概念來表示這條定律。在任何變化過程中,熵都必須整體地增加。熵大致等同于無序性,但奧地利物理學家路德維希?玻爾茲曼(Ludwig Boltzmann)將其更嚴格地表述為一個與系統擁有的微觀狀態總數相關的量:即粒子所有可能排列情況的總數。
首先,熱力學第二定律說明了常見的變化過程發生的原因。對于單個粒子的運動而言,經典的運動定律可以保證其逆向運動的可能性。但是,熱力學第二定律表明,變化必須以熵增加的方式發生。我們普遍認為,這種方向性就像是一個時間箭頭。根據這種觀點,時間從過去流向未來,因為宇宙開始時——出于某種我們尚未完全理解或確定的原因——就處于低熵狀態,并且正朝著更高熵的方向發展。這意味著,最終熱量將完全均勻地傳播,并且不會有任何進一步變化的驅動力——19世紀中葉的科學家將這種令人沮喪的前景稱為宇宙的熱寂。
玻爾茲曼對熵的微觀描述似乎可以解釋這種方向性。由于分子間相互作用,對于多粒子系統,更無序且熵更高的狀態數量遠遠超過有序的低熵狀態。熱力學第二定律似乎只是統計學上的一條定律,即大數定律。這種觀點認為,熵不能減少——比如,你房間里的所有空氣分子不能偶然地聚集在一個角落——是沒有根本原因的。
然而,這種與概率統計相關的物理學留下了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它引導我們研究所有可能狀態的集合中最可能的微觀狀態,并迫使我們傾向于在該集合中取平均值。

牛津大學物理學家大衛?多伊奇
但是經典的物理定律是確定性的——即只能允許單一的結果。如果只有一種結果是可能的,那么這種狀態究竟會在哪里出現呢?
牛津大學的物理學家大衛?多伊奇( David Deutsch)多年來一直試圖通過發展一種理論來避免這種困境。正如他所說,他的構造器理論描述的是“一個物理過程中完全沒有概率和隨機性的世界”。這個理論是他正在與馬萊托合作完成的項目內容。理論的目的是要確定哪些過程是可能的,哪些是被完全禁止的。
構造器理論使用將可能和不可能相互轉換的陳述來表示物理學。它與熱力學最初的形式類似,因為它將世界的變化視為以循環方式工作的“機器”(即構造器)產生的東西,遵循著名的卡諾循環的模式。卡諾循環于19世紀提出,用來描述發動機如何工作。構造器就像一個催化劑,促進某個過程順利進行,并使系統最后恢復到原來的狀態。
“假設你開始了一個變化過程,比如用磚頭蓋房子,”馬萊托說,“你可以想象有許多不同的機器來完成這一過程,并且具有不同的精確度。所有這些機器都可以叫作構造器,它們在同一個循環中工作。”——當房子建成時,它們就會恢復到原來的狀態。
執行某項任務的機器可能存在,但這并不意味著它也可以執行該任務的逆過程。建造房屋的機器可能無法拆除房屋。這使得對構造器的操作不同于描述磚塊運動的運動定律的操作,因為后者是可逆的。
馬萊托說,這種不可逆性的原因在于,對于大多數復雜的任務,構造器都只適合在給定的環境中工作。它需要與該任務相關的環境的一些特定信息。但是反向的任務是從不同的環境開始的,因此同樣的構造器就不一定有效了。“這臺機器只適用于它工作的環境。”她說。
最近,馬萊托與牛津大學的量子物理學家弗拉特科?韋德拉爾(Vlatko Vedral)及其在意大利的同事合作證明,構造器理論確實表明存在不可逆的過程——即使一切都是根據本身完全可逆的量子力學定律發生的。“我們發現了一些轉換過程,你可以找到沿著一個方向工作的構造器,但在另一個方向它就不能工作。”她說。
研究人員考慮了一種涉及量子比特狀態的轉換過程。這種過程可以存在于兩種狀態中的一種或兩種的組合或疊加中。在他們的模型中,當單個量子位B與其他量子位相互作用時,它可能會從某個初始的、完全已知的狀態B1轉換為目標狀態B2,一次移動一個量子位。這種相互作用使量子比特糾纏在一起:它們變得相互依賴,因此你除非查看了所有的量子比特的狀態,否則無法完全描述其中一個量子比特。
馬萊托說,隨著量子比特數量的增多,我們可以根據需要將B帶入狀態B2。B與量子比特行的順序交互過程構成了一個類似構造器的機器,將B1轉換為B2。原則上,你也可以逆向進行該過程,將B2轉回B1,只要將B沿量子比特行送回即可。
但是,如果在完成一次轉換后,你想要使用新的B讓量子比特的數組重新經歷相同的過程,那該怎么辦?馬萊托及其同事發現,如果行中的量子比特數量不是很大,并且同一行被重復使用,那么從B1到B2的轉換會越來越難以發生。但至關重要的是,根據理論預測,這一行也更難進行從B2到B1的反向轉換。研究人員使用B的光子和光纖電路來模擬一行三個量子比特,從而證實了這一預測。
“你可以在某個方向上任意逼近構造器,但在另一個方向上不行。” 馬萊托說。轉換存在不對稱性,就像熱力學第二定律描述的那樣。這是因為轉換將系統從所謂的純量子態(B1)轉變為混合態 (量子比特與行糾纏在一起的B2)。我們將已被完全知曉的狀態稱作純粹的狀態。但是當兩個物體糾纏在一起時,你無法因為自己對其中一個完全了解就把它們分辨開。實際上,從純粹的量子態到混合態比逆向過程更容易——因為純態中的信息由于糾纏而散開,很難恢復。就像在墨水分散在水中后試圖重新形成墨滴一樣,這是熱力學第二定律約束下的不可逆過程。
因此,這里的不可逆性“只是系統動態演化方式的結果”,馬萊托說。它與統計無關。不可逆性不僅是最可能的結果,也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因為它由系統組成成分的量子相互作用決定。“我們猜想,”馬萊托說,“熱力學的不可逆性可能正是來源于此。”
機器中的妖
不過,還有另一種思考第二定律的方式。蘇格蘭科學家詹姆斯?克拉克?麥克斯韋(James Clerk Maxwell)首先提出了這一觀點,并與玻爾茲曼一起開創了熱力學的統計觀點。麥克斯韋沒有意識到,我們可以將熱力學定律與信息學聯系起來。
麥克斯韋對宇宙熱寂和似乎破壞了自由意志的變換規則以及它們背后的神學含義感到困擾。所以,在1867年,他想方設法在第二定律中“挖坑”。在他假設的場景中,一個微觀生物(后來人們稱其為妖,這很令他煩擾)將“無用”的熱量重新轉化。麥克斯韋先前已經得出了熱平衡氣體中的分子能量分布情況,并且知道,有些分子比其他分子“更熱”——它們運動得更快,能量也更多。但它們都是隨機混合的,所以似乎沒有辦法利用這種差異。
麥克斯韋妖將氣體隔間一分為二,然后在它們之間安裝一個無摩擦的活板門。它讓在隔間周圍移動的熱分子沿一個方向通過活板門,但不能通過另一個方向。最終,門的一側有熱氣,另一側有冷氣,麥克斯韋妖可以利用溫度梯度來驅動機器。
麥克斯韋妖對分子運動的利用顯然破壞了第二定律。因此,信息是一種資源,就像一桶石油一樣,可以用來工作。但由于這些信息在宏觀尺度上隱藏了起來,我們無法利用它。正是這種對微觀狀態的一無所知迫使經典的熱力學需要涉及平均值和集合的思想。

卡爾加里大學物理學家卡洛?瑪麗亞?斯坎多洛
近一個世紀后,物理學家證明,從長遠的角度來看,麥克斯韋妖不會違背熱力學第二定律,因為它收集的信息必須存儲在某個地方,任何有限的記憶最終都必須被抹去,以便為更多信息騰出空間。1961年,物理學家羅爾夫?蘭道爾(Rolf Landauer)表明,如果沒有耗散掉一些少量的熱量,就永遠無法擦除信息,從而提高周圍環境的熵。所以,熱力學第二定律只是推遲發生,而不是被打破。
從信息的視角看熱力學第二定律,這是一個量子問題。人們認為,量子力學是一種更基本的描述——麥克斯韋妖在本質上將氣體粒子視為經典的臺球。但它也反映出人們對量子信息理論本身的興趣日益濃厚。我們可以使用經典理論無法企及的量子原理來處理信息。尤其是粒子的糾纏特性,這使得我們能夠以非經典的方式傳播和操縱它們的信息。
最重要的是,量子信息的方法可以擺脫熱力學經典觀點中的復雜統計思想。在經典的熱力學中,我們必須對許多不同的微觀狀態的集合取平均值。卡爾加里大學的卡洛?瑪麗亞?斯坎多洛(Carlo Maria Scandolo)說:“量子信息的真正新穎之處在于,人們可以用研究對象與環境的糾纏來代替整體。”
他說,這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只有關于狀態的部分信息——不同的微觀狀態具有不同的概率,因此我們必須對概率分布取平均。但是量子理論提供了另一種產生部分信息狀態的方法:糾纏。當一個量子系統與它的環境糾纏在一起時,有關系統本身的一些信息會不可避免地丟失:最終,它會處于混合狀態,就算是理論上你也無法通過只關注量子系統而獲取它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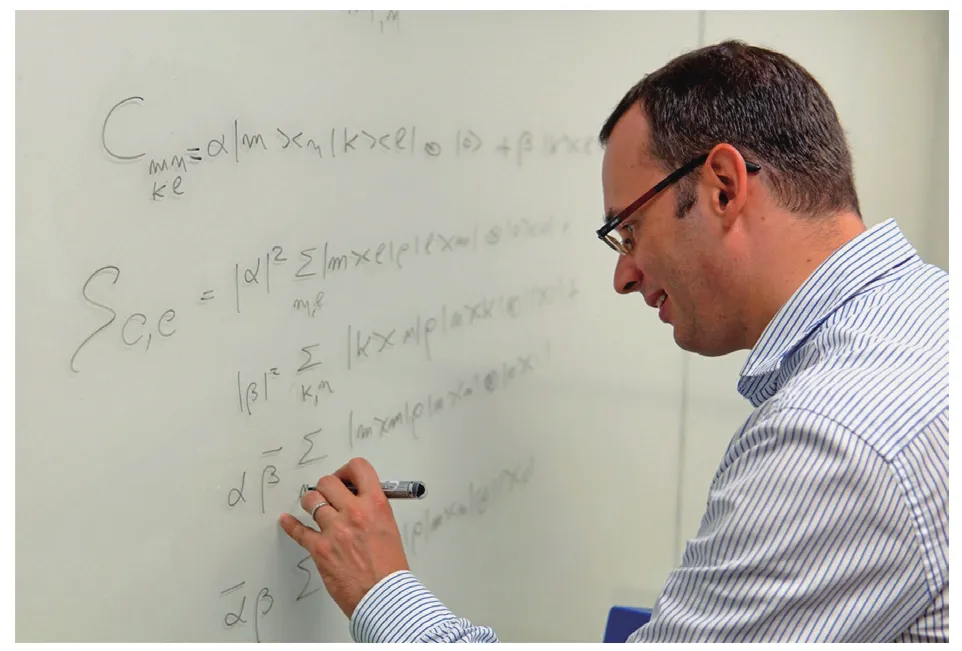
香港大學物理學家朱利奧?奇里貝拉
你只能去描述概率,不是因為你沒有得到系統中的某些信息,而是因為其中一些信息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不可知的。通過這種方式,“概率自然地從糾纏中產生,” 斯坎多洛說,“只有在存在糾纏的情況下,通過考慮環境的作用來了解熱力學行為的想法才有效。”
這些想法現在已經可以被精確實施了。斯坎多洛與香港大學的朱利奧?奇里貝拉(Giulio Chiribella)合作,提出了四個關于量子信息的公理,這些公理是獲得“合理的熱力學結論”所必需的——換句話說,這些公理與概率無關。公理描述了與環境糾纏在一起的量子系統中信息的約束。更重要的是,系統和環境中發生的一切原則上都是可逆的,正如量子系統如何隨時間演化的標準數學公式所暗示的那樣。

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物理學家妮可?容格?哈爾朋
重新定義熱力學
理解這種熱力學的全新量子版本的最通用方法之一,是調用所謂的資源理論——這一理論再次想要說明,哪些轉換是可能的而哪些不是。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的物理學家妮可?容格?哈爾朋(Nicole Yunger Halpern)說:“資源理論是一個簡單的模型,適用于我們可以執行的操作和可以訪問的系統由于某種原因受到限制的情況。”(斯坎多洛也將資源理論納入他的工作。)
量子資源理論采用了量子信息理論提出的物理世界的圖景,在這一圖景中,物理過程可能存在基本限制。在量子信息理論中,這些限制通常表示為“禁止定理”,它們給出“你不能那樣做!”的陳述。例如,從根本上來說,我們不可能復制未知的量子態,這種想法稱為量子的不可克隆性。
資源理論有幾個主要組成部分。允許的操作被稱為自由操作。“一旦你指定了自由操作,你就定義了理論的核心內容——然后就可以開始推理,哪些轉換是可能的,并進一步研究執行這些任務的最佳效率是多少。”哈爾朋說。資源是我們可以訪問并操作的東西——它可以是一堆煤,用來點燃熔爐并為蒸汽機提供動力。或者也可以是額外的記憶,使得麥克斯韋妖在更長的時間尺度上顛覆熱力學第二定律。
量子資源理論可以對經典的熱力學第二定律的細節進行放大。我們不必考慮大量的粒子,只需對其中一些內容進行研究。哈爾朋說,當我們這樣做時,很明顯,經典的熱力學第二定律(最終熵必須等于或大于初始熵)大體上只是各個不等式關系的總和。例如,在熱力學第二定律中,你可以將非平衡狀態轉變為更接近熱平衡的狀態。“但是,想要知道在這些狀態中,哪個更接近熱平衡狀態,這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哈爾朋說,“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對一大堆不等式進行檢查。”
換句話說,在資源理論中,似乎存在很多微妙的定律。“因此,可能存在一些轉換,它們處于傳統的熱力學第二定律允許的范圍內,但被這個更詳細的不等式集合禁止。有時我覺得每個人(在這個領域)都有屬于自己的熱力學第二定律。”哈爾朋說。
維也納大學的物理學家馬庫斯?穆勒(Markus Müller)說,資源理論“承認熱力學定律在數學上可以由完全嚴格的推導得出,在概念上和數學上都是嚴密的。”他說,這種方法“重新考慮了熱力學的真正含義”——它并不僅僅關注大量運動粒子的集合的平均屬性,更是在描述一場智能體與自然對抗以有效地執行資源利用任務的競賽。總而言之,熱力學仍然可以說與信息相關。哈爾朋說,信息的丟失——或者是無法跟蹤——確實是熱力學第二定律成立的原因。

大衛?希爾伯特提出的23個問題指導了20世紀的許多數學研究工作。他的第六個問題是,物理定律是否可以公理化
希爾伯特問題
這些重建熱力學和熱力學第二定律的努力讓人想起德國數學家大衛?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提出的挑戰。1900年,他提出了23個亟待解決的數學中的突出問題。這一清單中的第六項是“通過公理處理那些數學已經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物理科學”。希爾伯特認為,他那個時代的物理學似乎建立在相當武斷的假設之上,他對此十分擔心。他希望看到物理可以變得更嚴謹,就像數學家試圖在自己的學科中推導基本公理一樣。
今天,一些物理學家仍在研究希爾伯特的第六個問題,特別是嘗試使用比傳統公理更簡單、物理上更透明的公理來重新表述量子力學及其更抽象的版本,即量子場論。但希爾伯特顯然也考慮到了熱力學,他指出的物理學中使用的“概率論”思想如今已經相當成熟了。
希爾伯特的第六個問題是否可以在熱力學第二定律上解決,這似乎是一個個人傾向的問題。“我認為,希爾伯特的第六個問題遠未完全解決,它是物理學基礎中一個非常有趣且重要的研究方向,”斯坎多洛說,“仍然存在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但我認為只要投入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它們就會在可預見的未來得到解決。”
不過,也許重新推導熱力學第二定律的真正價值并不在于滿足希爾伯特的鬼魂,而是在于加深我們對定律本身的理解。正如愛因斯坦所說,“一個理論的前提越簡單,它就會越令人印象深刻”。 哈爾朋將研究熱力學第二定律的動機與文學家重新分析莎士比亞的戲劇和詩歌的原因進行了比較。我們進行這樣的研究,不是因為這種新的分析“更正確”,而是因為意義如此深刻的研究對象是我們無窮無盡的靈感和洞察力的源泉。
資料來源Quanta Magaz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