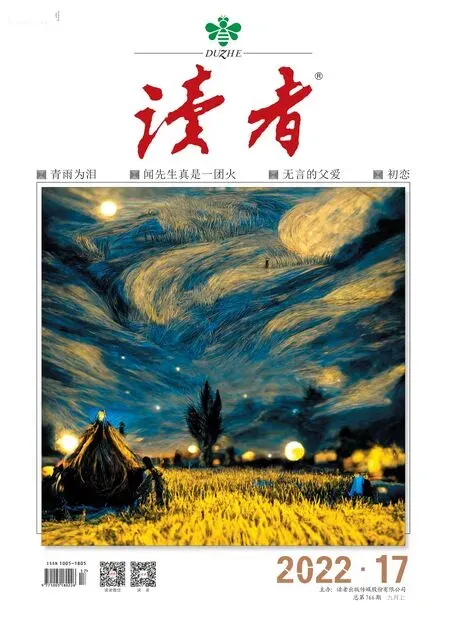一場教育實驗中的“折疊人生”
☉紀佳文 李小趣
看著紀錄片《真實生長》里的李文婷,方宇覺得她太乖了,甚至為她感到惋惜,“她曾經生活在那么一個充滿理想主義的地方,但她沒有發現”。這個被理想主義環繞的地方,是北京市十一學校。10年前,一場素質教育改革的大幕在這里拉開。《真實生長》的拍攝也以此為契機,記錄了2012級學生3年的高中時光。
面對鏡頭,李文婷說著對學業的焦慮,關于她的場景,大多也與功課有關。方宇則和紀錄片的另一位主人公周子其尖銳地抨擊著學校的各種規定,這是學校鼓勵的“批判精神”。
可如果把這種比照延伸到10年之后的現在,羨慕又變成了唏噓。進入社會以后,李文婷表現出更加舒服自然的狀態,方宇和周子其們,則經歷了與現實規則的艱難適配。
這樣一場教育實驗,究竟是要培養出怎樣的學生?
“考所重點”
方宇記不清六年級參加了多少場考試,才最終通過十一學校的選拔,進入了“2+4”學制的實驗班,可以直升本校高中。對于那場選拔考試,方宇一直記得那道他唯一準確作答的題目:假設用一根鐵絲緊緊箍住地球,在熱脹冷縮的作用下鐵絲膨脹了5米,問此時它與地球的縫隙能否鉆過一只老鼠?他至今都很感慨:“寧愿再參加一次高考,也不愿意再參加一次小升初了。”
當方宇早早開始經歷應試選拔的壓力時,在距離北京300多公里的山西大同,李文婷的生活還是平靜松弛的。她是那種傳統意義上的乖孩子、好學生,成績一直很好。李文婷的爸爸是鐵路職工,媽媽是工廠化驗員,父母對她的學習沒有太高要求。她有大把的時間和小伙伴們出去玩,或是帶上讀書卡去泡書店。她還讓父母給自己報了電子琴、書法和舞蹈的興趣班。
海淀區的小升初“雞娃”故事,并沒有在小縣城里上演。這個人口不足20萬的縣城里,只有兩條升學通道:劃片分配或是進私立學校。
李文婷被分到了縣里最好的公立初中,她還是報了輔導班,理由是“大家都報了”。初三那年,因為爸爸工作調動,李文婷轉學到北京市懷柔區的一所普通中學。兩地教材不同,爸爸擔心她跟不上進度,提出讓她留級。但李文婷不想,她買了練習冊“加碼”,成績依然是班里最好的。
對于李文婷,做“好學生”已然成了一種習慣,考出好成績,然后受到表揚,她很享受這種感覺。除了這種認可,她還有個短期目標:即將到來的中考,她至少也要“考所市重點”。
定 位
2011年,北京十一學校被確定為國家辦學體制和高中特色發展改革試點。取消行政班級,實行走班制,課程分層、學生自主選課、開設大學先修課程……這正應了方宇的心意,他一直討厭一切都被安排好的生活。
直升班沒有中考的壓力,方宇早早選擇了自己更擅長的文科。教育改革后,校園里隨處可見各種活動海報,社團一個接一個冒了出來。他參加了辯論隊、模擬聯合國,這些讓他覺得自己像個大人了,“自己的想法會被老師重視,可以和老師平等溝通”。
2012年,李文婷也以全校第一、全區前二十的中考成績進入十一學校。但作為一名后來者,她需要更多的努力,去適應這個全新的體系。
這好像一個學會“獨行”的過程。選課制下,每個學生的課表是獨一無二的,李文婷要自己安排上課、自習、活動的各種事項。但在她就讀的初中,時間是被老師安排好的,自己要做的只是執行。到了十一學校,她就像一直被長輩牽著手的孩子,突然被甩開了手。
她也參加了廣播站、明信片社、做手工的社團,下午的自由時間幾乎都用在了興趣活動上,但她總覺得這不完全是一件好事。入學后第一次考試,理科300多人,李文婷排200多名。拿到成績單,她一個人哭著走回宿舍。她沒有想過,自己的成績會變成這樣。
她有些懷念初中,初中的老師會盡可能多地講課,用她的話說,是大全景式的掃描,成績一下降,老師就會找她談話。但在十一學校一位任教近20年的老師看來,這些是“無用功”,甚至會對學生起反作用。這場教育改革,不光是為了讓學生掌握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更是要培養他們的“自我意識”,讓他們學會規劃自己的生活,為自己的決定負責。
無論以何種方式進入這場教育實驗,他們都經歷了一個重新尋找“定位”的過程。
在沒有講臺的教室里,課桌被擺成一個圓圈,方宇等幾個同學和老師圍坐在一起,泡上幾杯茶,討論甚至激辯著對各種話題的看法。在歷史課上講授馬克思主義之前,他接到的任務是閱讀《共產黨宣言》;讀罷余華的《在細雨中呼喊》,他和老師討論那些天馬行空的辭藻。
在這個不只以分數為標準的評價體系里,方宇發現,同學們在成績之外各有擅長,比如一位初一初二時成績不太好的同學,在學生會的工作中表現出很強的工作能力。方宇自己也因為體育和藝術成績優異,被評為“卓越學生”。
李文婷依然在為提高成績努力,聽從導師建議,把更多自由的時間用在自學上。慢慢接受了自己是一名中等生后,她的成績反而穩步上升。高二下學期,她進步了100名左右,拿到了“雙科飛躍獎”。
獨 立
2022年2月,李文婷坐在紀錄片《真實生長》的首映現場,看著多年前的自己,她有些不好意思。和片中其他兩位主人公相比,她顯得安靜又羞澀。
作為紀錄片的另外兩位主人公:陳楚喬喜歡寫小說,聽萬能青年旅店的歌,高二時她和同學一起拍攝了一部僵尸題材的電影,在學校上映后,獲得了7000多元的票房;周子其和同學們給校長寫了一封信,直接影響了學校之后的軍訓改革。
高一開學,同學們發現學校食堂飯菜漲價,菜品味道也不如從前。“菜品的更換,有沒有考慮過我們學生的意見?飯菜成本是不是應該公示?是否要建立溝通渠道?”帶著這些問題,負責管理食堂的老師、三家供應商的經理和學生代表們開了一次會,最終決定,食堂要將飯菜成本進行公示,學生有異議可以通過相關老師反映給食堂。
時任十一學校校長的李希貴在文章《學生第一》中寫道:“只有認真傾聽,才能讓學生產生更多更好的想法。讓學生參與到對學校真實問題的解決中來,是我們培養學生能力的一個重要方法。”
“康川新城”這一 “農轉居”地區從村落模式完全發展轉變為社區模式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由于發展相對落后,社區矯正工作的經費保障、科技運用、監督管理等相關配套機制尚不健全。
方宇和周子其做的那些事,都不在李文婷的考慮范圍。在她還是個尖子生的時候,她就不喜歡成為人群的焦點,也不想和別人不一樣。如果覺得一些規定是不合理的,她習慣的是去適應,小學和初中的教育環境讓她意識到,“別的地方不是這樣的,出了十一學校,沒有人會接受你這么做”。
在十一學校的體系里,如果說方宇得到了自由,李文婷則得到了“試錯”的機會。兩三百門選修課擺在面前,李文婷選了從沒有接觸過的法語、Java編程、3D打印建模,她覺得這些課名聽起來很“高大上”,但課程比她想象中難學。
這是一個“排雷”的過程,通過不斷嘗試,李文婷意識到哪些東西是不適合自己的。她猜想,如果沒有這些試錯的經歷,在填報高考志愿時,她大概率會選擇熱門的計算機專業。
她也找到了自己喜歡的東西。做數學題時,李文婷總覺得時間過得飛快,有時一抬頭,兩個小時就過去了。她很喜歡經過思考后豁然開朗的感覺,這種對數學的喜愛,直到上大學也沒有改變。
她學會了獨立做出選擇,但還是沒法在這樣自由的氛圍里,完全“放開自己”。對于那些落差和不適應,她更愿意看成一種財富。“有些東西早晚要經歷的,早點來未必是壞事”。
要改革,也要分數
方宇與李文婷好像平行線似的高中生活,在高三發生了交會。提起這一年,二人先想起的都是數不清的考試,他們都聽到了老師那句告誡:“硬仗要來了,你們不能像高一高二那樣玩了。”
高二下學期,要和高三學生一起參加二模考試,因為沒把握,李文婷失眠了好幾天。當進入高三,晚自習時間從九點半延長到十點半,即使沒有強制規定,大部分學生仍選擇主動留到最后。老師們也一直在自習室,方便隨時答疑。
和考試一起來到的,是年級排名。成績單上,歷次考試的排名被制成折線圖,提醒著每個學生在年級中的定位。老師們根據考卷和分數寫下評語,從哪門學科稍顯弱勢,具體到語文學習需要加強背誦。
在李亮看來,這是對十一學校教育理念的誤讀。“我們對學生絕對不是放養,而是更全面地關注。”李亮說,月考出成績,學生要寫總結分析,這是從高一就有的慣例,期中、期末考試后,學生也要對著試卷總結反思,這些都是在訓練解決高考這張試卷的能力。
年級給每個學生建立了學生檔案,老師們被分到不同的項目組,分別關注學生的學習、生活、紀律。
真實生長
李文婷的高考成績是630分,高出一本線80分左右。初中時和她成績差不多的同學,大都考出了比她更好的成績。


紀錄片《真實生長》放映活動現場
她也設想過,如果在自己更適應的應試教育體系里,也許能獲得更高的分數,讀一所更好的大學。但這個假設沒有給李文婷帶來太多苦惱,她被首都經貿大學的保險精算專業錄取,后來又被保送到對外經貿大學讀研究生。她很慶幸,因為在高中就明確了對數學的熱愛,選擇了一個喜歡的專業,沒有“擰巴”地度過4年。
“平平淡淡才是真”,這是李文婷爸爸的教育理念。“正常人的生活不見得比優秀的人不幸福”。高中時期的她不認同父親的想法。她想到頂級的外企工作,和職場劇里的女主角一樣,穿著職業裝、高跟鞋,賺很多錢,過著女強人的光鮮生活。
但那3年的經歷讓她早早接受了“落差”。就像高中考試后,她會用看電視劇的方式犒勞自己,而學霸會立刻投入學習一樣。在大學,身邊同樣有更優秀的人存在。一個男生從研一就在頂級證券公司實習,每天搭末班地鐵回學校,早晨5點依然去操場跑步。李文婷很佩服他,但也很確定,這是自己永遠也達不到的狀態。她更愿意在下班后做做晚飯、看看“不費腦細胞”的綜藝節目。她逐漸意識到,自己想要的其實是一種平淡安穩的生活。
有些東西一直沒變,比如她依然是個不喜歡“反抗”的人。畢業后她進入銀行工作,有顧客因為錯過叫號投訴,她不覺得自己有錯,但還是按領導要求寫了檢查。
離開十一學校之后,方宇遭遇了“落差”。方宇高考沒能被歷史系錄取,便讀了新聞專業。一心想要學歷史的方宇無法接受這個結果,雖然十一學校留給他的獨立和質疑精神還在,但他也體會到了某種無力,“在很多地方,甚至連意見反饋的渠道都找不到”。
一位老師表達過,十一學校希望培養出的,是各行各業的領軍人才。但這或許就是教育實驗的復雜之處,越是在當中表現出眾的學生,越可能在重新適應現實規則時,經歷摔打。
高考后,周子其被北大歷史系錄取,這本來是他喜歡的專業,結果他發現,歷史系注重史料考據,和他關注的現實問題相去甚遠。他帶著失望修讀了經濟學雙學位,之后又去芝加哥大學讀了公共政策專業的研究生。2021年7月,周子其入職了一家教培機構,隨即又被裁員。現在,他在北京市海淀區一家留學咨詢機構工作,工作和專業并不對口,好在“加班不多,收入還行”。
陳楚喬高中畢業后,到紐約視覺藝術學院學了電影專業,回國后參加了幾個影視劇項目。為了實現導演夢,她要從場記這樣最基礎的工種做起。但她對所謂的落差沒有明顯的感覺。與大多數畢業生的感受不同,她覺得十一學校更像一個微型社會,這種感悟,讓她在面對各種差異與變化時,總能保持一份平常心。
在豆瓣網關于《真實生長》的1000多條評論里,有人說:“羨慕周子其和陳楚喬在那樣的年紀就能夠認識自我,但不得不承認,更多人的高中形象,是李文婷。”
方宇逐條看完了評論,他到現在還保留著十一學校的錄取通知書,上面寫著:“十一學校,你一生的驕傲;十一學生,一個偉大的稱號。”現在,他嘗試著用不同的視角去審視那幾年的時光。
比如那次爭取自由活動時間的事件,年級主任王春易后來對著鏡頭說出了自己的委屈:“我辦公區的門是天天開著的,有諸多可以溝通交流的方式,但我沒有聽到他們的任何聲音。”
看過紀錄片的這段采訪后,方宇給王春易發了條短信致歉:“雖然時隔久遠,還是深感有愧于老師們的良苦用心。那一年元旦聯歡會您來一起參加,還跟我們道歉,但其實是我們應該為自己造成的麻煩道歉,未能以合理的渠道反映問題,和老師們共同進退。我現在也參加工作了,特別能體會老師們在當時的那種無奈,還有我們的年少輕狂,感覺非常慚愧。”
隔天,他收到了王春易的回復:“你們反映同學的訴求,讓老師發現了真實的學生,給我們提供了教育的契機,我們同樣獲得了專業的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