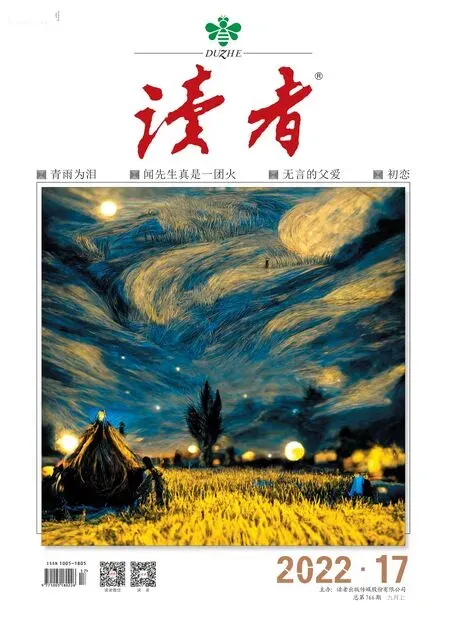黑白色的記憶
☉孫世豪
[1]
外公站在椅子上,從家里最高的柜子上,把“爸爸”取了下來。那時的我還小,還不知道為什么。
“回去畫畫,小孩子別多管閑事,待會叔叔來的時候乖一點兒……”
我跑進爸爸曾經的臥室,坐在他曾經坐過的位置上,看著書架上以前他最喜歡看的書,望了望他那因無人照料而枯萎的向日葵,拿起鉛筆,想在一張空白的素描紙上留下些什么,但遲遲難以落筆。于是我開始回想從前,希望能在時光里找回一絲快樂,但我的記憶是一片空白。
叔叔走后,媽媽和外公外婆看起來很高興,媽媽把白玫瑰插到花瓶里,擺在向日葵旁邊,走到遠處看了看。
“向日葵還是扔了吧……”她有著那么一絲不舍。但她還是抱起花盆,將它放在了家門外。處理好事情后,她來看我了。

“壯壯,你畫了什么呀?”接著,她看了看我的畫紙,愣住了。
被眼淚打濕的素描紙皺巴巴的,歪歪扭扭的灰色鉛筆字也因淚水而變得不再清晰。上面的內容依稀可見,一個小男孩和爸爸一起在公園寫生,畫小鳥,底下還配著一行小字:我想爸爸……
我不了解,也不敢去了解媽媽的看法,但從她撕掉整幅畫的行為來看,她也許生氣了,或許,也和我一樣難過。
半夜,我還在想著那盆向日葵,我覺得我和爸爸一樣都喜歡它,爸爸也很想它。我不想它被丟掉,于是悄悄溜下床,跑到門口,試著把花盆搬進來。
借助著微弱的光芒,我好像又一次看到了彩色的花盆,看到了和爸爸一起在金色陽光下澆灌向日葵的日子。
“哐當!”
家里人趕忙走進客廳,打開白色的大燈,只見我靠在灰白色的墻上,看著地上被黑色泥土覆蓋的彩色花盆碎片,痛哭流涕,手上流著鮮紅的血……
[2]
門鈴響了。
那天是我的初中班主任來家訪的日子,外婆和媽媽一反常態,滿臉掛著笑容,迎接老師的到來。我站在一旁,看著老師走進我的家門。
媽媽從鞋柜里翻出一雙白色的一次性拖鞋,遞給老師,隨后微笑著領著她走向桌前。我知道她只是在試圖給老師留下一個好印象。但老師并沒有領情。有些高齡的她頂著一頭剛被染得烏黑的鬈發,扶了扶眼鏡,一臉冷漠。
“以后我會接手上一任班主任的工作……”
她開始說起學校的事情,但我的思緒早已像往常一樣開始飄揚,我只看見我一個人穿著灰色的校服,在白茫茫的雪地里奔跑,尋找著他的身影。
“我的孩子有些特殊,他上小學時就沒什么朋友,性格也比較內向……”
我在雪地里漫步,看不到任何人,更找不到父親在哪里,但我還是漫無目的地四處游蕩,好似一個人在漆黑無燈的黑夜之中。
“他從小就失去了父親,受了點兒刺激,一直沒走出來……”
我突然看到一串腳印,順著腳印的方向,我看到前方有一個人,他的身影是如此熟悉,卻又如此陌生。
“我們一直都在試著了解他的內心,但是我們體會不到他的那種感受……”
我向前狂奔,努力試圖追上那個身影,淚水不自覺地奪眶而出,滴落下來。我的視線也逐漸變得模糊。眼前的身影變成了一團黑灰色的亂麻。
老師面無表情,扶了扶眼鏡,鏡片反射了白色的燈光,白光直射入我的眼中,亮得我睜不開眼。
我看見那團黑灰色不斷變大,膨脹,瞬間吞噬了我的視線,吞噬了周邊的一切,最后吞噬了我。
她轉過頭,看著我。
“這沒什么問題。雖然他的父親過世了,但我相信其他的愛總能彌補的……”
我的眼前,此時只有一片黑暗。
“不,你們永遠不會理解!”
我憤怒地拍了一下桌子,猛地站起身,睜開眼睛。
“有些愛,有些人,有些記憶,是永遠無法被代替的……”
我頭也不回地離開客廳,走回房間,關上了房門。
[3]
“你是幾號?”
“40。”
“這是你的藥,吃掉。”
我將白色的藥片送入口中,喝下一口水。
“張嘴。舌頭抬起來。”
我張開嘴巴,抬起舌頭。
護士看了看,從白大褂里掏出記事本,在紙上寫下記錄。
“40號精神狀態正常,配合治療。”
吃完藥,病人們開始各種娛樂活動,有些人搬起椅子,湊到電視前,看著電視上的節目;有些人則是扎堆在一起打牌,引來不少人圍觀,期待拿著黑桃3的那個人打出第一張牌;還有的則是坐在椅子上望著窗外黑色的夜空和皎潔的月亮。
我與自己下起了國際象棋,我執白,也執黑。一段時間后,黑王便倒下了,我不禁想起父親逗我開心的樣子。
我掏出日記本,開始寫今天的日記:
“第44天,還要一段時間我才能出院。家里人覺得我的思想生病了,實則不然:生病的的確是我,但也不只是我,只是誰輕誰重罷了。有時候真希望我會被診斷出什么重病、絕癥,這樣我也可以向生活示弱,得到他人的同情。而不是這種病,沒有同情,只有不解……”
寫到這里,黑色的字跡變得斷斷續續,原來是鋼筆沒墨水了。我拿出鉛筆,接上剛才的話。灰色的字與黑色的字產生了明顯的反差。
“我感覺到孤獨,一種奇異的孤獨,一種別人不經歷就不會理解的孤獨。就好比你用著自己的語言,卻來到了一群外國人中,沒人知道你在說什么。而孤獨的我,只能期待,有另一個同樣孤獨的人能找到并理解我的言語。”
寫到這里,剛好寫完一張紙,我注意到筆記本的下方還有一個小小的圖案,是一朵黃色的、鮮艷的向日葵,面朝我,在微笑。
[4]
“能和我說說你現在的想法嗎?”
“我想念我的父親。”
“但是你知道的,人死不能復生。”
“所以我難過,我痛苦,我無法接受。我希望我也能去另一個世界,去找他。只有有他的世界才是彩色的。”
“為什么這么認為?”
“我不想說。”
“你一直強調的東西往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愿意說的。試著把它說出來吧。這才是我們心理咨詢最重視的東西。”
“我……我……”
“慢慢來。”
“因為,我的記憶里,只有有他的那一部分,才是讓我真正感覺快樂的部分。可隨著他的離開,我的快樂也離開了。”
“繼續說。”
“我……我渴望回憶起那份快樂,可我漸漸地,再也感覺不到快樂。當我小時候,看著父親的向日葵從黃色慢慢枯萎,變成黑色,我發現我身邊的一切也開始變為黑白。家里的花從漂亮鮮艷的向日葵,變成了一成不變的白色菊花;因為沒有人看電視,家人再也不付有線電視費,打開電視只會看到雪花點;還有一抬頭就能看到的父親的照片,可連他也變成了黑白的。”
“難道你就再也沒有看到過其他顏色嗎?”
“不,我看到過。”
“那是什么?”
“紅色,血液是紅色的。”
“沒錯,但是你想想,血液是紅色的,這代表什么?這代表你心里依然是有色彩的……”
“我心里還有色彩嗎?我的記憶再也沒能出現彩色!”
“不,只要你還活著,你就是彩色的。只要你的血管里還流淌著你父親為你留下的生命之血,你就是彩色的。”
“為什么?”
“的確,你再也沒有看到彩色,但是,有沒有可能,從來就沒有彩色?”
“什么?”
“彩色本來就不存在,它只是一種感覺。你真正懷念的,正是那種感覺,那種名為父愛的感覺。你無數次地追尋彩色,就像小時候留下父親的向日葵一樣,希望找回父愛,但有些失去的必然無法回來。”
“那我又該怎么辦?”
“拋下彩色吧。”
“什么?”
“那根本不重要了,因為只有在一切被打破之后才會出現新生;只有在死亡之后,才會迎來復活;只有在黑白后,你才能再次看到彩色……所以,回到一切的根源上吧,為了你鮮紅的血液,而彩色的含義就是……”
“黑白……沒有任何意義……只是為了我的父親,而繼續堅強地活下去,不受所謂黑白的煎熬,不再沉溺于過去的色彩……”
有時我反思,為什么自己——以及許多其他的讀書人——會對楊過和令狐沖這些身具傲骨、獨行江湖的虛構人物如此情有獨鐘。我的解釋是,他們實際上是改裝成劍客的知識分子。而且由于他們都是有著完美結局、最終獲得了同情和理解的大俠,他們圓了我們既盼望獨善其身又希求兼濟天下的夢想。
——巫鴻《豹跡》
“那你現在看到了什么?”
“我的眼前,我的眼前是……”
[5]
我走在公園里,金黃色的陽光灑在大地上,春日的陽光十分溫暖,剛出冬的日子,令人感到愜意。
樹上,粉色的櫻花正在開放;樹下,綠色的草地正在不斷蔓延。
殘雪正一點點地融化,消失,直至不見。
我向前走去,看見一位中年男人正端著畫板寫生,畫的是面前的一只喜鵲。
那個男人的背影有些熟悉,像極了父親。他戴著黑色的帽子,穿著灰色的休閑服,拿著鉛筆,專心致志地畫著。
喜鵲黑白相間,有著藍綠色的尾巴,十分好看,我忍不住想走近些觀察。即使我已十分小心,卻還是驚動了它。那個男人看到喜鵲飛走了,也停下了手中的筆。
我向他走去,給他道歉。
“抱歉,我不小心嚇跑了它。”
男人摘下帽子,我看到了他已然斑白的鬢角,若父親健在,可能也是這樣吧。他對著我笑了笑,露出雪白的牙。
“沒關系,我已盡數記在腦中……”他說道。
我也笑了笑。
“是呀,我也全部記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