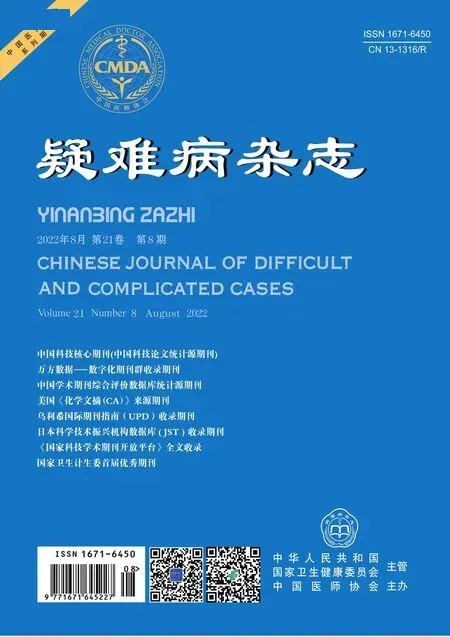APOL1基因變異相關性局灶節段性腎小球硬化研究進展
夏作勛綜述 黃朝暉審校
局灶節段性腎小球硬化(focal segmental glomerulosclerosis,FSGS)是一組比較常見的腎小球病變,在歐美國家FSGS是腎小球病變的主要原因之一[1],其發病率在我國也有上升的趨勢[2]。根據病因,FSGS主要分為原發性、繼發性及遺傳性。因其治療周期相對較長,加之部分患者治療后療效不佳或頻繁復發,乃至步入終末期腎臟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給國家醫療系統及患者家庭帶來了巨大的經濟負擔。
隨著人類基因測序技術的進步及對人類溶錐蟲效應的深入研究,有學者發現,載脂蛋白L1(apolipoprotein L1,APOL1)基因變異與FSGS相關[3]。APOL1基因相關性FSGS對現有藥物不敏感,常迅速發展至ESRD,故本文將對APOL1基因變異相關性FSGS的研究作一綜述。
1 APOL1基因突變概述
自1997年Duchateau等[4]發現了高密度脂蛋白家族中新的成員載脂蛋白L(APOL)以來,關于APOL的研究方興未艾。現有研究表明,APOL蛋白質分子的編碼基因位于人類第 22 號染色體上[5],目前共發現6種APOL蛋白分子(APOLⅠ~Ⅵ)。APOL1是APOL家族中唯一的分泌蛋白,為人類及部分高等靈長類動物所特有。該蛋白結構可分成3個不同的結構和功能區域[6]:(1)陰離子孔隙形成域,是一段被α螺旋包繞的長疏水發夾結構,參與溶酶體的滲透和細胞死亡;(2)膜定位結構域,由pH敏感的發夾結構橋接2個α螺旋組成膜定位區域,在中性pH條件下,該結構域露出疏水表面,使APOL1與高密度脂蛋白結合,在酸性pH條件下與細胞內的細胞器定位有關;(3)最后一個結構域是帶有亮氨酸拉鏈的C末端兩性分子的長串α螺旋,被認為參與蛋白質間相互作用。而對于APOL1基因變異廣為人知的研究是APOL1基因變異可以保護人類免受昏睡病的病原體布氏錐蟲侵襲(簡稱溶錐蟲效應)。目前研究表明,在非裔人群中APOL1基因變異主要與G1、G2 2個風險等位基因有關[7]。G1是指APOL1 C末端附近被2個氨基酸取代(S342和I384M);G2是一種雙氨基酸缺失(del388N389Y)。G1和G2相互排斥,從不發生在同一條染色體上,因此自然界有3種人群:第一種不攜帶G1或G2,即攜帶0個風險等位基因,第二種攜帶G1或G2中任意一個風險等位基因,第三種同時攜帶G1和G2 2個風險等位基因。
2 APOL1基因變異作為FSGS易患基因的研究
FSGS的大多數循證醫學證據來自于西方國家[8],我國對FSGS的研究開展尚不充分,且目前我國基層醫院基因檢測的開展率較低,現有研究暫未發現APOL1基因變異(G1/G2)型導致罹患FSGS,但我國人群中存在APOL1基因變異已得到了證實[9-12],APOL1基因變異廣泛存在非裔人群中,因而主要援引非裔人群的數據。
在Kopp等[13]的一項研究中表明,在美國發生ERSD的患者中大約有40%是罹患FSGS的非裔人群,其中72%的患者與APOL1基因變異有關。該研究發現在隱性遺傳模型下,攜帶APOL1中G1/G2風險等位基因純合子或復合雜合子的受試者,較不具有這類風險基因的受試者罹患FSGS的風險增加了17倍,且攜帶2個APOL1風險等位基因的FSGS患者腎臟存活時間顯著縮短。Genovese等[14]在研究中將不具有或只具有1個風險基因等位基因受試者與具有2個風險等位基因的受試者進行比較,同樣發現后者罹患FSGS的風險是前者的10.5倍。同時其提出了APOL1相關性FSGS基因變異可能是一種隱性遺傳模式。而Zee等[15]在對FSGS患者APOL1基因相關的形態學變化研究時發現,在FSGS患者中有著更為嚴重的腎小管損傷及系膜細胞增生。顯然APOL1基因突變與罹患FSGS有著密切聯系,極大可能是隱性遺傳,且有著更為嚴重的病理損害。
3 APOL1基因變異相關性FSGS發病機制
FSGS的發病機制目前尚不清楚,但足細胞損傷是FSGS發病機制中的核心環節[16-17],已得到世界范圍內學者的廣泛認可。Beckerman等[18]研究證明,APOL1風險等位基因的表達會導致足細胞功能改變從而發生腎小球疾病。了解APOL1基因在腎臟的定位對理解APOL1基因變異導致人類罹患腎病幾率增高有益。
Madhavan等[19]通過對人健康腎臟的組織切片、FSGS和HIV相關腎病(HIVAN)的病理切片進行研究,發現在健康腎臟足細胞、近端小管及中型動脈和小動脈內皮細胞均有APOL1表達。這一發現表明APOL1存在于正常腎臟中,結合此前學者研究發現,APOL1基因變異會影響患者血漿中血脂的運轉,從而增加發生心血管事件的風險[20-21],故APOL1可能在正常腎臟中發揮著功能性作用。隨著研究深入,發現在FSGS和HIVAN患者腎臟中,APOL1在足細胞中表達減少,而在中型血管平滑肌細胞和小動脈血管壁中APOL1表達顯著增加,APOL1是APOL家族中唯一的分泌蛋白,可隨血液循環到達各個器官,故在FSGS和HIVAN患者中APOL1在中小動脈血管壁內表達增加,但是從循環中攝取還是內源性表達所致尚不明確。隨著腎臟移植手術的大力開展,越來越多的證據更傾向于內源性表達,如Lee等[22]的一項回顧性研究發現,存在2個APOL1風險等位基因突變非裔美國人群,接受腎移植后,5年腎臟存活率并不受影響。Freedman等[23]研究結果也傾向于支持APOL1內源性表達這一論斷,在腎臟移植后受體體內腎衰竭進展的觀察中發現,攜帶2個APOL1風險等位基因的已死亡非裔美國人捐獻的腎臟,比不攜帶或攜帶1個APOL1風險等位基因的人捐獻的腎臟,在受體體內衰竭的更快。然而Kruzel-Davila等[24]卻認為此類研究的終點事件是移植后腎臟存活情況而不是FSGS的發病,且這些研究沒有同時對供體和受體進行基因檢測,因此內源性APOL1致FSGS患病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Ge等[25]的研究提示,APOL1在正常腎臟中可能發揮著功能性的作用,他們發現APOL1基因變異影響FSGS的足細胞脂質穩態和能量產生,在降低足細胞中的脂質含量時可改善APOL1基因變異介導的線粒體功能障礙。其研究也間接論證了“二次打擊學說”的可能性,即攜帶2個APOL1風險等位基因的個體并不會完全發生腎病,而是在某些因素驅動下致病。Zhang等[26]的一項研究結果也支持了二次打擊學說,他們發現UBD(一種泛素樣蛋白質修飾劑,可靶向蛋白質進行蛋白酶體降解)和APOL1在功能上相互作用,并且UBD表達的增高能減輕APOL1介導的細胞死亡。
近年研究發現,APOL1變異基因介導細胞死亡。Beckerman等[18]在其研究中提出了APOL1變異基因和炎性反應通路之間可能存在正反饋調節。APOL1變異基因受到炎性細胞因子調節,但其過表達會導致炎性細胞死亡,細胞死亡后釋放的細胞因子可以上調APOL1變異基因的水平,該過程細胞死亡包括了細胞焦亡,故炎性小體(NLRP3、Caspase-1)在APOL1變異基因研究中得到了關注。Wu等[27]通過研究發現,在APOL1基因變異的腎小球中,細胞溶質核苷酸傳感途徑(STING)和炎性小體(NLRP3、Caspase-1 和GSDMD)中各種關鍵蛋白被激活。此外在其培養的APOL1基因變異的足細胞中也觀察到細胞溶質核苷酸傳感途徑和炎性小體的激活。Wakashin等[28]則發現了APOL1-B3(一種 APOL1 亞型),可調節促炎信號,并與NLRP12(一種 Toll 樣受體信號調節劑)相互作用,促進足細胞和腎小管細胞中的炎性反應信號傳導,從而導致腎小球損傷。
內質網應激亦是導致足細胞損傷的因素,且與炎性因子有關,炎性因子可以上調APOL1變異基因的表達[18, 29]。Müller等[30]在研究中指出炎性因子上調內質網中順式(攜帶APOL1風險變異基因面向內質網管腔)、反式(攜帶APOL1風險變異基因面向內質網細胞質)APOL1變異基因過載,且變異的 APOL1基因會導致內質網的順式和反式方向都有細胞毒性作用, 從而導致足細胞損傷。
此外有關線粒體功能障礙、線粒體基因調控的APOL1基因變異致病機制也得到了不少學者的認可[31-32]。
4 APOL1基因變異相關性FSGS的診斷
腎穿刺活檢術對腎臟病的臨床診斷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行腎穿刺活檢術可明確腎臟疾病病理變化和病理類型,并結合臨床作出疾病的最終診斷,制定相應的治療方案。根據哥倫比亞病理分型[33-34],FSGS病理類型可分為非特異型、門周型、細胞型、頂端型、塌陷型(見表1),這一病理分型同樣適用于APOL1基因變異相關性FSGS。對于疑似APOL1基因變異相關性FSGS,行基因診斷是必不可少的,基因診斷不僅可以幫助臨床診斷,對治療方案選擇、預測疾病預后、產前診斷及腎移植也有重要意義[35]。

表1 哥倫比亞FSGS病理分型
5 APOL1基因變異相關性FSGS臨床特征及防治
APOL1基因變異相關性FSGS臨床特征仍然是腎病綜合征、高血壓、血尿、腎功能受損等,尤其腎功能具有迅速進展至ESRD的傾向,且與普通FSGS患者相比其腎臟存活率普遍較低[36-37]。這一現象提示應早期積極治療APOL1基因變異相關性FSGS。FSGS一線治療方案是口服足量激素治療(潑尼松1 mg·kg-1·d-1,最大劑量不超過80 mg/d),而這一方案在APOL1相關性FSGS同樣適用,現有研究表明,攜帶APOL1風險基因的患者使用激素、環孢菌素或霉酚酸酯等治療,其蛋白尿均得到了緩解,但其完全緩解率低于普通FSGS患者[36,38-39]。但目前沒有數據表明,用現有的FSGS常規藥物進行積極治療后,可以延緩APOL1基因變異相關FSGS進行性腎單位的毀損。
在預防APOL1相關FSGS發病方面,現有研究表明,并非所有攜帶APOL1變異基因的個體都會患上FSGS,環境影響在該類患者發病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有研究發現,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容易發生APOL1變異相關性腎病[40-41]。此外避免體內高干擾素狀態也是一個較好的預防措施,Nichols等[29]研究表明,內源性干擾素可上調APOL1變異基因的表達,從而導致人類罹患APOL1變異相關性腎病,病原體特別是病毒可觸發內源性干擾素反應上調APOL1變異基因的表達。近來也有攜帶APOL1 G1和G2 2個風險變異基因的患者在接受外源性干擾素治療期間出現FSGS的報道[42]。總之無論是外源性干擾素使用還是內源性干擾素升高都應預防APOL1變異相關性FSGS。
6 小結與展望
國外的流行病學數據表明,APOL1基因變異(G1/G2型)相關性FSGS主要流行于非洲及非裔美國人群,國內學者對一對同卵雙生FSGS患者的APOL1基因研究中發現新的錯義突變(c.C863T,p.T288I),該雙胞胎父母未攜帶該突變,且在深入研究后發現這種APOL1基因新突變對足細胞維持正常形態具有重要的影響,會造成足細胞的凋亡[9-10]。該研究提示我國APOL1基因變異相關性FSGS發生基因突變位點可能與非裔人群G1/G2型突變不一致,有待進一步研究證實。
盡管APOL1突變基因導致腎臟疾病問題的機制尚未完全揭開,但是二次打擊學說提醒臨床醫生不可忽視外界因素的參與,繼而導致炎性小體激活、內質網應激、線粒體功能障礙。近來有不少學者主張將APOL1基因變異相關性FSGS定義為新的FSGS類別,認為這種完全隱性遺傳模式不同于顯性遺傳性FSGS。此外APOL1基因變異相關性FSGS是目前非洲國家最常見的FSGS遺傳性形式。APOL1基因變異相關性FSGS較其他類型FSGS更為迅速地發展為ESRD,并且在腎移植方面對供體與受體有著更嚴格篩查。隨著對APOL1基因變異相關性FSGS的深入研究,將為改善該類疾病的預后提供更好的治療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