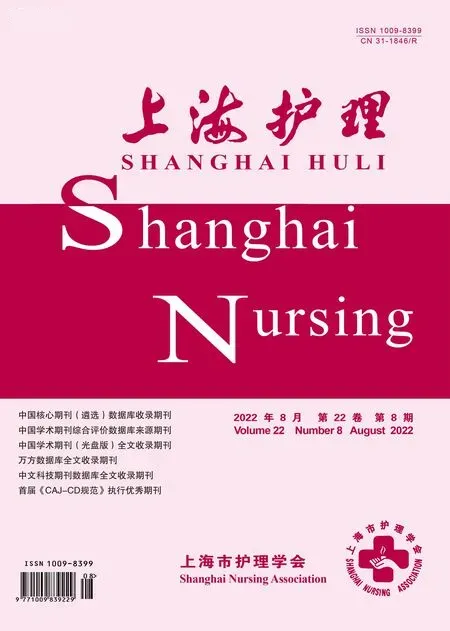認知行為療法對癌癥患者復發恐懼及負性情緒影響效果的Meta分析
迪麗胡瑪爾·庫爾班,曾 鑰,朱凌霄,施齊芳
(1. 西安交通大學護理學系,陜西 西安 710061;2. 煙臺毓璜頂醫院,山東 煙臺 264099)
癌癥是指機體內異常細胞不受控制地無限生長,向周圍組織、器官乃至全身侵略和轉移,對人體造成強烈破壞性的一大類慢性疾病[1]。癌癥是全球第二大死因,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癥研究機構數據顯示,2020 年約1 000 萬人死于癌癥[2]。身體功能受到嚴重摧殘、疾病預后的不確定性使癌癥患者身心遭受雙重打擊并引發患者心理諸多問題。癌癥復發恐懼(fear of cancer recurrence,FCR)是指對癌癥復發或進展可能性的恐懼、擔心或擔憂[3]。研究發現,46%的癌癥患者明顯表現出對疾病復發或惡化的擔心[4]。Simard等[5]的系統評價結果顯示,22%~87%的癌癥患者的FCR 為中高水平。多項縱向研究表明,癌癥患者的FCR 通常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輕[6-7]。高水平的FCR可導致癌癥患者痛苦體驗,加重抑郁、焦慮等不良情緒,降低治療依從性、生活質量水平并增加額外醫療負擔[8]。因此,FCR的管理與治療顯得尤為重要。認知行為療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是改善心理健康的一種心理社會干預,專注于挑戰和改變認知扭曲和行為、改善情緒調節及促使個人應對策略的發展[9],可以有效改善癌癥患者的FCR,減輕焦慮、抑郁等消極情緒,提高生活質量和幸福感[10-13]。但現有的研究[14-15]結果存在一定爭議。因此,本研究旨在通過Meta 分析探討CBT 對癌癥患者FCR的干預效果,以期為臨床實踐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文獻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納入標準①研究對象:年齡≥18 歲;通過病理學檢查明確診斷為癌癥;排除正在接受其他心理治療的癌癥患者。②干預措施:對照組給予常規護理(包括飲食與藥物指導、疾病相關知識手冊指導、心理護理及電話隨訪),觀察組在對照組基礎上給予CBT。本研究CBT 是指治療師通過評估患者對FCR 的認知行為,識別其不合理的認知及行為,幫助其進行認知重建和行為矯正、樹立對疾病的正確認知及增強參與治療積極性和抗病信心,給予其放松治療,鼓勵建立行為目標、維持健康行為、發展解決問題的技能、優化與護理人員和健康專業人員的溝通及促進個人使用社會資源[16]。③結局指標:主要結局指標為FCR[采用癌癥復發恐懼量表(Fear of Cancer Recurrence Inventory,FCRI)、癌癥焦慮量表(Cancer Worry Scale,CWS)、疾病進展恐懼量表(Fear of Progression Questionnaire,FoP-Q)或疾病進展恐懼簡化量表(Fear of Progression Questionnaire-Short Form,FoP-Q-SF)評價],次要結局指標為抑郁、焦慮[抑郁采用患者健康問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抑郁自評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醫院焦慮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或抑郁-焦慮-壓力量表(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Scale,DASS-21)評價,焦慮采用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HADS或DASS-21評價]。④研究類型:隨機對照研究。
1.1.2 排除標準①無法獲取全文的文獻;②無法獲得完整、有效數據的文獻;③觀察組設置大于1 組的文獻;④質量等級低于B級的文獻;⑤非中、英文文獻
1.2 文獻檢索策略計算機檢索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Medline、Proquest、The Cochrane Library、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萬方數據庫、中文科技期刊數據庫(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urnal Database,VIP)和中國生物醫學文獻數據庫(China Biology Medicine disc,CBMdisc)中公開發表的關于CBT 對癌癥患者FCR、抑郁及焦慮影響的隨機對照研究文獻。檢索時間自建庫至2021 年7 月31 日。英文關鍵詞為“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or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or cognitive therapy or CBT or behavioral therapy”and“fear of cancer recurrence or fear of recurrence or fear of progression or fear of disease progression or fear or depression or depressive disorder or depressed or anxiety or anxiety disorders or anxious”and“cancer or carcinoma or neoplasms or cancer patients or cancer survivors or tumor”;中文關鍵詞為“癌癥患者/癌癥/癌/癌癥幸存者/癌癥病人/惡性腫瘤”“癌癥復發恐懼/疾病進展恐懼/恐懼疾病進展/恐懼/抑郁/抑郁狀態/焦慮/焦慮狀態”“認知行為療法/認知行為干預/認知行為治療/認知療法/行為療法/認知心理療法”。再對與本研究密切相關文獻的參考文獻進行擴大檢索。
1.3 文獻篩選與信息提取所有文獻均導入NoteExpress軟件,由2名經過培訓的研究者根據納入、排除標準獨立篩選文獻并交叉核對,出現分歧時相互討論,討論后意見仍不統一時由第3 名研究者裁定。采用自制表格提取資料,包括作者、年份、研究對象、樣本量、干預措施、干預和隨訪時間、評價工具及結局指標。
1.4 文獻質量評價由2 名經過培訓的研究者采用Cochrane 偏倚風險評價工具獨立評價所有納入研究的文獻質量[17]。在正式評價文獻質量前,2 名研究者先對6~9 篇文獻進行預評價,熟悉質量評價工具、統一評價標準。正式評價過程中,若出現評價結果不一致,2名研究者之間先進行討論,仍不能解決則征求第3名研究者意見。文獻質量評價的內容包括隨機序列的產生、分配隱藏、對參與者和實施者的盲法、對結局評價實施盲法、結局數據完整性、選擇性發表以及其他偏倚。若被評價文獻完全符合以上評價標準,則質量評價等級為A 級;若部分符合,則質量評價等級為B 級;若完全不符合,則質量評價等級為C級。
1.5 統計學方法采用RevMan 5.3統計軟件進行Meta 分析。若納入研究異質性較小(I2<50%,P>0.1),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若異質性較大(I2≥50%,P<0.1),則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分析。若因臨床與方法學導致的異質性較大,則采用亞組分析;若因臨床與方法學導致的異質性較小,則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分析。若連續性資料評估工具不同,則選用標準化均數差。所有分析均要求計算95%可信區間,顯著性水平α=0.05。使用漏斗圖評價是否存在發表偏倚。
2 結果
2.1 文獻檢索及篩選結果初步檢索獲得785 篇文獻,剔除重復文獻后剩余554 篇,進一步閱讀標題、摘要及全文最終納入12篇文獻[8,10-14,18-23]。文獻篩選流程見圖1。納入的12篇文獻中,英文文獻8篇[10-14,18-20]、中文文獻4 篇[8,21-23],總樣本量為1 517 例,其中觀察組761 例、對照組756 例,12 篇文獻發表時間為2012—2021年,納入文獻的基本特征見表1。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圖
2.2 納入文獻的質量評價納入的12 篇文獻[8,10-14,18-23]均說明了隨機分組方法;3 篇文獻[10,12-13]有分配隱藏;2 篇文獻[10,18]實施了雙盲;12 篇文獻結果完整,其中8 篇文獻[10-14,18-20]采用了意向性分析。納入文獻質量等級均為B級,文獻質量評價具體見表2。
2.3 Meta分析結果
2.3.1 CBT 對 癌 癥 患 者FCR 的 影 響12 篇 文獻[8,10-14,18-23]均報告了干預結束后CBT 對癌癥患者FCR的影響,其中5 篇文獻[8,18-19,22-23]采用了FoP-Q-SF、4 篇文獻[10,12,14,20]采用了FCRI、2 篇文獻[11,13]采用CWS、1 篇文獻[21]采用FoP-Q 評價CBT 對癌癥患者癌癥復發恐懼的影響。將12 項研究結果進行合并,研究間異質性較高(I2=92%,P<0.001),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分析,結果顯示觀察組患者FCR 改善狀況優于對照組患者[SMD=-0.52,95% CI(-0.63,-0.42),P<0.001],見圖2。3篇文獻[10,14,18]報道了對癌癥患者實施CBT 干預后6個月的隨訪結果,研究間異質性較高(I2=84%,P=0.002),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分析,結果顯示觀察組患者FCR 改善狀況優于對照組患者[SMD=-0.31,95% CI(-0.52,-0.11),P=0.003],見圖3。根據干預形式與干預時間對FCR 的影響進行亞組分析。①干預形式:4項研究[18,20-21,23]對觀察組實施團體CBT干預,研究間異質性高(I2=97%,P<0.001),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兩組患者FCR 改善情況差異無統計學意義[SMD=-1.12,95% CI(-2.27,0.03),P=0.06];8 項研究[8,10-14,19,22]對觀察組實施個體化干預,研究間異質性低(I2=2%,P=0.42),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個體化CBT 干預可以改善觀察組患者FCR,且觀察組患者FCR 改善狀況優于對照組患者[SMD=-0.67,95%CI(-0.81,-0.54),P<0.001],見圖4。②干預時間:6項研究[8,10,14,18,21,23]干預時間<3個月,研究間異質性高(I2=96%,P<0.001),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分析,結果顯示觀察組患者FCR 改善狀況優于對照組患者[SMD=- 1.08,95% CI(- 1.77,- 0.39),P=0.002];6 項 研究[11-13,19-20,22]干預時間≥3 個月,研究間異質性高(I2=63%,P=0.02),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分析,結果顯示觀察組患者FCR 改善狀況優于對照組患者[SMD=-0.47,95%CI(-0.75,-0.19),P=0.0009],見圖4。

表1 納入文獻的基本特征

表2 納入文獻的質量評價
2.3.2 CBT 對癌癥患者抑郁的影響9 篇文獻[10-14,19-22]報告了CBT 對癌癥患者抑郁的影響,其中4篇文獻[11-13,20]采用HADS、2 篇文獻[10,14]采用DASS-21、1篇文獻[19]采用PHQ-9、1 篇文獻[21]采用SDS、1 篇文獻[22]采用HAMD 評價CBT 對癌癥患者抑郁的效果。將9項研究結果進行合并,研究間異質性高(I2=92%,P<0.001),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分析,結果顯示觀察組患者抑郁癥狀改善狀況優于對照組患者[SMD=-0.73,95%CI(-1.18,-0.27),P=0.002],見圖5。

圖2 CBT對癌癥患者FCR即刻影響的森林圖

圖3 CBT對癌癥患者FCR長期影響的森林圖

圖4 CBT對癌癥患者FCR影響的亞組分析

圖5 CBT對癌癥患者抑郁效果的森林圖
2.3.3 CBT對癌癥患者焦慮的影響7篇文獻[10-14,20,22]報告了CBT 對癌癥患者焦慮的影響,其中4 篇文獻[11-13,20]采用HADS,2 篇文獻[10,14]采用DASS-21,1 篇文獻[22]采用HAMA評價CBT對癌癥患者焦慮的效果。將7 項研究結果進行合并,研究間異質性高(I2=91%,P<0.001),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分析,結果顯示觀察組患者焦慮癥狀改善程度高于對照組患者[SMD=-0.50,95%CI(-0.64,-0.36),P<0.001],見圖6。

圖6 CBT對癌癥患者焦慮效果的森林圖
2.3.4 文獻偏倚結果以FCR 評分為結局指標繪制漏斗圖,見圖7。漏斗圖顯示兩側研究大致對稱,提示納入的文獻存在發表偏倚的可能性小。

圖7 以FCR評分為結局指標的漏斗圖
3 討論
3.1 納入研究的文獻質量尚可本文共納入12篇[8,10-14,18-23]隨機對照研究,文獻質量評價等級均為B級。12 篇[8,10-14,18-23]文獻均說明了隨機分組方法,研究對象基線資料均具有可比性(P>0.05);3 篇[10,12-13]文獻報 告 了 分 配 隱 藏;2 篇[10,18]文 獻 實 施 了 雙 盲;8篇[10-14,18-20]文獻交代了退出與失訪病例,并通過意向性分析進行數據分析;CBT 均由治療師(包括臨床醫師、心理學家、精神病學家以及臨床護士)負責實施。總體而言,被納入的文獻質量中等,尚可接受偏倚風險對結果產生的影響。整個Meta分析結果比較可靠。
3.2 CBT 可有效改善癌癥患者FCR本研究結果發現,CBT 可以有效改善癌癥患者FCR。這與Tauber等[24]的Meta分析結果一致。Tauber等[24]的研究結果表明,傳統的CBT 或以CBT 為基礎的新型干預方法均可以減輕癌癥患者的FCR。由于認知、情緒和行為是相互關聯的,認知和/或行為的變化也會引發情緒的變化,CBT作為一種以行動為導向的心理治療形式,可以識別和修改癌癥患者的消極思維模式[16]。本研究還發現,CBT 對癌癥患者FCR 的改善效果可以持續至干預后6 個月,可能與CBT 能幫助癌癥患者養成健康的認知思維并建立習慣行為模式,使得患者的積極情緒得以長期保持有關。本研究亞組分析結果顯示,個體化CBT 干預較團體CBT 干預更能改善癌癥患者的FCR。分析可能的原因,癌癥患者因心理創傷嚴重變得容易敏感,其在個體化干預中不僅能不受其他患者的負性情緒影響,而且在與治療師獨處時更愿意表達內心想法和需求,因此個體化CBT 干預能達到的預期效果也更好。此外,本研究針對干預時間進行了亞組分析,結果顯示,干預時間<3 個月與≥3 個月均能使癌癥患者FCR 有所改善。在進行CBT 初始干預期間,治療師就通過與患者交流在短時間內幫助其培養正向積極態度和提高認知水平,在滿足其心理需求的同時還通過布置作業、及時反饋和隨時提供咨詢等隨訪服務進一步鞏固和增強其認知和應對能力,減輕了其對癌癥復發的恐懼。因此,短期CBT 也可能會對癌癥患者FCR 起到改善作用。因此,醫護工作者可以在短時間內采用CBT 幫助癌癥患者改善FCR,讓患者保持積極態度接受疾病、配合治療,并堅持對其隨訪以鞏固干預效果,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水平。
3.3 CBT 可降低癌癥患者的抑郁和焦慮水平由圖5、圖6 可見,CBT 對癌癥患者抑郁、焦慮等情緒有顯著的積極影響,與Reavell 等[25]的研究結果一致。研究表明,CBT有助于患者識別和轉換無益的思維模式,嘗試并維持健康行為來監測和改善自己的心理健康,達到克服抑郁、焦慮等消極情緒的目的[26]。
4 小結
CBT 可以有效改善癌癥患者FCR、抑郁及焦慮等負性情緒,且個體化CBT 較團體CBT 對改善癌癥患者FCR 效果更好,短期干預對改善癌癥患者FCR 也有較好效果且改善效果可以持續一段時間。建議把CBT納入癌癥患者的輔助護理治療,以便更好地管理成年癌癥患者的心理健康。本研究納入的文獻為僅設立1 組觀察組的隨機對照試驗研究且已公開發表的中英文文獻,納入文獻較少,未對癌癥種類進行亞組分析,這可能對研究結果產生一定影響。希望未來有更多的高質量隨機對照試驗去探討CBT 對癌癥患者FCR 的療效,并進一步優化個體化CBT干預方案以便于臨床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