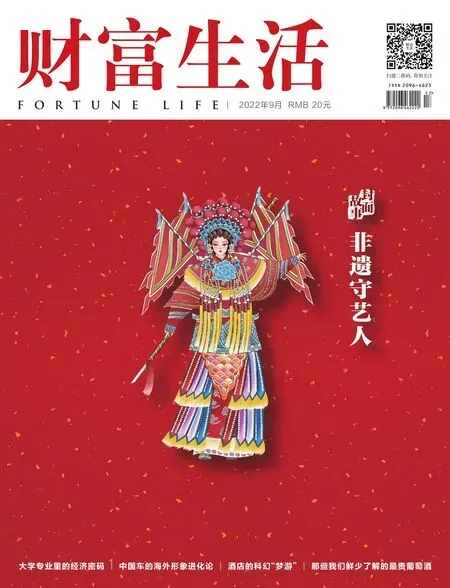大學專業里的經濟密碼
作者/蘆依、任彤瑤 編輯/周一澤
近期,應屆生就業再度成為熱議話題,而在大學專業背后,是一個個真實的產業。中國經濟已經高速發展了四十年,有這樣5種嵌入歷史進程的專業,為當時選擇它們的人帶來顯著的紅利。當然,這種紅利需要與之契合的個人努力才能兌現。從歷史的后視鏡中,我們能從大學專業中讀到怎樣的經濟密碼?

圖/視覺中國
│01│外語外貿:“改開”的寵兒
1984年,香港新鴻基拿下外灘一塊地皮,用22個月建起了上海第一座百米現代寫字樓——聯誼大廈。
竣工半年前,聯誼的預訂出租率已超七成,三菱商事、通用電氣、IBM、惠普、花旗銀行、三洋電機等大型外企魚貫而入,有公司排隊一年才搶到辦公室。建成一年左右,外企們的交租(還都是寶貴的外匯),就填平了建造費用。
在市場經濟尚草莽的年代,“外企”是一個新鮮且性感的詞匯。高薪、假期、補貼、跨國出差、空中飛人、五星級酒店等一系列遠超國企和民企的待遇,讓跨國外企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成為就業市場的明珠。聯誼大廈嶄新的玻璃幕墻內,中國第一批“白領”走向歷史潮頭。
在北京,去東三環大北窯上班也成了很多人的夢想,這片日后被稱為“國貿”的區域,集中了惠普、摩托羅拉等一批最早入華的外企,60%以上的外商駐京機構選擇駐扎于此。由于高端商場林立,一度被戲稱為“中國的香榭麗舍大街”。
在那個年代,一口流利的英語,可能就是決定工資是五十塊人民幣還是幾百美元的砝碼。
北京椿樹醫院護士吳士宏,花一年半時間聽收音機自學英語。獲得英語專科文憑后,如愿被聯誼大廈里的IBM公司聘用。此后12年,她從端茶遞水的文員,一步步成為IBM華南總經理、微軟大中華區CEO,被媒體稱為“打工女王”。
吳士宏成為IBM雇員的那年,李陽從新疆勉強考入了蘭州大學工程力學系。沒人能想到,這個高考英語16分、孤僻沉默的年輕人,會突然在大聲朗讀中找到激情。在外語成為外企準入證的年代,李陽靠著“瘋狂英語”俘獲大批虔誠信徒。

2000年4月17日,北京,“世界經濟論壇·2000中國企業高峰會”上,時任TCL集團副總裁的吳士宏接受記者采訪 圖/視覺中國

2009年1月3日,瘋狂英語創始人李陽在廣東東莞市為學生和家長們教授英語學習的方法 圖/視覺中國
在那個年代,寶潔的管培生在快銷行業可以橫著走;入職四大的Auditor在1990年代就能拿到四五千元的月薪;在領導面前,IBM的高管可以蹺著二郎腿談笑風生;而如果你掛著一只微軟的工牌去衡山路喝酒,大概率會有妹子來搭訕。
需要指出的是:語言是個通識技能,外企招聘的主力是業務對口專業里英語好的畢業生,純外語專業只是少數。不過,在當年大江南北的“英語熱”背景下,還有大量待遇優厚的培訓機構、外貿公司等能夠容納外語專業畢業生。
當李陽把萬人朗讀會辦到故宮太廟跟前,外語專業“復合型人才培養”在全國高校燃起燎原之火。北京外國語大學光英語就有5種專業方向,對外經貿大學的錄取分數線比肩“清北”,甚至創下一年狂攬16個高考“狀元”的驚人紀錄。
南京財經大學金融學院的吳正浩書記說:“當時但凡和‘國際’二字沾邊的專業都吸引了無數考生報考,國際經濟、國際貿易、國際金融等等,考生們夢想著在專業的學習后能夠和外國人做生意,從外國人的包里掏鈔票。”
在《微軟的夢工場》一書中,比爾·蓋茨寫了《在中國創新》的序言:
“當我在1997年訪問中國期間,中國學生身上所洋溢著的才智、激情和創造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正是緣于這次訪問,對我們于1998年在北京成立基礎研究院的決定,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蓋茨的高情商發言揭示了一個只屬于新世紀初的事實:大型的外資企業可以利用其高利潤的業務,在中國這樣的后發國家,以不菲的薪資,輕而易舉地吸納最頂尖的人才。只要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就能在時代的潮頭上賺好幾年差價。
這個賺差價的窗口期非常長,在中國加入WTO之后,高速增長的出口催火了外貿專業,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的“2003年招生大全”點擊量多達4萬多次,第一志愿上線是643分,但考了700多分的考生仍然焦慮地刷新頁面,生怕不被錄取。
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舉辦,掀起了中國迄今為止最后一輪全民外語熱潮,也是外語外貿專業最后的高光時刻,之后便是金融海嘯洶涌而過,外企的薪資待遇在頂級央企和民企面前,不再有昔日碾壓級別的優勢,這是中國經濟崛起的必然結果。而外語外貿等專業當年的火熱,也是中國向世界學習、交流、貿易的重要基礎,它們的意義不應該被否認。
│02│建筑土木:沒落的貴族
1987年12月1日,深圳會堂人頭攢動。
來自北京的高層領導、來自全國的17位市長、中外100多名記者共同見證了一場特殊的拍賣。競標從200萬起價,44家企業競相角逐,叫價聲此起彼伏,直到深圳特區房地產總經理駱錦星一錘定音——他高舉價牌,喊出了525萬元的最高價。
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場土地拍賣,它一改此前土地的無償劃撥制,為中國往后20余年的土地財政和樓市繁榮埋下伏筆。為抵御亞洲金融危機,中國在1998年開啟住房改革——延續半個世紀的福利分房被取消,居民住宅從此“貨幣化”。
買房,終于正式成為中國人一生中最大的開支項。伴隨商品房時代一同到來的,還有蹣跚起步的城鎮化改造。那一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僅有33.6%,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6%。修橋、通路、搭建基礎設施迫在眉睫。
房地產和城鎮化的兩重歷史機遇,讓建筑和土木工程這兩個專業,嘗到了時代紅利。
從招生來看,土木工程是清華大學、同濟大學和東南大學等名校當年的王牌專業,只招600分以上的頂級人才。而王牌專業代表了最好的就業,在全國大搞建設的潮流下,他們流向了建筑設計院、各大房企以及中鐵中建等施工單位。

圖/視覺中國
在建筑專業,有“老八校”和“新八校”之說,建筑專業的分數在這些學校里基本都排在前列。學子們在學校里通宵畫圖,畢業后進入萬科、保利、龍湖、中海等房企,待遇高升職快,買房、炒房近水樓臺,屬于風口中的風口。
1998年到2007年間,中國經濟增速僅有12%,而房地產在拿地和新開工面積上的平均增速分別達到21%和17%。在互聯網還是幾行代碼時,繁榮的樓市保證了建筑、土木人優于同齡人的就業和待遇。
2008年應對金融危機的救市舉措,讓建筑、土木專業加速起飛。“四萬億”投資計劃令2009年基建投資增速42.2%,創下歷史最高點,樓市再次迎來了長達10年的繁榮。
2013年,碧桂園老板楊國強對屬下說:“給你30個億,你去給我找300個人來。”自此拉開了地產商的“搶人大戰”。碧桂園年薪1.92億元的總裁莫斌、第一位年收入過億的區域總裁劉森峰等人,都是建筑專業畢業。
莎士比亞說:殘暴的歡愉,終將以殘暴結束。
2016年“房住不炒”提出之后,地產行業增速逐步放緩;2020年“三道紅線”出臺之后,所有抱有僥幸心理的房企,都迎來了“殘暴結束”。

華為公司2018屆校招高管宣講會在武漢大學開啟首站,臺下座無虛席 圖/視覺中國
建筑和土木的畢業生自然難逃行業趨勢的碾壓。B站UP主“大猛子”是土木專業出身,靠記錄工地日常走紅網絡。他調侃自己“來工地兩個月,看著老了20歲”,更有經典語錄:“3000塊招不到農民工,卻能招來一個大學生。”二十年來,房地產行業成為孕育富豪的沃土,既讓炒房群體享受到了流動性紅利,又讓從業人員賺到了遠超時代的回報。當大基建時代和大地產時代結束之時,建筑和土木兩個學科的“回報率”,也必然會回到社會平均水平。
大猛子的視頻的確透露出辛酸,但不管怎么說,這兩個專業的確“祖上闊過”。
│03│通信工程:登頂的榮耀
通信工程專業,是第一個由背后產業做到了全球第一,從而成為填報高考志愿時熱門多年的專業。這個行業的發展史,基本是華為和中興這兩家公司的企業史。在改革開放初期,全國9億人口只有不足200萬臺電話,通信設備嚴重依賴進口;1990年代,電話裝機費高達數千元,來自7個國家的8種制式設備讓電話的成本居高不下。
中國通信行業自此開始了漫長的“逆襲”,從固化通信到移動通信,從2G到3G,4G,5G,在一輪又一輪的技術演進中,昔日的“七國八制”退出了市場,華為和中興逐漸擠進全球前五,前者更是反超愛立信,成為全球第一的通信公司。
華為在沖頂全球第一的同時,還抬高了整個行業的薪酬。
世人都知道華為的薪水高,但到底有多高呢?據《創華為》一書記載,2000年,其本科生月薪就有7000元,年終還有10萬元~16萬元的分紅,待遇遠高于深圳其他公司,工科院校的電子通信專業整班地被華為收編的情況在當時非常普遍。
1998年10月,中興與華為都在清華園招聘。本是中興先來,但華為開出了高薪,原本簽約中興的人才至少七成轉投華為。2000年,重慶郵電大學電信專業畢業班40多人,其中有39人入職華為;東南大學30多人的無線電班,被華為招走25個。
高薪的另一面,是華為的狼性文化和“奮斗者”制度。雖然受到了廣泛的口誅筆伐,但每年奔赴華為的人仍然如過江之鯽。
2021年,被制裁中的華為全球收入6300億人民幣,全年發放的薪酬及其他福利費用超過1300億元人民幣。按照員工數量20萬人來推算,華為平均每位員工的年薪超過了70萬元。老員工如果加上股票分紅,拿到手的可能會更多。
還有人認為,華為和中興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通信專業就業的“多樣性”。
理由是中國通信設備商崛起的同時,“外企”們都在凋零:北電破產,諾基亞和西門子的電信部門合并,摩托羅拉出售電信部門,阿爾卡特朗訊并入諾基亞……想在通信設備行業找一份朝九晚五、無須超負荷加班的外企工作的確不容易了。
但從另一個層面來看:華為和中興占全球通信設備40%的市場份額,也就是說如果全球通信行業的高端崗位有10000個,那中國就至少占有4000個。而在華為和中興尚未崛起的1990年代,這個數字可能只有500個甚至更少。
另外,這個專業的好處在于它的延展性:既要學焊電路板,也要學算法編程,所以既能往電子芯片等硬件方向走,也能往計算機互聯網方向走。一位C9高校通信專業研究生告訴筆者:“去不了互聯網公司,起碼還有華為或中興可以保底。”
一個行業如果做到了全球第一,的確能夠給本國畢業生提供足夠的就業縱深。
│04│計算機:流動性的神話
2009年春天,紅杉中國在京郊開年會,創始人沈南鵬把主題定為“Mobile Only”。
在這之前的一年,為了刺激內需而提前發放的3G牌照,令三大運營商大打價格戰;往后一年,雷軍開始緊鑼密鼓做第一款小米手機,iPhone4在國內炒到上萬元,蜂擁而至的黃牛在三里屯蘋果店的長隊前大打出手。
提速降費的網絡、易用的智能機,與龐大的人口基數產生化學反應,在逐漸萎縮的PC端外爆發出新能量,移動互聯網的時代呼嘯而至。
VC / PE投資人們提著水管,綠油油的美鈔從大洋對岸嘩嘩流進中關村;電商大戰、外賣大戰、直播大戰、網約車大戰、短視頻大戰、共享單車大戰、社區團購大戰、在線教育大戰……每種生意都值得用互聯網重做一遍,不計成本、不惜代價。
滾滾的鈔票把互聯網老板們送上各類富豪榜,與房地產大佬同臺競爭,也把底下打工人的薪酬福利和期權價值逐步拉高。
作為整個行業的核心燃料,信息技術相關專業人才的收入從2013年開始超越金融業,高居所有行業之首。
揮別了通信基建的輝煌年代,北京地鐵13號線盡頭的北京郵電大學搖身一變,成為中關村最大碼農培訓基地,畢業生從三大運營商,分流向到了BAT和TMD。對北郵學子來說,這是一條通往人生幸福的快線:
從北郵所在的大鐘寺站上車,五站直達西二旗,大廠遍地,向北兩站之外的回龍觀,有數不清的隔斷次臥靜待合租。

北京郵電大學校園招聘會 圖/視覺中國
在這條地鐵線上熬幾年,他們就能迅速完成同齡人辛苦半生才有的財富積累。
這十多年來,中關村的置業顧問都知道,如果一個客戶全款買房,要么是拆遷戶,要么是公司剛上市的互聯網碼農。
2021年初,快手上市2周,市值飆到1.5萬億元人民幣,園區4公里外的融澤嘉園房價一周漲了20萬元。快手員工談論公司股價,計量單位用的是“今天我跌了一輛大G”,或者“漲了一輛特斯拉”。
類似的故事在杭州西溪、深圳南山科技園反復上演。2014年阿里上市,杭州多出上百位千萬富翁,員工的丈母娘和西溪的房地產商笑得合不攏嘴。碼農一躍成為21世紀相親市場上的香餑餑,也成為高考志愿填報的頭號對標職業。
但造富的窗口不會永遠敞開。2014年,程序員郭宇來到中關村,窩在民房里和創業公司同吃同住。起床把被子塞到沙發底下,抽出桌子就開始寫代碼。那時的中關村并沒讓郭宇有硅谷的感覺,他只記得滿街還在賣電腦配件。
公司被收購后,他成為字節的早期工程師。2020年,28歲的郭宇決定辭職退休,手中的期權已經漲了200倍,足夠他做任何想做的事,比如去日本開溫泉旅館。同一時期,那些擠破腦袋進入大廠的計算機畢業生,發現自己被卷入了一場漫長的、聲勢浩大的“畢業”潮。
有記者問過郭宇:“走到今天這一步,你覺得運氣大概占多少?”他面色平靜地回答:“運氣大概占70%,個人努力占30%。如果我媽媽不在五歲時送我上小學,那我會錯過所有移動互聯網爆發最關鍵的時機。就算滿足了這個條件,也可能不會來北京,而大部分分享移動互聯網創業紅利的公司都在北京。這些都是看起來簡單的、隨機性的、不怎么重要的事情,但等你真正獲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再去回溯,這些都是有決定性意義的重大事項。”
│05│生化環材:板凳的逆襲
在2022年的畢業季,搶破頭進互聯網的畢業生被無故毀約,原本無人問津的天坑專業卻成為香餑餑——車企、半導體和風投高薪挖化學和材料人才,甚至有VC的新能源團隊點名要化學博士。這一幕,似乎成了風口變遷的隱喻。
化學與材料此前一直籍籍無名,更是跟生物、環境等一起并列為“生化環材”,被貼上“天坑專業”的標簽。
所謂“天坑”,是說薪資低、機會少、工作環境也算不上舒適。讀書時課程枯燥難懂,畢業也沒太多出路——要么本專業就業,待遇一言難盡;要么畢業轉行,忍痛放棄專業積累;要么讀到博士,爭取到競爭更激烈的科研崗位。
這形成了一種荒誕景象——即使在一些985院校,天坑專業的學長學姐們也會主動“傳幫帶”,提點后輩們要么早學編程,轉行互聯網,要么早準備考公,爭取畢業后“上岸”。即使有人想認真學專業課,也會被這種架勢嚇到。
這種尷尬的窘境,一直到近幾年大家意識到有了很難突破的技術瓶頸,才有所改善。
中國從“下游應用創新”,逐漸轉移到“上游技術創新”上。這種轉移的動機既有頂層設計的主動引導,也有國際形勢的現實因素。在上游頻頻被其他國家卡脖子的當下,對基礎學科的需求驟然提升。
在“生化環材”四個專業中,生物工程的就業伴隨著國內藥企的壯大而逐步改善,化學和材料專業的就業,也被新能源汽車、光伏、半導體等行業帶動起來。這些行業都是不折不扣的“硬科技”,都需要高密度的基礎學科人才。
以新能源汽車行業為例,兩位蜚聲全球的人物——寧德時代的曾毓群和比亞迪的王傳福均有基礎學科背景。曾毓群曾經在中科院物理所攻讀凝聚態物理專業,師從資深電池專家陳立泉院士,王傳福則畢業于中南大學冶金物理化學專業。

工人在生產太陽能光伏組件 圖/視覺中國
新能源的下游產業鏈中也不乏化學、材料專業出身的大佬。比如贛鋒鋰業董事長李良彬是化學專業畢業,天賜材料董事長徐金富是中科院的化學碩士、當升科技和容百科技的創始人白厚善則是中南大學有色冶金專業畢業。
光伏領域的老板們專業背景更硬:隆基股份的三個創始人都是半導體材料專業畢業;TCL中環的掌舵人沈浩平是半導體物理專業,天合光能的高紀凡是量子化學碩士,陽光電源創始人曹仁賢的另一個身份是合工大博士生導師……
昔日冷門學科的畢業生出現在富豪榜之上,某種程度上是中國產業升級的勝利。
當然,中國上游創新仍處于青萍之時,類似互聯網那種高薪崗位相對有限。對于沒有特別興趣的寒門學子來說,需要坐多年冷板凳的基礎學科,并非最好的選擇;但對于家境好且有興趣的學生來說,選擇它們并不會錯。
任正非談及芯片領域的“卡脖子”時講道:“我們國家修橋、修路、修房子……已經習慣了只要砸錢就行。但是芯片砸錢不行,得砸數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但是我們有幾個人在認真讀書?博士論文的真知灼見有多少呢?”
任正非這段話頗有道理,但有一點沒講透:要想中國的科學人才達到可以“砸”的數量,需要一個關鍵的前提:要有足夠多的高薪崗位來容納他們,而不能寄希望于他們一邊過著清貧的日子,一邊向諾貝爾獎沖擊。所以,生化環材和基礎科學爬出深坑的那一刻,應該就是中國產業升級蹚過深水區的那一刻。
實際生活中,專業的選擇與行業的景氣往往是錯配的,比如2012年跟風學金融,四年后進銀行喜迎降薪;2018年學計算機,2022年畢業趕上互聯網大廠“畢業典禮”。不難發現,人人趨之若鶩的時刻往往意味著行業的頂點,也是衰退期的開始。專業的選擇與對口行業的興衰看似充滿巧合,實則是個人努力與歷史進程的共同作用。無論其中有多少規律與法則可循,我們都必須承認,能夠學一個合適的專業,去一個合適的行業,并最終跨越階層的這種順遂的人生,在這個社會始終是少數。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真正通過努力改變命運的人,無論其出身顯赫或平凡,無論其家境殷實或尚可,無論時代對其慷慨或辜負,他們往往都有在關鍵選擇時孤注一擲的勇氣和在十字路口告別舒適的魄力。
行業的風口、資本的推動、時代的紅利也許是那99%,但最關鍵的還是源于自身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