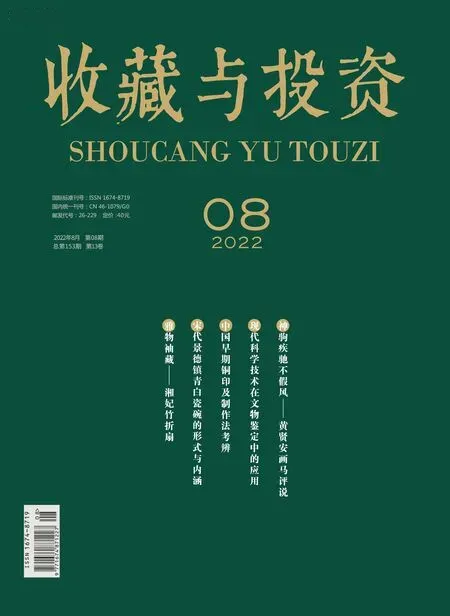宋代景德鎮青白瓷碗的形式與內涵
黃 越,于 歡,陳 猛,吳光昊(景德鎮學院,江西 景德鎮 333000)
歷史上任何一件器具從構思到制作,無不受造物者主觀認知和當時環境客觀的影響。宋代由于趙匡胤“重文”,加上活字印刷讓各類書籍流入市場,為文人學習交流文化提供了有利的物質技術前提。這一時期文化的繁盛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使得宋代人民生活安定富足,人們對器物的要求不再局限于其功能性,對其審美性也有所要求。這一時期瓷業發展非常迅速,五大名窯百花齊放,各窯口生產的陶瓷器類繁多且都具有很高的技術性和審美價值。這些窯口生產的諸多器物無不受宋代這一特殊時期的文化背景影響,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內涵在日常用具之中皆有反映。在這龐雜的陶瓷器類中,景德鎮生產的青白瓷碗可謂獨樹一幟,具有獨特的形式與內涵。
景德鎮之所以被譽為“千年瓷都”,離不開宋代青白瓷的大放異彩。宋代由于北方戰事不斷,許多北方窯口被毀,許多制瓷工匠逃到當時四面環山、較為安定的景德鎮。青白瓷是在景德鎮吸收南北名窯的背景下生產出來的。在諸多青白瓷類日用器具中,青白瓷碗似乎是最不起眼的。但這看似簡單的青白瓷碗,無論是造型還是裝飾,都涵蓋了宋代的文化內蘊。從器物文化內在而言,各類器物受儒、釋、道三家的思想影響,繼唐代以“渾圓飽滿,舒展大方”為特征后,宋代瓷器注重秀美、雅致的意蘊,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外在功能和內在思想的融通,青白瓷碗也不例外。青白瓷碗中承載的宋代造物觀念,正是以器為載,融中華傳統文化于其中。
一、形式中的曲線與圓
在所有的陶瓷器物造型中,碗類的結構相對簡單。它的起源至今還無法得到準確考證。根據現存陶瓷史料,早期的碗多為圜底器,仿佛切開的半圓形,只是有深腹和淺腹之別。碗的形式大多由口沿、碗腹、碗底、碗足組成,有些碗還帶有盞托。隨著功能和形式的不斷發展,人們設計出來的造型式樣也愈加豐富,除突出功能性以外,其形式美感也愈加突出,比如斗笠碗、蓋碗、葵口碗等,造型獨特,形式多樣。在形式上成熟而協調,在功能上完整而規范,一些細節都處理得非常具有時代特征。宋代瓷碗作為主要的日常用具,各個陶瓷窯口均有燒造瓷碗,如定窯白釉刻花石榴紋碗、鈞窯青灰釉碗、龍泉窯青釉碗、建窯黑釉小碗等。在這些瓷碗中,景德鎮生產的青白瓷碗具有特殊美感。
北宋初期,景德鎮燒造的青白瓷燒制工藝還不成熟,一些青白瓷產品釉色泛黃,器型以日用器物為主,有瓶、碗、盤、碟一類,有些器物還伴有少量刻畫花紋。北宋中期以后,青白瓷的制作工藝逐漸成熟,在學習南北方窯口的燒造和裝飾之后,逐漸形成了穩定的造型和裝飾特點。北宋晚期至南宋,由于覆燒工藝和對生產規模的要求,大量的印花裝飾出現并流行。整個宋代,青白瓷碗的發展都離不開線條的運用,例如青白瓷中常見的蓮花紋、嬰戲紋。在青白瓷碗的造型構成中,絕大部分由曲線與圓組成。曲線作為形式美的重要表現元素和傳達媒介,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
從設計的角度而言,曲線可以分成幾何曲線和自由曲線兩大類。幾何曲線顧名思義,就是一些具有明顯形態特征的曲線,如波浪、圓圈等。青白瓷碗中的花葉刻畫、水紋波浪都屬于幾何曲線。這類曲線裝飾在碗中,弧度較小,舒緩卻有堅韌的生命力。青白瓷碗中典型的自由曲線就是其外輪廓線。由于瓷碗經過不同工匠的純手工拉坯、修坯等工序,這種外輪廓的自由曲線極具個性,即使器型相同也會有些許不同。也許正是這種流變之美,讓人既體會到宋瓷的美感,卻又并不覺功利和張揚,讓人在使用和觀賞的過程中保持精神的舒緩和心情的愉悅。
除曲線外,青白瓷碗形式中最主要的是圓形。楊雄曾形容“圓則杌棿,方則嗇吝”。這在當時是一個哲學命題,表達的是天的動蕩不定和地的內斂靜止。這一命題用在美學上,恰好表達了一種動態的、博大的美感。青白瓷碗造型圓潤飽滿,不露鋒芒,和宋代含蓄內斂的時代風尚相契合。青白瓷碗的功能和審美是相互作用和聯系的。圓的造型一方面是功能性的體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器物的整體之美和回環之美。這種回環結構一方面具有功能性要求,另一方面也體現了與自然的關聯,有“碗中天地”之感。由曲線構成的圓,可以看作曲線流動變化的循環往復,自造了一種圓滿的、無缺憾的形式美。曲線組成的圓更能體現一種活的生氣,使器物表現出一種靈動之美。青白瓷碗運用自己的藝術語言作為媒介,表達了特定時期歷史下的特定傳統文化,這是其他物象所不能替代的。正如美國著名哲學家杜威所言,每一種媒介所說的用任何其他媒介都不可能說得那么好,那么完整。
二、“制器尚象”和“有無相生”的文化內涵
人類文化遺產包含了有形與無形、物質與非物質,二者從內涵層面而言是不可分割的。制器在不同時期不同文化背景下崇尚的理念不同,比如在佛教盛行時,陶瓷器物的裝飾多蓮瓣紋。“制器尚象”最早出自西周《周易》之中,它的內涵不僅指仿物象,畢竟器物承載的不只是物象,還有意象。器物制作一般從簡單的象形逐漸發展到象意。只有在通曉宏觀規律之后,具備了概括和提煉的能力,才能在創作時抽象表達具有象意的符號。
所謂“制器尚象”,指的是在造物過程中從某個方面仿照特定物的“形象”(此“形象”可以是外在形象,亦可以是內在性質),以達到特定物審美意蘊在器物上的應用及體現,從而使得器物能夠糅合特定物的美感。陶瓷器物最主要的表現形式是“形”,即器型。器型不僅能決定器物的功能,還能展現器物自身的審美特點。宋代青白瓷碗多是圓器,拉坯的手法變化能夠令瓷器,尤其是碗類等圓器的造型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景德鎮青白瓷碗十分符合道家所推崇的“意在言外”“質樸至真”等審美取向。瓷碗中有一類瓷碗口部為花瓣狀,盞托底部也做成花瓣形態,整體均體現“尚象”這一內涵。
“有無相生”作為老子提出的重要哲學觀念,在推崇道家思想的宋代,器物美學的內涵對道家思想也有所反映。《老子》中有論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研究者對這句論述的釋義大致是在車的制造中,運輸是車的用途。同理,對于建筑和容器來說,從空間構成角度看,青白瓷碗器物的框架皆為兩部分,由“有”和“無”這一對矛盾構成,但青白瓷碗所擁有的內涵絕大程度上來自“無”這一非實體部分,而并非“有”的部分。如果說宋代青白瓷碗遵從了“制器尚象”的造物觀,那么其同時也未忽視“有無相生”的內涵意義。從藝術創作之初對事物感知與聯想,進行有和無的創作,到最后實現有和無的聯合,才能完成一件器物。“有”體現的都是具象的、有形的形式,“無”則是通過器物本身,表現創作者的技術和創作意圖。“有無相生”整體地展示了器物完成的整體意境,用自然而內斂的藝術語言表達了它的功能和藝術性。
從造物文化角度上來說,一方面青白瓷的造物過程與尚玉之道生成與發展相吻合,若把尚玉視為一種“道”,則其與青白瓷這一“器”相輔相成,互為表里。青白瓷碗舍去了繁復的紋飾,形成了線條更為流暢的器型。這種去繁成簡的方式使得器物呈現出靈動、飄逸的美感,從而體現了“尚自然之道”。
三、小結
不論是從觀感還是從觸感上來說,青白瓷碗追求類玉似玉的腳步就從未停止過。究其原因是,玉是不經人為過分雕琢而形成的自然質樸事物,更是大自然所饋贈的原材料,因此尚玉則是尚自然。由此可見,宋代青白瓷碗在各個層面上都追求“道法自然”的境界。器型法自然而又有所簡化,能夠從中尋得一個巧妙的契合點,使得器物在貼近自然的同時,又不拘泥于自然。以“道”制器能夠讓生動的自然變化法則發展于器物的外在結構和內部審美,使得事物的表象變化創造出因不同需求產生的內外之別。人類在討論器物合理性和實用性的過程中,常常會融入自我的認知。這類器物的完成不僅是技術的發展結果,同樣也是當時思想的凝結。我們感受觸碰青白瓷碗的器物本身,不僅僅是它的外部輪廓,更多的是體會其器物之意象、器物之道象。今天的設計審美經過歷史的傳承和發展,已經得到演變,人類通過當世科技和主觀意識形成了更新的認識,這種認識包含宋代哲學和美學體系,也外顯于器物。宋代青白瓷碗給予世人的不僅是功能的沿用,還有思想的交融。

宋青白釉刻花嬰戲蓮花紋碗 故宮博物院
一件器物的完成,需有形之“器”與無形之“道”結合。宋代青白瓷碗則正好融合了這兩極,能夠從有形之“器”中體察出無形之“道”。不論是尚玉之道還是尚自然之道,都能從具體的器物中窺見端倪,但又絲毫不覺突兀,同時還可以發現其在經意或不經意間所注重的有無相生之功能性。在各種人類活動中,造物活動可以說是人類生活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內容。青白瓷碗中承載的宋代美學觀念,正是以器為載,引發人們去感受優秀的古代文化之美,吸引人們傳承精良的技藝,讓人們在繼承與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過程中進一步增強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