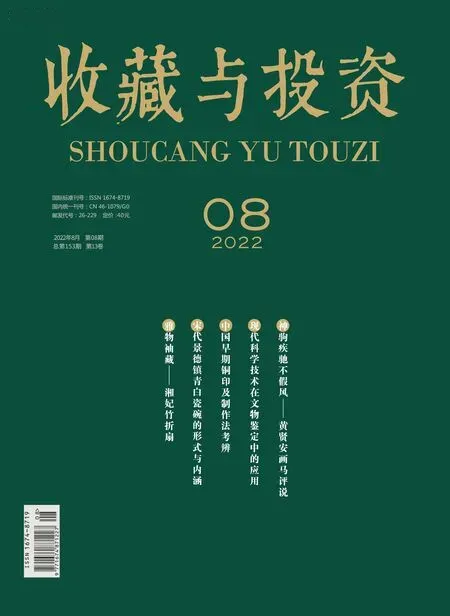中日傳統書畫裝裱與修復的差異
喬鑫宇(吉林藝術學院,吉林 長春 130031)
一、中日傳統裝裱與修復差異的起源
據文獻記載,中國最早出現裝裱技藝,是在公元5世紀也就是春秋戰國時期,《歷代名畫記》中曾提到“自晉代以前,裝背不佳,宋時范曄始能裝背”。從這里我們就可以看出,書畫裝裱在晉代就已流行,但當時的技術可能不夠完善,到了宋代,社會上已經出現了裝裱能匠,產生了許多流派與風格,“宋宣和裱”是這一時期的巔峰,為書畫注入了靈魂和生命,說明書畫裝裱的技術已經相當完善。日本的裝裱歷史則是始于其遣唐使入唐期間。唐代書畫盛行,繁榮華麗成為主流,日本裝裱藝術自此得到了啟蒙。唐朝奢靡、莊重的氣息對日本后來的裝裱風格起到了根本性影響,以至日本在如今的裝裱風格和材料上多運用大量富麗、華麗的錦緞,莊重氣息十足。但裝裱最初引進日本時多和茶文化掛鉤。日本茶室多懸掛宣和裱的立軸。宣和裱在當時的日本皇室以及上流社會得到了廣泛喜愛。隨著現代文化日新月異,日本善于接受不同渠道傳播過來的各種新型文化,且20世紀60年代左右,即日本經濟發展大跨步時,隨著裝裱原材料的更新以及當時審美文化的快速更新,日本在裝裱風格以及修復手段方面發生了較大變化,裝裱風格逐漸變得多元化,大膽融入了大量現代元素,并且裝裱的目的不再是單一地襯托畫面,而是強調整體融合與創新,出現了裱更顯于書畫的情況。用裝裱凸顯主題,利弊交織,這樣形成了日本當時獨特的裝裱風格,其修復運用了大量現代技術,增加了檢測、分析過程并配以電腦輔助,通過現代技術分析修復方案。現代技術為其提供了技術的根本支撐。中國文人講究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多追求素雅、隨和的風格,所以在裝裱方面以襯托其畫面高雅、秀麗和精美為主。形式上往往用裱襯其書畫,為避免喧賓奪主,多以素雅之色表現主體,更強調凸顯書畫本來面貌。自古就有“三分畫,七分裱”的說法,說明裝裱主要功能在于修飾主體,襯托書畫。
二、中日傳統裝裱的材料差異
在材料方面,因為中日在人文內涵、地理分布、氣候環境等多方面條件不同,所以二者裝裱修復所用的材料也大不相同。中國古代書畫裝裱早期以帛為主要材料,帛為絲制品,這是因為當時的絲織業發展較快,蠶織產業興盛。隋唐之后,錦繡、綾羅綢緞也成為裝裱的原材料之一,用綾羅綢緞裝裱的畫作品質精良。但由于這類裝裱材料僅供上流社會使用,使用帛作為材料的裝裱發展相對緩慢。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裝裱材料并未獲得大規模的創新。在用紙方面,我國早期多用藤紙和麻紙。明代之后,隨著造紙業的飛速發展,絹、綾是最為受用的,其次是用稻草和檀皮等材料制作的宣紙,這類宣紙由于具有良好的柔韌性、綿糯的性質且吸水性好,一躍成為裝裱的主流用料。
日本則因其地理和環境非常適合楮的生長與利用,所以日本的紙張大多數都是用楮皮做的楮紙,美棲紙、宇陀紙為使用楮皮原料所制成的代表紙。日本修復紙質文物多用麻紙、雁皮紙以及竹制的中國宣紙(畫仙紙)等。日本人多喜愛色彩濃烈、富麗堂皇的裝裱風格。為表示材料貴重,裝裱材料多利用織金錦和七子織等材料。中日在裝裱與修復方面存在的差別也包括糨糊的制作。日本制作糨糊采用的是與我國北方相近的熬制法。染色方面,中國多以礦物質染料或傳統國畫染料,多選用赭石、花青、藤黃等顏色,并在其中加入明礬固色;日本一般使用矢車草、丁子之類的草本植物染色,多以草木灰為固色原料,再到后來,轉為以工業染料為主。因為日本地理環境的原因,礦產資源較少,所以材料多以草木為原料。

圖1 楮紙

圖2 麻紙
三、中日傳統修復工具手段差異
首先是刀具的差別。在裁切畫心等方面,我國傳統用刀為立刀與馬蹄刀。馬蹄刀的刀身為純鐵打造,刀刃處加以精鋼,因刀型酷似馬蹄而得名。南派裝裱使用馬蹄刀較多,而北派裝裱中則更多應用立刀。立刀最大的特點為雙面開刃。日本的刀具風格迥異,主流使用的為一種被稱為“丸包丁”的刀,其刀身為半圓狀,而另一種則為與現在魚生壽司用刀非常相似的一種刀,外形似匕首,單面開刃。
其次是裝裱所用的刷子也存在許多差異。中國傳統裝裱修復多用棕刷,棕刷原料多為樹棕;用來上漿的排刷原料,大多為羊毛。日本則大量采用刷子,用得最多的是撫毛刷和水毛刷,這些刷子多以鹿毛、熊毛為原材料制成。日本多用水晶、玻璃珠子和瑪瑙等進行砑畫,而中國則用特制的石頭進行砑畫并打蠟,使裝裱材料更加光滑,方便收藏與存放。日本在大量西方新奇事物的影響下,熱衷于使用科學儀器,并將許多更精細的儀器,例如手術刀等引入裝裱材料,各種電子裝裱產品層出不窮,中國的傳統修復方式則更注重工藝本身,并融合修復理念,對原材料的選擇和應用遵循“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理念。
在畫心清洗上,我國首先是用溫水對受損、受污的畫心進行沖洗,慢慢去除污穢,然后用腹背紙分多次小心吸取液體,之后進行揭心。日本的方法則是使畫心向上,在其下面放上可以吸收水分的宣紙或麻紙,紙的下面還會放上毛氈,然后用刷子把水均勻地刷到畫心上,使畫心完全濕潤,等待片刻后更換下面的紙張,多次重復這一過程,直到畫心的污穢變少變淡。污漬去除后將畫放在環境適宜處晾干。日本還會用藻膠固色,預防顏料墨跡發生變花、跑色和脫落現象,然后在畫心畫面上覆蓋一層保護紙,從后背揭取托紙。所有這些工作都要在畫心沒干透的情況下快速進行。揭背紙時,中國多用排筆在畫心背面上糨糊,用先前染好的紙進行托心,日本則是先對畫心進行拼接、全色和修補等操作,拼接用料為美濃紙等楮紙,在畫上墻后還會進行多次調試,以盡力讓畫心與新材料完美融合。在全色方面,我國主張修復后的作品越接近原作越好,這樣有助于觀者了解真實的創作背景,力求復原最真的那一面,而日本則更在意畫心與材料顏色意境是否相符,更關注修復作品的品相、美丑等方面。
四、中日傳統裝裱的風格差異

圖3 馬蹄刀
中國的傳統裱件款式很多,例如三色裝、二色裝、一色裝、宣和裱、屏條裝和錦眉裝等,日本主流裝裱法則為佛裝裱、奴裱和大和裱等。日本佛教文化異常繁榮,這主要是受到唐朝禮佛的影響。宣和裱的風格影響最大,日本古代大多數建筑比較低矮,進門就需要褪去鞋物席地而坐,所以日本的裝裱裱件都不會太長,大多短小精悍,且橫幅偏多。中國建筑多舉架坡高,且以皇家為代表的上流社會廳堂多、門窗巨大、掛軸繁多。四方形的屏風更適合斗方四條屏等建筑裝飾,因此屏風尺寸多較長且寬。
由于佛教盛行,日本大多裱件被用于祭祀鬼神和佛像裝裱。日本創作風格和環境因素導致裝裱風格多為深色調,且他們大多喜歡以金、銀、玉、瑪瑙和象牙等為裝飾的裱件,試圖以奢華的形象凸顯社會地位,并且日本人天馬行空的創意也是一大特點,尤其是對鬼神畫作的裝裱尤為明顯。我國追求的是裱襯托畫,裝裱不可蓋過作品本身的風采,多以襯托其風采,修飾深意境界等為目的。這與兩國歷史環境也有很大關系。中國古代書畫繁榮,被裝裱的多為傳世佳作,畫作本身異常出彩,所以裝裱的功能以修飾保護畫作為主。走到今天,我國現代裝裱風格出現了許多創新。當今社會,裝裱傳統風格加入了大量現代元素,日本在這方面更是標新立異,兩國可以借鑒交流。
五、結語
中日傳統的書畫裝裱與修復存在許多差異,但本出同源,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影響下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兩種風格,不論好壞,二者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在當今社會,人們對歷史和文物愈發重視,傳統裝裱與修復也逐漸進入大眾視野。在科技日益發展的今天,筆者希望我國書畫修復吸收傳統裝裱精華,結合現代化技術手段,更好地保護傳世書畫珍品,使傳統藝術瑰寶煥發生機,把書畫裝裱與修復轉化為一種對技術、科學、藝術乃至歷史的傳承。

圖4 棕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