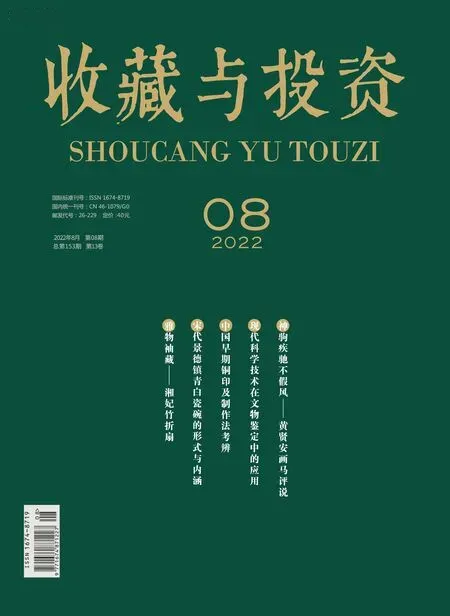《只此青綠》的宋代美學神韻
桂玲玲(西南大學 美術學院,重慶 400715)
《千里江山圖》是北宋畫家王希孟唯一流傳至今的作品,被譽為“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整個畫卷描繪出作者錦繡壯麗的山河之美。畫面中峰巒起伏綿延,江河煙波浩渺,氣象萬千,壯麗恢宏。《千里江山圖》在設色和用筆上繼承了傳統的“青綠法”,以石青、石綠等礦物質為主要顏料,顏色較為夸張,具有一定的裝飾性,被稱為“青綠山水”。
《只此青綠》是2022年虎年春晚展示的一段群舞,該舞蹈將《千里江山圖》中的青綠色山川抽離出來改編為擬人化女性人物形象,這一段舞蹈很好地展示了群山層巒疊嶂的概念。由于時間限制,節目未能展示完整版。完整版以“展卷、問篆、唱絲、尋石、習筆、淬墨、入畫”等篇章為綱目,講述了一位故宮青年研究員“穿越”回北宋,以“展卷人”視角,“窺”見畫家王希孟《千里江山圖》創作過程的故事。
一、繼承
(一)設色的借鑒
《只此青綠》通過著重體現表演服裝的水墨質感來演示毛筆暈染顏料浸潤紙上繪圖的瞬間。綠色、白色加青色營造出空氣感,配合有質感的面料呈現出濃墨到淡墨侵染的美感,淡墨遠山江河、濃墨染屋頂,展示了一幅氣勢磅礴、秀美異常的錦繡山河圖。青綠山水典型的特點在于其使用了牢固、經久不褪色的礦物質石青、石綠等色彩塑造層巒山川,畫面青綠相映,凸顯富麗堂皇。《只此青綠》作為以肢體表達藝術意象的舞蹈表演作品,其表演服裝對于整個藝術作品創作理念的表達尤為重要。群舞表演者中領舞者身著水墨侵染質感的青綠色舞蹈服飾。上裝從低到高為深綠、青綠再到淡青色,服裝下半身為深綠色舞蹈長裙,長水袖依次漸變侵染凸顯水墨質感。其他表演者同領舞人的服裝相比,上衣顏色要淺許多,她們的下裝與領舞者一致,上身服裝的顏色與領舞者水袖部分的顏色一致,為淡青色,無任何漸變。石青與石綠作為底色,讓袖子疊搭在一起時猶如山巒起伏,將襦纏繞至腰間,用裙型的層疊感形成山巒層疊之勢。色彩的風格走向是觀賞者對于舞蹈作品最直觀的感受,凡見過《千里江山圖》的觀眾總能從服飾色彩的搭配中找出靈感來源。在色彩上,除了服裝有所借鑒,表演者的妝容也與“青綠”二字相呼應。這段青綠舞蹈成為點睛之筆,主要取色于畫卷中的頭青和石綠,用漸變的色彩傳遞觀眾的情感。它生動還原了十八歲天才少年畫家描繪《千里江山圖》的傳奇身影。
(二)詩意和留白的繼承

《只此青綠》片段(2022 央視春晚)
詩意和留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極具浪漫色彩的部分。關于《千里江山圖》畫中展現的主題,各路學者說法不一。大多數人認可這幅圖是北宋生活的寫照;傅熹年認為表現的是江南水鄉;曹星原認為該畫“是出世、避世的場所,絕不是生活的寫照”;馮海濤說該畫“實際上是一件以道家思想為線索的宋代招隱畫卷”。雖然很難有一個標準的說法,但這幅畫的深意值得思考是肯定的。十八歲的天才畫家將對人生、對國家和對天下的寄托與感悟藏于畫中。《只此青綠》的舞蹈表演跨越時空,用不同的展示方式將這些疑問拋給了現代觀眾。中國傳統舞蹈向來偏愛喜慶和熱鬧的表演氛圍,人們力求通過顏色鮮艷的華麗服裝、滿眼笑意的眉目、大幅度的身體動作等使表演達到最高層次的“滿”,觀眾只需靜心觀賞即可,不用過多思考。反觀《只此青綠》的表演,無論是背道而馳,避開大紅大紫的飽和色彩,采用淡雅的青綠色調,還是舞蹈動作展示、隊形排列甚至是舞臺布局主題,都與“滿”字相距甚遠。整場表演動作似靜、神情似喜似悲似淡漠,演出結束后留給觀眾無限的遐想,讓他們去猜、去聯想、去感悟、去思考,各自在心目中去思索“青綠”的含義。一直以來,宋畫以極簡的美學風范聞名于世。這種基于哲理與頓悟的思想濃縮,摒棄了煩瑣的裝飾,追求簡單的筆墨與簡潔的藝術效果。舞蹈《只此青綠》開場“入畫”一幕將“寫意”之美推向全篇的頂峰。舞蹈演員還原了畫中青峰疊嶂、綠水隱現的場景,以不同造型和體態變化模擬山巒,舞蹈反映的不再是女性的柔美,而是大氣磅礴、氣勢恢宏的中國傳統文化沉淀的歲月之美。
二、發展
(一)山水的擬人化
擬人化是指畫筆到人的轉變,畫筆的繪畫過程由舞者通過表演展示出來,畫筆的軌跡就是舞蹈表演的來源。在這段舞蹈表演中,開場時舞蹈者們身姿各異地站在不同的位置,高低也不盡相同,姿態動作的各異象征著山峰的高低起伏,凸顯出群山之間風云變幻的山川雄競圖。《只此青綠》表演的開端是一張鋪開的空白的畫紙,主舞和其他表演者身穿的表演服顏色各異,這些服裝的顏色作為這幅畫卷畫筆的顏色登場。舞者代表著山川大河,既豪邁大氣又剛柔并濟,表演者的臉上亦無喜無悲、自信從容,仿佛她們不是在表演,而是《千里江山圖》中大好河山里的一部分。大河山川孕育了無窮的生命,女性的舞姿又恰如其分地展示出柔美的一面,這往往是中式繪畫美之所在。中式的美往往是剛柔并濟、優雅大氣的,就像舞者的動作除了女性的婉約之美外,其中還有豪邁的氣魄,二者完美結合演示出畫筆蘸上顏料在畫紙上揮灑自如的質感。《只此青綠》時而靜,時而動,時而利落,時而又溫婉如水,盡顯祖國山河之壯麗。《只此青綠》以《千里江山圖》在故宮的展覽為背景,通過現代展卷入場。央視播出的這段群舞是完整舞蹈結構詩句里的一個支點。舞蹈者作為卷中山水存在,擬人化的舞蹈表演,展現出不一樣的《千里江山圖》。
(二)跨越時空的結合
隨著時代不斷進步,科技不斷發展,今天藝術的表達不再具有單一性,部分藝術的表現方式日益呈現多樣化發展趨勢。《千里江山圖》繪畫作品以沒骨法畫樹干,用皴點畫山坡,豐富了青綠山水的表現力,鮮艷而不媚俗。畫家總體把握、周密布局,由七大組群山組成,像是某個具體地域的山勢作橫向展開,每組都將主峰和諸多輔峰組合起來,如同一座座山島矗立在江邊湖畔,形成互有聯系的“島鏈”。《只此青綠》的舞蹈表演,除了身姿挺拔、舞姿優美的舞者傾力表演外,現場的舞臺設計、背景布局、燈光、伴舞音樂等的互動配合也是《只此青綠》獲得成功的重要因素,這是多人參與的藝術活動。改編的舞蹈《只此青綠》擁有了比古代更多的欣賞者。春節期間,這個節目通過電視轉播的方式得以廣泛傳播,引起了許多人靈魂深處與宋朝美學文化的共鳴。“青綠”之于舞臺,象征物之所在的意境與況味,它在展卷人與王希孟輕盈、靈動、深沉的互動之外連接了跨越百年的時空。
三、欣賞者審美傾向的變化
(一)審美意趣導向——由個人向集體的轉變
宋代王希孟學習繪畫青綠山水時,社會正處于宋徽宗時代。王希孟描繪《千里江山圖》,對大好河山的贊美和對宋朝疆土的構想式創作,帶有一些對宋徽宗的討好意味。改編作品《只此青綠》的觀賞者是全中國的觀眾,是向所有觀看表演的人們傳達傳統文化之美,意在強化人們的審美意識,加強文化自信,不是刻意迎合某一單方面的審美傾向,創作者也更加自由。由于觀看人數的增加,主創團隊的壓力也隨之增大。不過正是因為前人留下了優秀的青綠山水畫卷,幾百年后的今天,舞蹈主創團隊才能在前人的基礎上取其精華,創造出包含傳統文化精神的優異作品。
(二)在不同時代,雅與俗所占比重不同
《千里江山圖》和《只此青綠》的不同之處在于前者所處的時代雅更多于俗,而后者則處于俗多雅少的境遇。宋朝藝術不再是上層階級的專屬,涌現了一大批雅俗共賞的優秀藝術作品,總的來說仍逃不出迎合士人階級雅的意趣的桎梏。如今的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愈加旺盛,越來越多的人更愿意欣賞脫離“庸俗”標簽的文藝作品。因此,像《只此青綠》這樣蘊含宋代美學精神的舞蹈劇目讓許多觀眾眼前一亮,觀眾對傳統文化精神的探索需求得到滿足,舞蹈表演更直觀、門檻更低,更有利于欣賞者欣賞藝術作品。在文娛生活中,雅要存在,俗也要存在。只有既滿足陽春白雪的藝術追求,又滿足大眾文藝需求,才能營造出健康的文化產業氛圍。
四、結語
宋代美學思想為后世藝術發展留下了寶貴的財富,對弘揚傳統文化也起到了正向引導作用。具體到舞臺藝術創作,那就是美學精神是意和觀念的東西,把意和觀念呈現在舞臺上,就需要藝術家們的創作。他們以舞蹈、音樂、美術等各種鮮活的形象在舞臺上出現。《只此青綠》通過舞臺實踐傳承中華傳統藝術之美,最終必將成為經典。
每一個時代,藝術的發展都有一定藝術思想的指導,藝術作品所呈現的意向包含人類的經驗、想象或感情的結晶。宋代的美學思想為各個藝術門類提供了發展方向,反過來,各類藝術作品所反饋的審美精神,都是對那個時代美學思想的豐富和發展。只有兩者互不偏航,文化藝術才能獲得良性的發展。目前,我們正面臨著部分主流審美思想偏離引發審美錯位的現狀,也導致一部分群體觀看現代藝術作品后產生強烈的空虛感。在物質追求遠超精神追求的今天,重拾思想顯得尤為重要。《只此青綠》的成功不只體現在表現形式、敘事手法和舞蹈技巧的創新上,更重要的是實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這是一次成功的探索。期待有越來越多《只此青綠》這樣的經典作品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