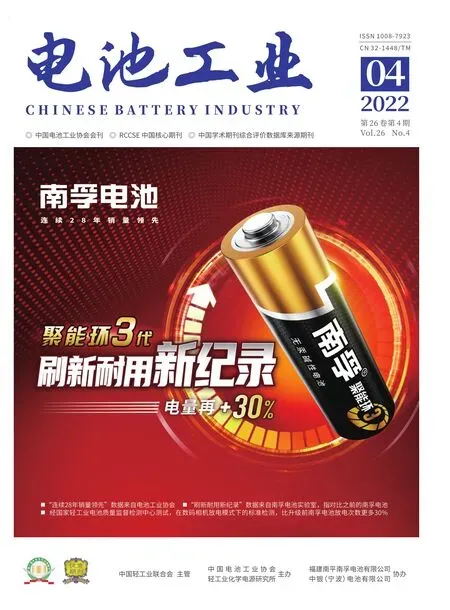親鋰材料在鋰金屬負極應用中的研究進展
陳 濤,李晶澤,邢健雄,劉芋池,王子豪
(電子科技大學材料與能源學院,四川 成都 610000)
1 引言
鋰金屬具有超高的理論比容量(3 860 mAh·g-1),最低的氧化還原電位(-3.040 Vvs.標準氫電極),如果能用于電池負極,將極大地提高電池的能量密度[1],但鋰金屬非常活躍,當與電解液接觸的時候,會與電解液反應在鋰金屬表面形成一層固體電解質界面(solid electrolyte interface,SEI)膜,SEI膜在結構上和成分分布上不均勻,并且與鋰金屬負極表面的接觸不穩定[1],鋰離子通過該膜到達鋰金屬負極表面發生電化學沉淀時,會在負極表面形成不均勻的沉淀形態,隨著循環的進行,逐漸形成枝晶形態,這降低了電池壽命,并且帶來安全問題,圍繞著抑制鋰枝晶的生長,學術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中在負極內部加入親鋰材料是廣泛采用的技術方案,本文綜述了親鋰材料的發現過程,各種不同親鋰材料的應用,討論了不同親鋰材料的特點,并總結了親鋰材料可能的發展方向。
2 親鋰性材料的發現
2016年4月斯坦福大學崔毅團隊[2]首次在實驗中發現親鋰性的物質可以誘導鋰的電化學沉淀行為,他們發現在10 μA·cm-2的電流密度下,Li在Mg、Al、Pt、Si、Sn、C、Cu和Ni等材料上進行電化學沉淀時,具有不同的成核勢壘,如圖1所示。

圖1 10 μA·cm-2的電流密度下鋰在不同物質上進行電化學沉淀的電壓曲線圖[2]Fig.1 Voltage profiles of various materials with some solubility in Li during Li deposition at a current density of 10 μA·cm-2[2].
根據這個發現崔毅團隊發現由于鋰成核過程中存在不同的過電位,鋰金屬優先沉積在沒有成核過電勢的晶種上。他們在Cu箔上放置Au箔,進行電化學沉淀實驗,發現在0.5 mA·cm-2的電流密度下0.1 mAh·cm-2的面容量下,Li優先沉淀到Au箔上(圖2(b)),隨后他們將Au箔個數增加,并且間距逐漸變大,發現Li仍然優先沉淀到沒有成核勢壘的Au箔上(圖2(c)),當Au以納米顆粒的形態存在時,Li依然優先沉淀在Au上(圖2(d)),當Au以三角形陣列的形式存在于C和Cu基底上時,Li仍然優先沉淀到無成核勢壘的Au三角陣列表面(圖2(e,f,g)),利用Ag做實驗時,他們得到了同樣的結果(圖2(h)),而將Cu以三角形陣列的形式存在于C基底上時,發現Li并沒有優先沉淀的方向,容易形成鋰枝晶(圖2(I))。

圖2 鋰金屬的圖形化沉積[2]Fig.2 Graphical deposition of lithium metal[2].
通過實驗,他們驗證了親鋰性材料能夠誘導Li+的電化學沉淀,并且他們分析了其機理,發現親鋰材料與鋰在常溫下能形成合金,從而能為鋰離子的電化學沉淀提供過渡層,另外這些親鋰材料與鋰具有相似的晶體結構。
3 親鋰性材料的應用
根據崔毅團隊的研究成果,很多親鋰性材料被應用到鋰金屬負極中,這些材料與鋰具有較強的結合能,包括碳材料、陶瓷材料和金屬材料等。
廈門大學孫世剛團隊[3]在鋰金屬負極內部構建了三維碳骨架以及石墨烯納米片實現對鋰枝晶的抑制(如圖3所示),他們利用三維碳骨架代替銅箔做集流體,增大了電化學反應面積,降低了有效電流密度,利用碳骨架表面的石墨烯片的親鋰性,實現了鋰離子的均勻的電化學沉淀,有效抑制了鋰枝晶。

圖3 三維碳骨架及其石墨烯片的掃描電鏡圖及其X射線衍射圖[3]Fig.3 SEM and XRD analysis of three-dimensional carbon skeleton and graphene sheet[3].
胡良兵研究團隊[4]在三維碳骨架表面覆蓋親鋰的SnO2層同樣實現了抑制鋰枝晶生長的目的,在與磷酸鐵鋰(LFP)組成的全電池測試中,在2 C倍率下,500個循環內實現了100.9 mAh g-1的可逆比容量以及99.7%的庫倫效率(圖4)。

圖4 Li-CF|LiFePO4全電池的電化學性能測試[4]Fig.4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test diagram of the Li-CF|LiFePO4 full battery[4].
清華大學張強團隊[5]利用電化學方法在碳纖維上電化學沉淀親鋰的Ag納米顆粒,利用Ag納米顆粒的親鋰性,在300 ℃的溫度下,可以將Li預存到碳纖維內部,在Li-S電池測試中表現出良好的電化學性能。
除了在碳表面進行親鋰化修飾,在銅表面覆蓋親鋰層也是眾多團隊研究的對象。中國科技大學俞書宏團隊[6]利用電化學方法在Cu納米線上覆蓋一層親鋰的Ni,也達到了抑制鋰枝晶的目的(如圖5所示)。

圖5 Li-Cu@Ni復合鋰金屬負極充放電過程結構變化示意[6]Fig.5 Schematic diagram of structural change of composite lithium metal anode during charging and discharging[6].
楊全紅團隊[7]通過簡單固液反應在泡沫銅骨架表面生長出Cu2S納米線,利用Cu2S的親鋰性改進了泡沫銅對鋰的浸潤性。
對三維導體進行親鋰化修飾雖然能夠誘導鋰離子的均勻沉淀,但是無法誘導鋰離子從負極底部進行電化學沉淀,電化學反應同時發生在電極表面和內部,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很多研究團隊對鋰金屬負極內部進行了親鋰的梯度化處理,武漢理工大學麥立強團隊[8]在負極底部構建了親鋰的氧化鋅/碳納米管底層,在頂部構建了憎鋰的碳納米管,中間由過度層有序構成(如圖6所示)。親鋰的底層可以誘導鋰從底部開始沉淀,頂層的憎鋰層可以抑制鋰枝晶生長,中間的緩沖層可以防止因親鋰、憎鋰的突然轉變而產生明顯的鋰枝晶分級層,從而改善了負極的電化學性能。

圖6 梯度化親鋰結構[8]Fig.6 Schematic diagram of graded lithiophilic structure[8].
4 結論與展望
雖然親鋰材料在提高鋰金屬負極的電化學性能中得到了廣泛研究,但是親鋰性與結合能、表面能以及晶格失配度等的關系還缺乏深入研究,另外親鋰材料在鋰離子電化學沉淀的初始階段能夠誘導鋰離子的均勻沉淀,但是在后續的電化學沉淀中,鋰離子的電化學行為主要受電解液的鋰離子傳導率、電極/電解液界面穩定性的影響,如何將親鋰材料與改性電解液和穩定電極/電解液界面結合起來共同提高鋰金屬負極的電化學性能是將來需要重點關注的研究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