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創傷后應激障礙癥狀群變化軌跡及其影響因素
王雯沁,吳敏娟,李俊花,馮國和,張邢煒
(1.杭州師范大學 護理學院,浙江 杭州 311121;2.杭州師范大學 附屬醫院,浙江 杭州 310015)
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創傷性事件,具有高發病率、高致死率的特點,常導致AMI生存者并發如抑郁、焦慮及創傷后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等心理問題。既往研究顯示,AMI患者術后PTSD的發生率約為4%~28.3%,其中中青年的發生率為34%,表現為再體驗、回避、麻木及高警覺等典型癥狀群,這些癥狀常協同發生且相互關聯,約2/3的患者在起病2年后仍存在上述癥狀,不僅使心血管事件的復發率與死亡率增加了一倍,對患者的生存質量也造成了嚴重的影響。
抑郁、焦慮等負性情緒在中青年AMI患者術后的發病率高達52.98%,其與PTSD的共病率約為PTSD單一患病率的3倍,是PTSD發生的關鍵因素。目前有關中青年AMI后 PTSD現狀的研究多為橫斷面調查,其隨疾病進展的變化規律尚不明確。縱向調查則可識別中青年AMI患者PTSD癥狀變化軌跡,并據此為患者制定具有前瞻性的干預措施。傳統的縱向數據分析法僅集中于各個測量點的組平均值,關注總體的發展趨勢,將個體水平的差異歸結于誤差項中,無法解釋個體間的差異。本研究擬采用潛增長曲線模型(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LGCM),綜合考慮總體水平的平均變化趨勢和個體間的發展差異,縱向調查探究中青年AMI患者術后1年PTSD癥狀變化特征及影響因素,以期為制定具有前瞻性的、個體化的延續性心理護理干預措施提供理論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用便利抽樣法,選取2018年1月—2020年12月在杭州師范大學附屬醫院心內科住院治療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納入標準:①臨床首次診斷為急性心肌梗死;②18~60周歲;③接受冠狀動脈介入支架植入術;④知情同意。排除標準:①合并有其他嚴重疾病或嚴重并發癥;②有癡呆或其他精神疾病;③聽力受損或交流障礙;④既往經歷過創傷事件者。本研究通過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查,患者知情同意。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資料調查表 自行設計,內容包括人口學資料(年齡、性別、婚姻、文化程度、付費方式等)及疾病相關資料(如是否存在并發癥、犯罪血管分布、術中知曉程度等)。
1.2.2 PTSD癥狀問卷中文平民版(PTSD checklist-civilian version,PCL-C) 該量表由美國PTSD癥狀研究中心制定,魏玉兵等于2011年對量表進行修訂,包括再體驗(5個條目)、回避(2個條目)、情感麻木(5個條目)、高警覺(5個條目)4個癥狀群。根據癥狀嚴重程度采用 Likert 5 級評分法,總分為 17~85 分,分值越高,PTSD發生的可能性越大,≥38分為創傷后應激障礙癥狀陽性。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07。
1.2.3 綜合性醫院焦慮抑郁量表(HADS) Zigmond等研發,包括焦慮(7個條目)和抑郁(7個條目)2個分量表,采用0~3分4級評分,每個分量表總分為0~21分,>7分即可判斷存在焦慮或抑郁。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84。
1.3 資料收集方法 在行冠狀動脈介入支架植入術后3 d(Time 1,T1)及出院后3個月(Time 2,T2)、6個月(Time 3,T3)、12個月(Time 4,T4),由課題組成員發放問卷及電話隨訪,采用統一指導語講解問卷內容。閱讀或填寫困難者,由研究者逐條復述并客觀記錄,以確保數據的準確性和真實性。問卷當場發放,當場回收。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本研究共發放問卷280份,其中111例患者被診斷為PTSD,PTSD陽性率為39.64%。對111例PTSD癥狀陽性患者開展正式隨訪,其中106例患者完成全程隨訪,年齡23~60歲,平均(50.05±8.56)歲。106例患者中,男性95人(89.6%),女性11人(10.4%);已婚97人(91.5%),未婚7人(6.6%),喪偶2人(1.9%);文化程度小學及以下31人(29.2%),初中46人(43.4%),高中/中專17人(16.0%),大專7人(6.6%),本科及以上5人(4.8%);費用支付方式為自費的26人(24.5%),新農合36人(33.9%),省市醫保44人(41.6%);有并發癥19人(17.9%),無并發癥87人(82.1%);犯罪血管分布為左主干16人(15.1%),前降支51人(48.1%),右冠27人(25.5%),回旋支12人(11.3%);病情知曉程度情況為完全不知曉31人(29.2%),部分知曉29人(27.4%),完全知曉46人(43.4%)。
2.2 量表評分情況 PTSD各癥狀群、抑郁及焦慮的得分均為術后第3天最高,隨后均出現下降趨勢,差異有統計學意義(<0.001)。患者在各時間點的得分情況見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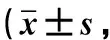
表1 106例中青年AMI患者各時間點的PTSD、抑郁、焦慮得分情況分)
2.3 中青年AMI患者PTSD各癥狀群的變化軌跡 以PTSD各癥狀群及總分的4次測量結果建立LGCM,在模型1中將截距固定為0,斜率分別固定為0、3、6、12,用來檢驗線性LGCM的擬合度指數及參數結果,在模型2中將截距固定為0,測量時間T1和T4的斜率固定為0和1,T2、T3的斜率進行自由估計,用來檢驗不定義的LGCM的擬合度及參數結果,相鄰因子載荷的估計值之差表示所對應的相鄰測量時間之間發生的改變量。由結果可知除高警覺外,其余3個維度及PTSD總分的不定義無條件潛增長模型擬合結果均優于線性增長模型,而在高警覺維度中,線性模型未達到擬合效果,不定義曲線模型中各擬合度指標達到模型分析標準要求。見表2。各癥狀群截距與斜率均呈負相關,說明各癥狀群初始水平越高其改善速度越快。通過各癥狀群T2、T3的因子載荷可知回避和高警覺癥狀群的改變主要集中在院后6個月內;再體驗和情感麻木癥狀群的下降幅度在院后3個月內較小。見表3。

表2 線性及不定義的無條件潛增長曲線模型的系數及擬合指標

表3 中青年AMI患者PTSD癥狀群的因子載荷及協方差估計
2.4 中青年AMI患者PTSD變化軌跡的影響因素分析 將抑郁、焦慮作為時間變化協變量,性別、婚姻、文化程度、付費方式、是否存在并發癥、犯罪血管分布、病情知曉程度作為時間恒定協變量構建不定義潛增長曲線模型。結果表明,該條件模型的擬合度良好:=68.412,=49,=0.035,=0.934,=0.890,=0.061,=0.064。協變量預測效果提示,婚姻、文化程度、付費方式及犯罪血管分布情況對中青年AMI患者PTSD的截距和斜率均無影響(>0.05);而性別、 是否存在并發癥、病情知曉程度對患者PTSD的初始水平存在影響(<0.05),其中病情知曉程度對患者PTSD的改善速度存在影響(<0.05),見表4。隨訪期間中青年AMI患者的焦慮、抑郁水平對相應時期的PTSD癥狀均具有正向影響(<0.01),見表5。加入協變量的潛增長模型見圖1。

表4 時間恒定協變量對PTSD變化軌跡的影響

表5 抑郁、焦慮對中青年AMI患者PTSD變化軌跡的影響

圖1 加入協變量的中青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創傷后應激障礙的不定義條件潛增長模型Figure 1 Undefined conditional latent growth model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young and middle-aged AMI patients with the addition of covariates
3 討論
本研究通過構建潛增長模型探討中青年AMI患者術后1年PTSD癥狀群的縱向變化軌跡,結果顯示患者PTSD癥狀群的變化呈曲線遞減趨勢,除回避維度外,其余各維度均存在個體間差異。該現象的發生可能為:①AMI起病突然、進展迅速,對患者的健康而言是一種持續潛在的威脅,大多數患者對現狀無法接受,因此在發病初期PTSD癥狀較為明顯;②在恢復過程中,患者對疾病的認知逐漸加深,并通過積極參與心臟康復,運動耐力得到恢復,自我管理能力呈可持續增長,使得患者在康復過程中更加從容、踏實;③由于個體之間存在自我管理能力、社會因素等方面的不同,其PTSD癥狀群的初始水平及變化亦存在差異。
本研究發現,回避和高警覺癥狀群的改變主要集中在院后6個月內,其后的下降速度緩慢;再體驗和情感麻木癥狀群的下降幅度在院后3個月內較小,主要集中在出院3個月后。說明中青年AMI患者回避和高警覺癥狀的改善可能先行于再體驗和情感麻木癥狀的改善。與本研究結果不同的是,由地震或戰爭引起的PTSD以再體驗為核心癥狀,當再體驗癥狀改善后,其余癥狀群相繼得到顯著改善。可能是由于本研究中的中青年患者擔負著重要的家庭和社會責任,難以在早期客觀理智地面對疾病對身心造成的巨大壓力,常采取回避的態度對待疾病相關治療;其次,由于AMI起病時癥狀兇險、進展迅速,伴有強烈的瀕死感,導致患者術后對軀體癥狀(如血壓升高、心率加快等)的變化高度警覺,并將其理解為發生心血管不良事件的信號。而后隨著軀體功能的恢復以及對疾病的認知逐漸深刻全面,回避和高警覺的癥狀得以改善。由于AMI患者再體驗癥狀主要表現為對當下或對未來的預感,如擔憂心臟事件再次發生或最終死于心臟事件,當回避態度改善后,患者積極配合治療,對疾病的良好預后重拾信心,同時有效改善了負性情緒。因此,護理人員應重視中青年AMI患者術后PTSD癥狀的識別與篩查,并根據癥狀群的變化軌跡特征開展心理干預和院后隨訪。
本研究結果發現女性、存在并發癥、術中知曉程度低的患者,PTSD的初始水平更嚴重,且術中知曉程度與PTSD改善速度呈正相關。其中術中知曉指患者在PCI手術過程中的意識狀態,即對手術過程的記憶程度,其與PTSD的關系與現有研究結論不一致,可能因為現有相關報道均為復雜手術、麻醉方式為全麻,術中知曉的發生常因麻醉深度不夠導致。而本研究的PCI術為微創手術,麻醉方式為局麻,對患者的創傷小,患者在術中感到不適能夠向醫務人員及時反饋,有利于緩解緊張、恐慌情緒。因此,護理人員在臨床工作中應加強患者術前、中、后的認知指導及心理干預,以預防PTSD的發生。
本研究結果亦提示,在4個時間點上,抑郁、焦慮水平的變化能正向影響中青年AMI患者PTSD癥狀的軌跡,即抑郁、焦慮水平越高的患者其PTSD癥狀越嚴重。表現為在康復行為方面,焦慮、抑郁的發生會降低患者治療積極性及依從性,阻礙其參加心臟康復活動,影響其對疾病的正確認知,從而影響患者的預后及生活質量;在疾病轉歸方面,焦慮抑郁易引發血栓形成、增強交感神經興奮性從而降低患者的心率變異性、加重心肌耗氧量,增加心血管不良事件的發生率及患者的死亡率,上述因素易使患者長期處于創傷造成的心理應激中,故其PTSD癥狀水平也較高。
綜上所述,中青年AMI患者PCI術后PTSD癥狀群變化軌跡均呈曲線下降趨勢,其中回避、高警覺癥狀群的改變可能先行于再體驗和情感麻木癥狀群。女性、存在并發癥、術中知曉程度低的患者其PTSD癥狀初始水平較高,其中術中知曉程度對PTSD癥狀的改善速度有正向影響,且焦慮、抑郁情緒與PTSD癥狀呈正相關。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AMI術后制定以PTSD為重點的前瞻性心理干預方案的依據,但隨訪周期只有一年,相對于整個疾病病程較短。未來進一步的研究可延長追蹤的時間,綜合考察患者的社會環境、家庭背景、經濟情況等多方面因素在其PTSD癥狀發展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