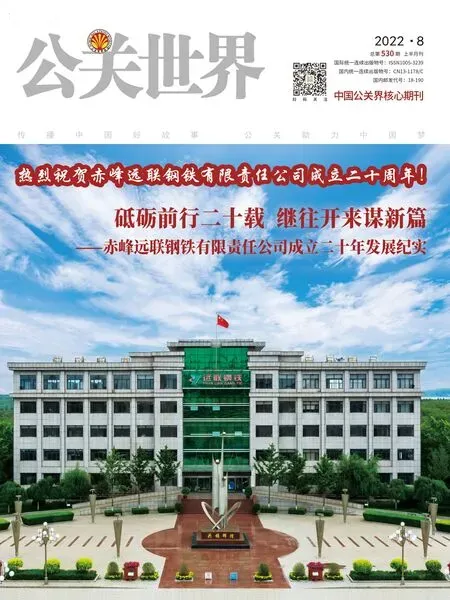任建民:融入國際話語體系,全面講述中國故事
“只有自己先全面認識自己的國家,在做對外宣傳的時候才能更加有底氣,更加客觀全面地講好中國故事。”
好的中國故事需要哪些內容要素?
講故事,就要講他人喜歡聽、內容有吸引力的故事。這是講好中國故事的關鍵。從同理心的角度來說,想講吸引人的故事,那講故事的人就需要先考慮自己講的這個故事是否有趣、是否有吸引力。只有在自己也覺得這個故事很有意思的時候,故事才有可能吸引到他人。
除此之外,講故事也要求講述者有豐富的觀察生活的經歷。這讓我想起來我在青海基層工作的那兩年。那個時候我特別注意貼近和深入基層,了解到了許多我們國家的真實情況,收獲到了很多在大城市所不能體驗到的經歷,這對我現在從事的對外傳播工作是特別有幫助的。
我們國家既有北京、上海這種繁榮發達的大城市,也有農村、山區這種相對落后和貧困的地區,這是我們國家的兩面。我覺得我們只有自己先全面認識自己的國家,在做對外宣傳的時候才能更加有底氣,才能更加客觀全面地講好中國故事。有人認為我們做對外宣傳不能只宣傳我們國家的成就,也有人認為做外宣工作的時候不應該反映我們國家的不足,應該多宣傳積極的一面。我認為,我們在做外宣工作的時候應該以正面宣傳為主,但不足的一面也需要客觀地反映出來,讓讀者通過我們的宣傳工作了解到立體的中國。讀者如果通過我們的賬號看到了多方面的中國,就會覺得我們的宣傳工作更加真實、客觀、具有全面性,對我們的信任度也會更高。
“我正經歷著互聯網對傳統媒體行業產生巨大沖擊的變革時刻”
我們了解到您之前做科技新聞和體育新聞,現在在做國際新聞,這之間的跨度似乎非常大。您覺得國際新聞工作和您之前的工作內容相比有哪些特殊性?您又是如何適應這一跨越和轉變的呢?
我覺得國際新聞工作的特殊性在于讀者群的不同。原來的新聞工作都是面向國內的中文讀者群,現在做對外傳播工作主要是面向國外的讀者群。
比起具體的工作內容方面的轉變,我覺得更大的轉變實際上是由互聯網帶來的媒體行業的轉變。
從媒體的角度來說,媒體本身是二次販賣信息的中介機構。互聯網發展起來之后,信息傳播的手段和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信息傳播變得非常容易,任何人都可以利用互聯網成為信息傳播的主體。在這種情況下,媒體機構專業人員的不可替代性和特殊性自然而然受到了強烈的沖擊,我們的重要性可能僅僅體現在普通民眾沒辦法代替的事情上,例如報道危險的突發事件之類。實際上,全球的媒體行業都在萎縮,從業人員減少,規模縮小,即使是《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芝加哥論壇報》這些在全世界都鼎鼎大名的媒體機構,現在也都很難獨立運營了。這種轉變應當如何適應呢?我覺得大家都還處于摸索的階段。
“文字傳播和視頻傳播的重要性是并列的,都應該受到重視”
您認為講好中國故事,需要哪些具體的傳播形式呢?具體有哪些要素呢?
不可否認的是,在目前這個時代,對于講中國故事而言,視頻這種形式具有非常大的優勢。對各個方面的事件而言,視頻都是最直觀最有效的傳播方式,而文字的描述總是很蒼白的,在故事的敘述上不如視頻直觀。但是文字的傳播形式仍然存在重要性。相較于有趣又直觀的視頻而言,文字更能傳達有影響力的觀點與看法。所以,其實文字和視頻都是好的傳播形式,只是兩者的特點不同,適合傳播的內容不同,總體來講兩者的重要性是并列的。就我自己的工作經歷而言,我們在運營人民日報賬號的時候也會盡量多發視頻。
“針對惡意抹黑,必須果斷出擊才能贏得掌聲”
您覺得在做國際新聞的過程當中,自己和團隊講的最好的中國故事是什么呢?能不能跟我們分享一下?
2011年、2012年,人民日報海外社交媒體帳號初創的時候,我們做了很多非常靈活的內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印象最深的是,當時推特上有一個叫做RevelantOrgan的個人大V級賬號,刻意模仿我們國家政府的官方語氣、結合我們國家的時事熱點,發布一些諷刺我們國家的推文,在推特上影響力還比較大。我們就在推特上直接@他,對他發布的內容逐一進行反駁。我們和那個賬號的反擊戰引起了推特上的媒體的圍觀,有包括《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路透社在內的幾十家媒體對此進行了報道,我們賬號的影響力由此得到了迅速的擴大。
“被貼‘標簽’、被限流是我們在外講好中國故事的現實困難”
在工作當中,您在講好中國故事這件事情上面遇到過哪些困境?
我們遇到的困難是所有社交媒體平臺近年來給中國媒體“貼標簽”,標注上“中國官方媒體”。受西方媒體長期抹黑報道的影響,西方民眾對我國的認識有很深的誤會。在此大背景下,這樣的標簽就會造成西方人的誤解,一方面讓他們誤以為我們是完全代表中國政府發布言論,另一方面也會先入為主地認為我們發表的觀點、發布的信息都是不客觀、不可信的。這對我們的外宣工作是很不利的。
除此之外,這些社交媒體平臺還會對我們的賬號在后臺進行限流,使得讀者無法閱讀到我們發布的動態。我們現在的Facebook賬號,單條推文理論上閱讀量應該能達到8000多萬,但因為限流,現在每一條只有十萬左右閱讀量。
“不僅僅是個人角色上的轉變”
從一開始的一線記者到現在的人民網美國公司總經理,您覺得在講好中國故事的議題之下,您自己扮演的角色有沒有發生什么轉變呢?
從個人角色的轉變上來說,我最大的轉變是從一個采訪寫稿的記者變成了一個團隊的領導者。這個團隊人數不多,但從大的方面來講,我們運維的帳號,實際上在海外代表了人民日報,在很多外國人眼中我們也被當作了中國黨和政府的代表,因此責任十分重大。
“我們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去建立起自己的全新話語體系,現階段應當做的是融入”
中國在對外傳播的過程當中,應該以怎么樣的姿態去和不同的受眾進行對話呢?是作為舊牌桌上的新玩家,融入已有的話語體系,用容易接受的話語來宣傳呢;還是作為一個新牌桌上的莊家,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呢?
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進行直接有力的宣傳,就要求我們擁有堅實的粉絲基礎和強大的影響力。就現狀而言,我們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去建立起自己全新的話語體系。所以我覺得現階段我們應當做的是融入,在現有的國際體系下,用他人能夠接受的話語和方式來傳遞我們的聲音。在講述中國故事這一方面,我們還處于新手時期,很多事情尚待摸索與學習,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要繼續提高我們國家的實力,同時也要提高講故事的本領,兩者結合才能讓我們的對外傳播事業越做越好。
訪談總結
本次訪談以“如何立體地講好中國故事”為主題,重點與任建民先生探討了中國故事的內容要素、講述中國故事的過程中遇到的困境、對外傳播時是否應融入現有的話語體系等問題。任建民先生也與支隊成員進行了積極的互動,同支隊成員交流了對我國講述中國故事的現狀的看法,并對正在及未來講述中國故事的青年學子們寄予了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