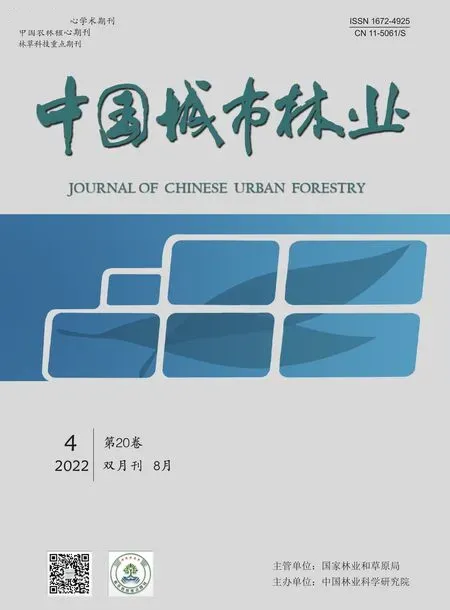城市綠地春季潛在花粉污染風險評估*
周江鴻 夏 菲 車少臣 李新宇 李 潔 劉育儉 張 卉 葉彩華 尤煥苓
1 北京市園林綠化科學研究院 北京 100102 2 北京市頤和園管理處 北京 100091 3 北京市天壇公園管理處 北京 100061 4 北京市氣象服務中心 北京 100089
園林植物是城市中有生命的綠色生態基礎設施,承擔著改善城市生態環境、維護公眾健康和優化人居環境等重要功能,然而有些植物的花粉卻含有特殊的抗原蛋白,能夠誘發人體的過敏性反應(俗稱花粉癥)[1-3],在許多國家已經成為一種季節性流行病,嚴重危害人體健康[4-5],因此許多研究者建議將致敏花粉作為一種植物源性空氣污染物進行治理[6-7]。花粉污染評價是花粉污染研究的重要內容,也是正確認識和處理花粉污染問題的前提條件。廖鳳林[8]提出了致敏花粉種類含量評價法、空氣花粉污染指數評價法和花粉癥發病率評價法,前兩種方法均是基于已建成綠地的逐日空氣花粉監測數據,而第3種方法則是基于醫院門診數據或市民的問卷調查數據。但是這3種方法均無法在規劃設計階段對新建綠地的潛在花粉污染風險進行評估。
影響空氣中花粉含量的因素包括植被因素、地理因素和氣候因素等[9-10],其中植被因素是決定性因素,特別是產生氣傳致敏花粉的高大喬木,其生長緩慢、生命周期長,一旦種植,幾十年甚至幾百年都不會改變,對空氣中花粉含量的影響是穩定的、持久的。因此,加強園林綠地規劃設計方案的審核把關,強化源頭管控,嚴格限制在城市新建綠地中大量使用致敏花粉源樹木,才能逐步解決花粉過敏的問題,但如何根據園林綠地規劃設計方案中的植被組成情況對花粉污染風險進行評估尚未見報道。
本研究利用6臺孢子捕捉儀連續3年(2019—2021年)對北京市3個主城區空氣中的花粉種類和濃度進行監測,分析不同樹種的種植密度與其最大日花粉濃度之間的關系,建立根據綠地植被組成對其潛在的花粉污染風險進行評估的數學模型,對于建設和諧宜居的城市綠地環境具有重要意義。
1 材料與方法
1.1 花粉樣品采集
本研 究 針 對 柏 科(Cupressaceae)、榆 科(Ulmaceae)、楊屬(Populus)、柳屬(Salix)、白蠟屬(Fraxinus)、銀杏科(Ginkgoaceae)、松科(Pinaceae)和桑科(Moraceae)8類風媒花喬木,使用英國Burkard公司生產的HIRST型孢子捕捉儀進行花粉樣品采集;分別在頤和園(海淀區)、天壇公園(東城區)和北京市園林綠化科學研究院(朝陽區)的不同位置各設置2臺HIRST型孢子捕捉儀,于2019—2021年連續3年對春季空氣中的逐日花粉濃度和種類進行監測,采用Cressington 108auto離子濺射儀和Phenom ProX臺式掃描電鏡進行樣品制備和觀察[11]。
1.2 花粉濃度計算
HIRST型孢子捕捉儀進氣孔長14 mm,寬2 mm,每小時轉動2 mm,每小時采樣區域面積為28 mm2;計算每立方米空氣中花粉總濃度的公式為:

式(1)中,N為空氣中花粉總濃度,A為每平方毫米計數點內的花粉個數[11-12]。
在5 KV電壓、250倍放大倍數下,每視野面積約為1 mm2,統計1 mm2視野內的花粉數目,每小時采樣區域統計3個視野,以一天中所有測量值的平均值作為當日花粉總濃度。每視野內選取10粒花粉,放大至6000倍左右,測量其大小,觀測其形狀、極面和赤道面的表面紋飾、萌發溝或萌發孔的數量及形態,參照《中國木本植物花粉電鏡掃描圖志》和《北京常見植物花粉圖鑒》等[13-16]確定花粉種類。由于同科或同屬不同樹種的花粉形態具有很高的相似性,種類鑒定時將其歸為一類,如將所有柏科樹木花粉歸為柏樹花粉、將所有松科樹木花粉歸為松樹花粉、將所有楊屬樹木花粉歸為楊樹花粉,計算當日每類花粉所占的比例,再結合空氣中日花粉總濃度,最后得到某類樹木的日花粉濃度。計算公式如下:

1.3 花粉污染風險評估
以某類花粉濃度最高的一天作為該類樹木的盛花期,以該日的花粉濃度對其花粉污染風險進行評價。空氣中樹木花粉濃度主要與采樣點附近的樹木種類和種植密度有關,但也受氣象因子(如溫度、光照、降雨、風力和風向等)的影響。為了消除這些氣象因素的影響,本研究采用連續3年3個研究區域6臺孢子捕捉儀所獲取的8類風媒花喬木花粉濃度數據的平均值進行回歸分析。統計各研究區域內不同樹種的數量,根據各區域的面積計算各樹種的種植密度(株·hm-2)。
1.4 數據分析
利用IBM SPSS Statistics 22.0軟件進行數據統計分析,以某類樹木的最大日花粉濃度為因變量(Y),以該類樹木的種植密度為自變量(X),選擇“輸入(強迫引入)”方法進行線性回歸分析,建立評價模型,再根據該類樹木的種植密度對其在盛花期可能產生的最大花粉污染風險進行定量評估。
樹木氣傳花粉濃度(污染風險)等級的劃分參照美國國家過敏癥研究總署的樹木花粉濃度劃分標準[17](表1)。

表1 樹木氣傳花粉濃度(污染風險)等級
2 結果與分析
2.1 2019—2021年春季不同樹木的最大日花粉濃度
由表2可知:2019—2021年3—4月,頤和園的桑科、柏科和柳屬樹木的最大日花粉濃度平均值分別為1205.51、436.34、205.44粒·m-3,屬于高濃度等級;楊屬、白蠟屬、銀杏科和松科樹木的最大日花粉濃度平均值在15~89粒·m-3,屬于中濃度等級;榆科樹木最大日花粉濃度平均值低于14粒·m-3,屬于低濃度等級。
2019—2021年3 —4月,天壇公園的柏科樹木的最大日花粉濃度平均值為1249.43粒·m-3,其中2019年和2020年柏樹最大日花粉濃度均超過1500粒·m-3,達到極高濃度等級;桑科樹木最大日花粉濃度平均值為98.67粒·m-3,屬于高濃度等級;其余樹木的最大日花粉濃度平均值均在15~89粒·m-3,屬于中濃度等級(表2)。
2019—2021年3 —4月,北京市園林綠化科學研究院的柳屬、桑科樹木和銀杏的最大日花粉濃度平均值分別為238.48粒·m-3、104.75粒·m-3和90.21粒·m-3,屬于高濃度等級;其余樹木的最大日花粉濃度平均值均在15~89粒·m-3,屬于中濃度等級(表2)。
2.2 各研究區域不同樹木的種植密度
頤和園是我國現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園林,全園總面積290 hm2,現有常綠喬木10種,2.2萬株;落葉喬木82種,1.3萬株。萬壽山前山以側柏和圓柏為主,后山則以松樹為主;昆明湖沿岸種植了大量桃樹和柳樹[18]。由表3可知:頤和園中柏樹的種植密度最高,為47.03株·hm-2;其次是柳樹,為12.19株·hm-2;第3是松樹,為11.68·hm-2;楊樹和榆科樹木的種植密度均為2.61株·hm-2;桑科樹木、白蠟和銀杏的種植密度分別為1.40、0.66、0.23株·hm-2(表3)。

表3 3個研究區域產生氣傳花粉樹種的種植密度株·hm-2
天壇公園是我國保存最為完整的祭壇園林,全園總面積273 hm2。為了從整體上營造靜謐、肅穆、莊重的祭祀氛圍,自明清時期壇域內便廣泛種植柏樹和松樹,樹木總數達5.6萬余株,其中側柏1.1萬株、檜柏2.0萬株、松樹0.4萬株[19]。從表3可知,天壇公園8類喬木樹種種植密度為柏樹>松樹>銀杏>楊樹>柳樹>榆科>白蠟>桑科。
北京市園林綠化科學研究院總面積14.16 hm2,設有城市綠地生態系統科學觀測研究站,包含6種典型植物配置群落。8類喬木樹種中銀杏的種植密度最大,為9.82株·hm-2;其次是松樹,為9.75株·hm-2;榆科樹木的種植密度最小,為0.14株·hm-2(表3)。
2.3 不同樹木種植密度與最大日花粉濃度的回歸分析
根據8類樹木最大日花粉濃度與種植密度的回歸方程(表4),當柏科、榆科、楊屬、柳屬、白蠟屬、銀杏科、松科和桑科樹木的種植密度分別超過8.28、15.35、7.00、2.63、0.86、9.77、41.00、0.28株·hm-2時,各類樹木的最大日花粉濃度就可能超過90粒·m-3,達到高污染風險等級;當柏科、榆科、楊屬、柳屬、白蠟屬、銀杏科、松科和桑科樹木的種植密度分別超過143.08、256.79、118.64、44.82、14.40、172.21、706.09、4.73株·hm-2時,各類樹木的最大日花粉濃度就可能超過1500粒·m-3,達到極高污染風險等級。

表4 不同樹木最大日花粉濃度(Y)與種植密度(X)的線性回歸方程
北京地區榆科、柏科和楊屬樹木的花期重疊,盛花期均在3月15—25日,但新建綠地中很少有榆科樹木栽植,因而此階段的花粉污染風險評估只需考慮柏科和楊屬樹木,其花粉污染風險評估模型為:Y=4.99+10.46X1+12.63X2(X1=柏樹種植密度、X2=楊樹種植密度,P<0.05),當柏樹和楊樹的種植密度分別小于4.06株·hm-2和3.37株·hm-2,就能將3月15—25日期間的最大日花粉濃度控制在中低污染風險等級。
盛花期在3月25—31日的只有柳樹,其花粉污染風險評估模型為:Y=2.22+33.42X(X=柳樹種植密度,P<0.05)。
白蠟和銀杏的盛花期均在4月1—15日,其花粉污染風險評估模型為:Y=5.49+104.14X1+8.68X2(X1=白蠟種植密度、X2=銀杏種植密度,P<0.05),當白蠟和銀杏的種植密度分別小于0.41株·hm-2和4.87株·hm-2,就能將4月1—15日期間的最大日花粉濃度控制在中低污染風險等級。
松科和桑科樹木的花期重疊,盛花期均在4月15—30日,但新建綠地中很少有桑科樹木栽植,其花粉污染風險評估模型為:Y=3.08+2.12 X(X=松樹種植密度,P<0.05)。
3 討論
花粉污染程度與空氣中花粉種類和濃度密切相關,其主要影響因素是綠地的植被組成。不同樹種開花量不同、同一樹種不同植株開花量不同、同一植株不同年份開花量也不同。春季開花的風媒花樹木的花期較短,一般在7~10天左右,且要經歷始花期、盛花期和未花期,其中盛花期產生的花粉數量最多,對過敏人群的影響最大;其花粉粒較小,一般直徑在10~30 μm,一個花藥中的花粉量約有數千粒以上[20-22]。因此,要準確測算一株風媒花樹木所產生花粉的數量是難以實現的,但根據不同樹種的種植密度和空氣中最大花粉濃度,對各樹種在盛花期時單株可產生的最大花粉濃度進行估算是可行的。因此,利用本研究結果能夠僅根據新建綠地的樹種組成對其潛在花粉污染風險進行評估。
隨著北京城市綠化率的不斷提高,空氣中花粉濃度和種類研究很難排除研究區域外樹木花粉的影響。研究表明,雖然氣傳花粉的水平飛散距離很遠,但在距離開花植物50 m以外濃度會急劇下降[5]。本研究的3個采樣點中,頤和園和天壇公園面積均超過200 hm2,公園中心區域空氣中的花粉濃度受周邊綠地影響較小。因此,利用本研究結果進行花粉污染風險評估時,綠地面積在100 hm2以上才能有效避免評估結果受到周邊綠地的影響。
北京城市綠化建設所應用的喬木集中在少數常用樹種,10大綠化骨干喬木中側柏、圓柏、楊樹、柳樹、油松、銀杏和白蠟的栽植數量約占喬木總量的40%左右[23-25],說明花粉致敏樹種的種類和數量較多,分布較廣。為了最大程度地減少致敏花粉對市民工作和生活的影響,全面提升城市綠地服務群眾的能力和水平,城市綠化建設要堅持以人為本,把適地適樹、生態文明、安全保健等科學觀念融入樹種選擇和配置過程中[26];加強對綠地規劃設計方案的審核把關,強化源頭管控,在人員活動密集場所,如居民區、學校、醫院、廣場等,盡量減少白蠟、楊樹、柳樹和柏樹的栽植數量;適度增加松樹的使用量,滿足冬季對常綠樹種的需求;同時多使用蟲媒花喬木樹種,如糠椴、楸樹、文冠果、稠李、絲棉木和毛梾木等,不僅可以滿足人們春季踏青賞花的需求,也能為蜜蜂和天敵昆蟲提供食物,提高城市綠地的生物多樣性指數,從而增加城市生態系統的穩定性,促進城市林業健康發展。
4 結論
種植密度與最大日花粉濃度間的回歸系數可以反映樹木單株所產生花粉量的大小,北京地區8類風媒花喬木單株最大日花粉量的大小順序為:桑科>白蠟屬>柳屬>楊屬>柏科>銀杏科>榆科>松科。
不同樹木的盛花期不同,花粉污染風險評估應分不同階段進行,盛花期重疊的不同樹木對空氣中花粉濃度的影響具有加和效應。新建綠地中柏樹、楊樹、柳樹、白蠟、銀杏和松樹的種植密度 分 別 小 于4.06、3.37、2.63、0.41、4.87、41.00株·hm-2時,可以將該時段的最大日花粉濃度控制在中低污染風險等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