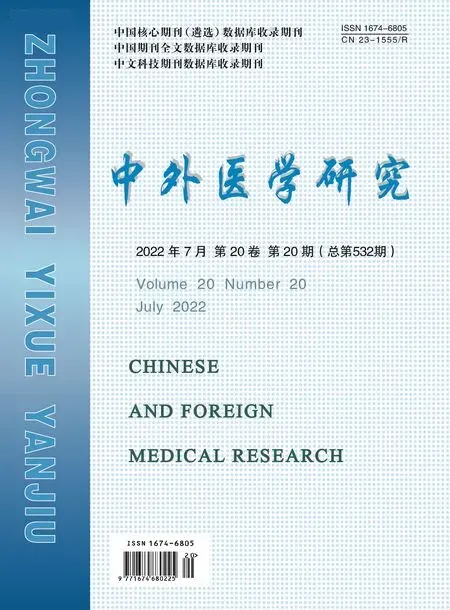個體化介入栓塞術對前交通動脈瘤破裂患者的影響
陸柳成
從臨床治療的情況分析,在常見的顱內動脈瘤破裂中以前交通動脈瘤為主,其占比大約為30%,屬于比較常見的動脈瘤類型。前交通動脈瘤的發生位置相對而言比較特殊,它位于患者兩側大腦前動脈之間。治療前交通動脈瘤的主要方案為患者實施外科手術夾閉及介入栓塞治療,但因動脈瘤結構復雜、位置特殊,在實際治療過程中很容易對患者的血管造成損傷,整體而言的手術治療風險系數較高,不利于患者群體的預后。隨著我國臨床醫學技術的持續發展與改進,目前已可以為前交通動脈瘤患者應用個體化介入栓塞治療,其治療成效與預后都比傳統手術治療方案更為理想[1-4]。鑒于此,選取橫州市人民醫院2018年6月-2021年6月收治的60例前交通動脈瘤破裂患者為本次研究對象,現將研究結果整理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本院2018年6月-2021年6月收治的60例前交通動脈瘤破裂患者為本次研究對象。納入標準:一般資料完備;術前均接受頭顱CT血管成像技術或數字減影血管造影技術診斷,診斷后確診為前交通動脈瘤破裂。排除標準:中途表示退出研究;罹患其他惡性腫瘤疾病;罹患心、腎、肝、腦等重大器官疾病。隨機將其分為對照組與觀察組,各30例。對照組男女比例為18∶12;年齡39~79歲,平均(52.03±5.12)歲。觀察組男女比例為20∶10;年齡為38~78歲,平均(51.49±5.14)歲。兩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有可比性。本次研究中所有患者家屬均簽署醫學研究同意書,且經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
1.2 方法
1.2.1 對照組 接受傳統開顱動脈瘤夾閉治療:患者以仰臥姿勢躺好,對其實施麻醉處理,麻醉生效后固定其頭架,按照相應的入路方法對患者進行開顱處理,利用高倍顯微鏡對患者的腦組織進行細心分離,將腦脊液進行稀釋,讓患者腦組織充分松弛,對動脈瘤及蛛網膜進行分離時,必須保護前交通復合體附近的各個穿支狀態下的血管,分離完成后,要選擇相應大小的動脈瘤夾,逐漸夾閉前交通動脈瘤,再以罌粟堿及生理鹽水對瘤動脈進行浸泡。
1.2.2 觀察組 實施多學科診療模式(multi disciplinary team,MDT)會診討論,為患者制定個體化的治療方案,個體化介入栓塞術治療:患者同樣取仰臥位,對患者實施麻醉處理后對其右股動脈進行導管鞘放置,實施全身性肝素化處理,之后觀察動脈瘤的形態及位置、結構大小等情況,用微導絲將微導管放入到瘤腔中鎖定微導管,再通過微導管將彈簧圈慢慢放入,以此法實現對瘤腔的填塞。而針對寬頸動脈瘤患者,則要采取血管內支架輔助的方法幫助彈簧圈進行栓塞。
本次研究中所入選的所有患者都需要接受抗血管痙攣治療,手術治療后第2天,需通過引流血性腦脊液來緩解患者所出現的頭痛及腦血管痙攣。手術治療后要保證患者在臨床上的補液量。
1.3 觀察指標及評價標準
(1)預后情況,對兩組術后1周的預后情況進行評估,①5分:患者身體情況恢復良好,雖出現了輕度缺陷但基本不對患者的日常生活構成影響;②4分:患者能夠獨立生活,但是患者必須在外界保護的狀態下從事生產勞動;③3分:患者的日常生活需要接受外界協助;④2分:對外界所給予的刺激患者只能反饋最小反應,睡眠/清醒周期之際能夠睜眼;⑤1分:患者已死亡。良好率=5分例數/總例數×100%。(2)認知功能:采用臨床上常用簡明精神狀態量表(MMSE)對兩組術后的認知功能進行評估,主要是對患者的定向能力(10分)、記憶力(3分)、注意力及計算能力(5分)、回憶能力(6分)及語言能力(6分)等進行測定,總分值為30分,其中評定27~30分正常;21~26分認知功能輕度障礙;10~20分中度認知障礙;低于10分重度認知功能障礙。本次研究中的所有評分環節均由兩名及以上的專業人員評定完成。(3)相關因子:比較兩組治療前后相關因子水平,測定人基質細胞衍生因子-1A(SDF-1A)、轉化生長因子-β(TGF-β)及白介素-10(IL-10)水平,本次研究所用的試劑盒購于上海裕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上海高創化學科技有限公司。(4)并發癥:比較兩組術后并發癥,包括肺部感染、尿路感染、尿崩癥及電解質紊亂。
1.4 統計學處理
本研究數據采用SPSS 21.0統計學軟件進行分析和處理,計量資料以(±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預后情況比較
觀察組臨床治療良好率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1。

表1 兩組預后情況比較
2.2 兩組并發癥比較
觀察組術后并發癥發生率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2。

表2 兩組并發癥比較[例(%)]
2.3 兩組認知功能比較
術后,觀察組記憶力、回憶能力評分均高于對照組(P<0.05);兩組定向能力、注意力及計算能力、語言能力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3。
表3 兩組認知功能比較[分,(±s)]

表3 兩組認知功能比較[分,(±s)]
組別 定向能力 記憶力 回憶能力 注意力及計算能力 語言能力對照組(n=30) 7.85±1.15 1.16±0.36 3.94±0.56 3.95±1.85 4.89±1.85觀察組(n=30) 8.11±1.14 2.95±0.56 4.89±0.36 4.32±1.94 5.23±1.45 t值 0.879 14.727 7.816 0.756 0.792 P值 0.383 0.000 0.000 0.453 0.431
2.4 兩組相關因子比較
術后,兩組SDF-1A、TGF-β及IL-10水平均下降,觀察組SDF-1A、TGF-β及IL-10水平均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4。
表4 兩組相關因子比較[pg/ml,(±s)]

表4 兩組相關因子比較[pg/ml,(±s)]
組別 SDF-1A TGF-βIL-10治療前 治療后 治療前 治療后 治療前 治療后對照組(n=30) 498.15±35.26 326.12±29.61 65.98±12.59 44.56±9.55 652.98±32.59 345.16±27.55觀察組(n=30) 500.12±29.36 241.23±21.31 66.54±10.21 23.59±7.45 646.54±30.21 213.09±21.35 t值 0.235 12.745 0.189 9.483 0.794 20.754 P值 0.815 0.000 0.851 0.000 0.431 0.000
3 討論
目前,針對前交通動脈瘤破裂患者經治療后所出現的認知功能障礙是海內外學術的熱點,與國內相比,國外針對血管性認知功能障礙進行了多項研究,對其發病機制、誘發因素、臨床診斷標準等都有過硬的學術觀點,從目前大量的研究數據分析,不管是傳統的夾閉治療還是個體化的介入栓塞治療,均有可能導致前交通動脈瘤破裂患者出現神經及心理層面的改變,當然也有學者的研究結果提示手術對前交通動脈瘤破裂患者的認知功能并不構成絕對影響,患者可能在手術治療前就已經存在認知功能障礙了[5-8]。
醫學研究發現,動脈瘤主要臨床表現在動脈壁的局限性或彌漫性膨出或擴張上,反映在患者中則為體表觸及搏動性的腫塊。人體動脈的任何部位都會有可能出現動脈瘤,而最為常見的位置則是人體的主動脈、頸動脈及肢體主干動脈上,且多數患者都為年齡超過50歲的中老年人,他們中又有很多人在平時就有動脈粥樣硬化的表現,除此之外,常見的發病因素還有感染、損傷及免疫等因素。目前臨床上公認的治療方式為介入治療與開顱手術夾閉,但是不管是哪種治療方式都被認為有一定的概率會影響到患者的認知功能,而一旦出現認知功能障礙,患者的日常生活、工作等都會因此受到嚴重干擾,只是治療方式的不同將導致患者在術后出現不同程度的認知功能障礙。從臨床操作的角度來說,前交通動脈瘤的血管內栓塞治療流程的獨特性主要有以下幾點:(1)從應用情況分析,微導管塑形得越好越是能順利進入到患者的動脈瘤中,塑形好的微導管才能在栓塞過程中保持理想的穩定性。因此在進微導管的頭端時,盡量不要用微導絲將微導管頭端直接帶入到患者的瘤腔內,而是應該讓微導管頭端被自然地推入到瘤腔內,這樣一來即便在栓塞過程中,微導管被彈出了,后續再次進入微導管也能變得更加容易;(2)關于微導管的塑形問題,一般情況下是要根據患者動脈瘤的空間立體結構來進行塑形,比如如果患者的瘤頂指向朝下、瘤體與A1段走形趨于一致,則不需要格外對微導管進行塑形,或者可以直接塑成角度較小的小彎;(3)選擇彈簧圈也有一定的規律,比如第一枚的彈簧圈大小不能超過患者動脈瘤體積的二分之一,特別是針對形態不規則的動脈瘤,則應該將彈簧圈的長度設計的短些;(4)針對兩側大腦前A1段發育正常的患者,則可以為患者實施雙側股動脈置鞘,并在患者的側頸內動脈中預留下5F造影管,這樣可以更好地在手術治療過程中反映出大腦前動脈與前交通動脈的情況[9-10]。
而在本次研究中,對照組接受的是經典術式,即傳統開顱動脈瘤夾閉治療。此術是在完全直視的狀態下進行的,對動脈瘤實施了夾閉處理。根據相關研究數據證實,傳統的手術治療具有較多的弊端,比如手術治療所耗時間相對更久、術后可能誘發更多的并發癥等,同時還有可能會降低患者對手術治療的耐受性[11-12]。本次研究結果提示,觀察組臨床治療良好率高于對照組(P<0.05);觀察組術后并發癥發生率低于對照組(P<0.05);術后,觀察組記憶力、回憶能力評分均高于對照組(P<0.05);術后,觀察組SDF-1A、TGF-β及IL-10水平均低于對照組(P<0.05)。這說明個體化介入栓塞術治療不僅僅能夠控制對患者腦組織的損傷,同時還可以減少術后并發癥,避免患者出現嚴重的認知功能障礙問題。
綜上所述,與傳統開顱動脈瘤夾閉治療相比,個體化介入栓塞治療不但可以取得較好的預后,更不易導致患者在術后出現認知功能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