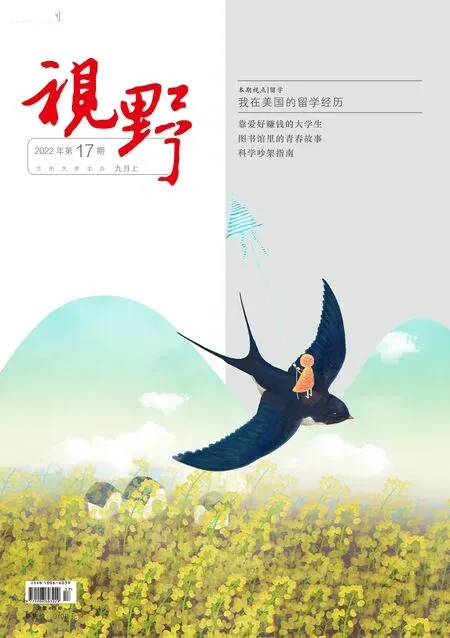圖書館里的青春故事
/文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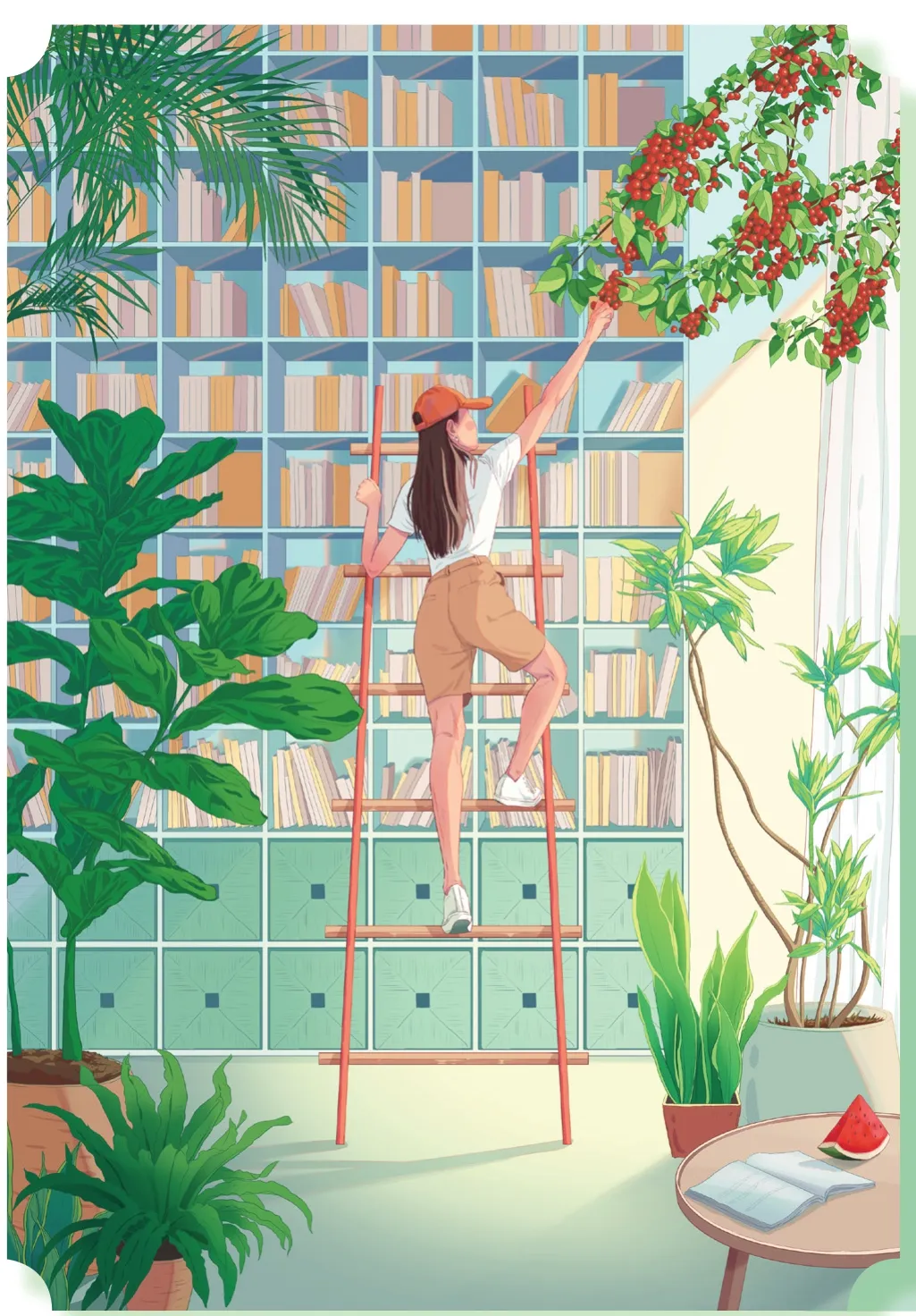
有關圖書館,有關個人,也算是一段悲歡史,該從何處說起呢——這樣的開頭,大有“不道別來愁幾許,相逢更忍從頭訴”的意味,但其實當然是恩多于怨,樂多于愁。
媽媽還記得我第一次去深圳市立圖書館時驚訝萬分的樣子。
那時已舉家南遷——從湖南移民至深圳——她要找新的工作需要參加職稱考試,因此每個周末都要去圖書館復習。十二歲的我跟她一起去了那里才知道:以前去過的中學圖書館是何等簡陋。
阿根廷最著名的圖書管理員博爾赫斯說過的最著名的話,無關鏡子、迷宮和交叉小徑的花園,而是這一句:“如果有天堂,大概就是圖書館的模樣。”誠如是言,深圳市圖書館無疑是少年時代的我見過的真正的“天堂”。
初到大都會的我忍不住給留在湖南小城的舊日好友寫信炫耀:這里不光有無數版本的《紅樓夢》,還有《紅樓夢魘》和《紅樓夢補》!過了整整一個月后,好友才淡淡地回信說:那你就替我們多看些書吧。
這才意識到可能傷害了舊友感情的遲鈍的我,已經幸或不幸地在圖書館里發現言情專架,從此棄紅樓于不顧,從岑凱倫、瓊瑤一氣看到亦舒、梁鳳儀乃至于著名集體寫作團伙“雪米莉”。直到大半個暑假過去,熟諳所有港臺言情套路才罷手。緊接著,又發現了金庸、古龍、蘇童、陳丹燕,明清小說,《青鳥》和《騎鵝旅行記》,等等。
高雅和濫俗在同一個圖書館里和光同塵。也就是說,安然共享同一個“天堂”。
剛轉學去深圳的我時常逃學。理由很簡單,就是迷路。
那條下車后穿過私立醫院去學校的小路走過若干次了,但也許是因為岔路太多,還是很容易迷失——也有可能自己潛意識里故意的——等終歸正途時,往往已經遲到,而遲到就勢必會被罰站。每當此時,我就果斷地決定逃學——反正上課也沒有什么意思。
也怨不得老師總罰我站。那年我剛上初二,正是慘綠少年的年紀。覺得沒意思就想逃,可是逃到哪里去呢?深圳這么大這么冷淡,我并不知道。
終于有一次,班主任忍不住給我媽媽打了電話。媽媽掛斷后便直奔市圖書館,果然在文學閱覽室里把我抓了個正著:無處可去的我,站在書架前消磨光陰,和此前的大多數時間一樣。
那天媽媽的表現著實古怪。在深圳十月依然灼人的正午驕陽下,領著我往學校一路疾走,紋絲不笑,直嚇得我心膽俱裂。到學校已過飯點,她便在外面的小飯館要了兩份盒飯,吃飯全程同樣板著臉一言不發。吃完差不多已到上課時間,她才說:“你快去上課。不許再逃。”
我灰溜溜地走了,一下午都在忐忑,不知回家后會受到怎樣可怕的懲罰——然而,那天晚上并沒有。此后很多天,都沒有。
過了好幾年之后,媽媽才告訴我,其實她那天一直在拼命忍著笑——一個逃學都逃往圖書館的小孩,能壞到哪里去?可又不能笑。一笑,就沒法教了,萬一以后再逃學怎么辦?
另一個關于圖書館的記憶,是常在圖書館里遇到騷擾者。
十三歲以前,大概這輩子能遇到的流氓,我差不多都碰上過了。在圖書館的開架閱覽室里看書,脖頸處偶爾感到異樣灼熱——猛一回頭,總能看到一張慌亂潮紅的人臉,便如驚鹿般逃開,但還是舍不得放下手中的書。倘若來者再反復逼近,只得放下書快速逃離。有一次受驚嚇太遽,在這座尚且陌生的海濱城市的大街上發足狂奔,猶如奮力逃離身為一個少女的危險宿命。
而記憶中狂奔不已的畫面里,大街上的夕陽總是慘淡灰黃,公交車站則像永遠也抵達不了的、足以自保的成年時光。
過了那段危險期,日后再在圖書館遇到搭訕者,早已練就金剛不壞之身。就讀研究生時期,有一次在閱覽室自習,不知為何總感覺對面有兩支小火炬灼熱地投向我。終于,一張紙條“啪”地按在書上。我眼皮都不抬,當即收拾東西起身。還沒走過長廊,空蕩蕩的樓道里腳步聲越來越近:“同學!”
我回頭看那人,他比我想象中更從容:“同學,可不可以要你的電話號碼?”
彼時我早非驚惶如雀的十三歲女孩,正色道:“同學,你不覺得在圖書館這樣影響別人學習不好嗎?”
他似乎吃了一驚。
過了幾年,某個冬夜又在國家圖書館遭遇搭訕者,已經不再那么可笑地大義凜然。搭訕者同樣是看我離開閱覽室,一路追出,在萬家燈火次第亮起的中關村大街上大喊:“你讀幾年級了?”
我想了想,還是平靜地回頭:“已經工作了。”
那個中年男人“噢”了一聲,聽不出失望還是別的:“你看上去很年輕。”
我忍住了沒說“謝謝”。
問話熟極而流,也不知道重復了幾百上千次:“請問,我有這個榮幸可以認識你嗎?”
“并沒有。”我同樣禮貌地回答。
也許是長大后漸漸就理解了,在圖書館搭訕成年女子的人和騷擾者不同,多數還是耽于幻想的多情種子。這樣一想,讓我多少原諒了這些搭訕者。后來偶然看到門羅的《忘情》,書中閱覽室的讀者愛上圖書管理員的套路,竟和我記憶中的幾幕如出一轍——
但就在她的圖書館辦公桌上,差不多幾周前一個周六的晚上,最后一位讀者離開后,她在鎖門關燈之際發現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我去海外之前就訂婚了。沒有寫名字,無論他的還是她的。還有她的照片,半邊壓在吸墨臺下。
那天晚上他就在圖書館。正是她最忙的時候。她時不時得起身幫讀者找書,整理報紙,忙著給圖書上架。他就在這兒,跟她共處一室,看著她,還悄悄留言,自始至終卻不曾介紹自己。
更著名一點的案例,則是日本電影《情書》,那兩位同樣叫藤井樹的男孩和女孩。
習慣在圖書館里追逐女孩的男人們,在書與書的空當處茫然四顧,幻想顏如玉從天而降。是讀書給他們制造的幻覺,抑或被某種孤獨感驅使,能接近最大數量陌生女性的唯一可能,也就只有在這全然免費的“天堂”。
還有一些時候,不一定要自己去圖書館,也可以委托他人借書。
表妹家比我家到深圳要早好幾年,她家里繳了擇校費讓她進了市重點,據說該校有全市數一數二的校圖書館,比我插班的普通中學的圖書館規模大得多。我有次隨她混進去借了本港版《唐伯虎詩詞歌賦全集》,至今還可以將里面的詞倒背如流:
牡丹含露真珠顆,美人折向庭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強妾貌強?檀郎故相惱,須道花枝好。一向發嬌嗔,碎按花打人。
據說這首《菩薩蠻》是唐代無名氏所作,也不知道怎么竄人唐寅的集子。唯一記得的就是這本書差點遭遇不測。事發于某節語文課,我剛把書拿出來看不久,語文老師突然過來輕敲桌子,讓我去他辦公室幫他拿一本書。我趕緊把書藏在書桌抽屜里,起身就走。回來后發現整個班氣氛很異樣。下課后才知道,我剛起身離開教室,語文老師就把我抽屜里的書拖出來向全班展示:“你們看看人家在看什么書!豎版,還是繁體……”
那是一個說不清楚到底是稱職還是不稱職的老師。同學都叫他老鬼,他看上去很嚴厲,會罰遲到的女生在操場上跑五圈。當時學校不允許女生蓄長劉海兒,中考前夕他會拿自己的刮胡刀剃掉人家的長劉海兒(幾乎所有女生都為此露出難以忍受的表情)。他會在上課時把“干涸”念成“干固”,引得我這樣的二愣子學生忍不住舉手站起來說:老師你念錯字了——端的是書生意氣,揮斥方道。而老師到底是什么反應,我卻完全忘記了。
不過我一直沒忘記那個細節,他從我抽屜里拿出書向大家展示,又在我回來前迅速放回——雖然并沒有真的看到那一幕。就是這行為的出人意表,讓我猜想他也許并不像表面上那樣討厭我。不光因為是唐寅,是繁體字,是豎版。
也許更多的,只是人到中年的漸漸吃力,面對年少輕狂的學生不知所措。同時又對這無知無畏不由得不退避三舍,并感到某種悵惘。
人生忽如寄。當我開始懂得這點時,早已過去很多年,幾乎到了和那個老師差不多的年紀。一生再也沒有機會問這個被稱為老鬼的語文老師當年到底怎么想的——被一個十三歲的女孩指出自己念錯字,以及發現她上自己的課時卻在看繁體字的古籍。
這就是我和從圖書館里借來的書有關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