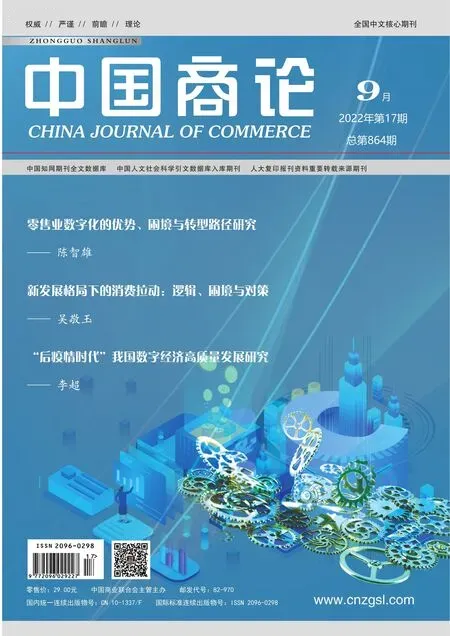江蘇智能制造產業集聚的影響機制與創新發展路徑研究
王暑雯 閭安琪 鄭熙 夏麗娟(通訊作者)
(蘇州科技大學商學院 江蘇蘇州 215000)
作為擁有世界上最完善工業體系的國家,我國始終走在世界制造業發展的前列。2010—2021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均位居世界首位,制造業水平穩步提升。近幾年,江蘇制造業的發展取得了諸多成效,并呈現智能化發展趨勢。與此同時,江蘇制造業企業及細分產業樣本凸顯了一定的集聚態勢和顯著的空間集聚特性。本文結合國內外學者的相關研究,對江蘇智能制造集聚的影響機制提出假說,通過引用相關指標及構建面板模型,對江蘇智能制造集聚程度的影響機制進行統計分析與實證分析,并對以上假說進行驗證,借助整合式創新的戰略引領、創新筑基和制度賦能三大實現路徑,構建江蘇智能制造發展路徑的總體模型,并闡述江蘇智能制造的具體發展路徑。
1 文獻回顧與述評
1.1 國內外智能制造的相關研究
智能制造是制造業實現轉型升級的重要方式。近年來,諸多國家先后頒布了相關政策,如美國的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日本的協同式機器人發展計劃、德國的“工業4.0”戰略規劃及我國的“中國制造2025”規劃等。對于智能制造概念的界定,韓江波(2017)認為,在產業價值鏈上下游企業間的技術環節中,智能制造起著十分關鍵的作用,銜接前后不同階段的核心業務。工信部發布的《智能制造發展規劃(2016—2020年)》指出,智能制造是在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與先進制造技術深度融合的基礎上,貫穿制造活動的各個環節,具有多種功能的新型生產方式。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智能制造是新一輪工業革命發展的重要指引與核心驅動力。傳統制造業的智能化轉型升級,既能推動我國裝備制造業打破在全球價值鏈中“低端鎖定”的困局,又會影響我國在世界上的制造業水平和地位。鐘志華等(2020)指出,智能制造為我國制造業的創新發展提供了歷史機遇,實現制造業的創新發展必須依靠智能制造。經濟的高速發展引發了社會環境的變化,我國制造業的現有水平已不能滿足消費結構升級的需要,因此亟需進行智能化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未來,通過不斷發揮智能制造對新一輪工業革命的引領和促進作用,我國制造業將逐步實現智能化、數字化與網絡化,并完成歷史性的變革。
1.2 關于智能制造集聚影響機制的相關研究
智能制造的空間集聚受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且各因素對智能制造集聚的影響程度與機制有所不同。學者許夕青、葛和平以長三角三省一市為研究對象,從不同角度對長三角智能制造集聚的影響機制進行理論分析,并初步提出了四個理論假設,運用相關數據和指標對長三角智能制造集聚的影響機制進行統計分析和實證分析,有效說明并驗證了提出的理論假設,進一步明晰了影響長三角智能制造發展的因素及各因素的作用機制,最后針對長三角智能制造的發展,總結并提出了相關建設性建議。智能制造的集聚在多重因素的影響下進一步加強。本文通過探析智能制造集聚的影響機制解決江蘇智能制造產業如何實現有效集聚與創新發展。
1.3 文獻總結及述評
“智能+”時代,制造業實現智能化是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和方法,智能制造是傳統制造業發展模式變革和轉型升級的必經之路。江蘇制造業的規模不斷擴大并具有強大的制造實力,為江蘇制造業的改革與創新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通過對相關文獻的分析與總結,可知江蘇制造業的產業集聚程度較高,但其發展仍有可升級空間。江蘇傳統制造業占比近70%,亟需通過智能化、數字化及網絡化改造實現向智能制造的轉型升級,引導并拉動江蘇制造業逐步邁進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的中高端。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從江蘇智能制造集聚的影響機制和創新發展路徑兩個方面進行研究與探討。
2 江蘇智能制造集聚的影響機制理論分析
本文以江蘇省5個城市為研究對象,從基礎性理論假說、拓展性理論研究兩個方面出發,探討江蘇智能制造集聚的影響機制。
2.1 基礎性理論假說
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到來,促使我國制造業開始向數字化方向發展,當前需以數字技術為基礎,對我國制造業進行數字化賦能,加快推動傳統制造業智能化的轉型升級。數字化賦能,即采用數字化技術、信息化數據處理技術和大智云移技術,制造企業智能化轉型是指運用工業機器人、工業物聯網、工業軟件三項技術實現產品智能化。智能制造的本質是制造,制造業企業通過數字化賦能實現技術、發展、生產方面的智能化轉型并逐步向智能制造過渡。由此可見,制造業與智能制造的關系即源頭到龍頭的關系,智能制造是制造業通過智能化轉型升級得到的,制造業的各項指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智能制造各方面的指標。對此,提出假說1:
假說1:智能制造的集聚程度與制造業的集聚程度具有正向相關性,制造業的集聚程度決定了智能制造的集聚程度。
2.2 拓展性理論研究
制造業是我國利用外資數量與規模較大的產業,德國、日本等國家為促進制造業的發展制定了制造業發展戰略,這一系列措施極大地影響了我國的國外貿易需求量。安娜(2021)通過數據對比分析得出,受新冠疫情影響,當前制造業利用外資占比有所下降,人員流動及復工復產均受到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外商對我國制造業投資的信心。作為制造業大國,外商投資能給我國制造業提供資金并帶來技術和市場,國外貿易需求量的減少會給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帶來壓力、減緩智能制造集聚,并影響我國制造業的國際地位和國內經濟發展。對此,提出假說2:
假說2:國外貿易需求量的增長能推動我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對智能制造的集聚具有拉動機制。
本質上說,智能制造的核心是新一代信息技術,依賴信息技術的推動,我國制造業企業的智能化趨勢更明顯。制造業的信息化,即運用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多種技術,在提升制造業企業綜合信息技術水平的基礎上,完善企業產品設計、開發、生產等環節。同時,提高企業在管理、創新、自動化技術方面的能力,降低各方面的能源消耗,實現企業在產品設計、開發、生產等環節中的信息化、智能化,全面促進我國制造業的數字化賦能改革,提高競爭力并擴大智能制造的集聚程度。對此,提出假說3:
假說3: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依賴新一代的信息技術,信息化水平的不斷提升能帶動智能制造產業的集聚。
推動智能制造的集聚需要設備、技術的支持,更關鍵的是人才支持。當前,制造業面臨嚴重的“人才危機”,部分地區制造業企業空有技術、設備而缺乏適合各個崗位的人才,導致智能制造產業出現就業缺口。對于智能制造產業,地區科技水平越發達,人口規模等級越高,對城市經濟水平的推動越大,越能吸引更多的人才聚集,越利于其發展。為此,江蘇需將現有的智能制造人才最大化集中,以滿足制造業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的需求,解決當前制造業的“人才危機”,促進制造業的智能化轉型升級,拉動智能制造的集聚。對此,提出假說4:
假說4:人口規模的等級對制造業的智能化轉型升級有顯著影響,智能制造的集聚需要高質量的人才供給。
3 江蘇智能制造集聚的影響機制統計分析
3.1 指標和數據說明
考慮到數據的完整性及可得性,本文選取南京、無錫、徐州、鹽城、連云港5個城市的數據,探析江蘇智能制造集聚的影響機制。研究樣本為江蘇省的5個城市及智能制造相關的7個產業。各細分產業的數據來源于2006—2020年《江蘇統計年鑒》及江蘇省5個城市的統計年鑒。文中2005—2019年細分產業就業人數以年就業人員平均數來計算。根據OECD制造業技術劃分標準,從中選擇了造紙及紙制品制造業、醫藥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橡膠和塑料制品制造業、金屬制品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7個制造業產業。
3.1.1 空間集聚程度指標
為衡量以上7個制造業產業的空間集聚程度,本文借助空間基尼系數(),其計算公式如下:


3.1.2 集聚效應測度指標
本文將成本費用利潤率作為指標,衡量智能制造業的集聚效益。其計算公式如下:

3.2 統計分析
3.2.1 空間集聚程度分析
通過調查統計江蘇省及下屬5個城市的相關數據并根據式(1)的計算方法,得出了江蘇省5個城市智能制造的7個細分產業2005—2019年的空間基尼系數,如表1所示。

表1 江蘇省5市智能制造相關細分產業的空間基尼系數
由表1可知,江蘇省智能制造相關細分產業之間的集聚程度在2010年前后產生了顯著的變化:(1)2005—2010年,江蘇省智能制造各細分產業之間集聚程度的差異不顯著。(2)2011—2019年,其差異十分顯著。其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的空間基尼系數在2011—2019年均保持在0.06以上,呈現出較高的集聚性;金屬制品制造業的空間基尼系數于2012年達到峰值,呈現出較高的集聚性,其余年份均與其他5個產業相同,呈現出較低的空間集聚性。
2005—2019年,江蘇省制造業細分產業空間基尼系數的變動趨勢如圖1所示。

圖1 江蘇省制造業細分產業空間集聚程度變動趨勢
由圖1可知,江蘇制造業各細分行業的空間基尼系數呈現出不同的變動趨勢: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的空間集聚性在2010年后出現了較大的上升波動并始終保持著較高的空間集聚程度;造紙及紙制品制造業、醫藥制造業、橡膠和塑料制品制造業以及通用設備制造業的空間集聚性總體上呈波動上升趨勢;金屬制品制造業的空間集聚性在2012年前后出現了較大的波動,總體上與專用設備制造業一樣呈現出波動下降的趨勢。
3.2.2 集聚效益分析
2016年江蘇省5市智能制造相關細分產業的成本費用利用率如表2所示。

表2 2016年江蘇省5市智能制造相關細分產業成本費用利潤率
由表2可知,江蘇智能制造相關細分產業中,醫藥制造業的成本費用利潤率最高,造紙及紙制品制造業的成本費用利潤率最低。其中,南京制造業各細分產業的成本費用利潤率基本處于較高水平,而鹽城則處于較低水平。在智能制造相關的7個細分產業中,鹽城、徐州、無錫、連云港、南京成本費用利潤率超過江蘇省整體平均水平的產業數量分別為1、5、5、4、6,說明總體上江蘇省智能制造的集聚效益較高。
4 江蘇智能制造集聚的影響機制實證分析
4.1 模型構建及變量解釋
基于上述研究假設和數據統計分析,根據數據橫向和縱向特征,構建了動態面板模型,并對江蘇省5個市的智能制造集聚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構建的面板模型如下:

面板模型的變量采用學者許夕青、葛和平使用的測量方式。
式(3)中:

外需依賴程度=江蘇省5個市各市的人均出口總值;
江蘇省第個城市的信息化水平=江蘇省5個市各市的人均電信業務總量;

其中:為常數項;、、、為帶估計的參數;ε為隨機誤差項。
4.2 數據統計與解釋
表3為面板模型中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數據來源于2006—2020年《江蘇統計年鑒》及2006—2020年江蘇省5市的統計年鑒,采用的數據范圍為2005—2019年江蘇省各市的相關統計數據。

表3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4.3 江蘇省智能制造集聚的影響機制實證分析
為研究各個主要變量與智能制造集聚程度之間,即INT分別和MIA、OMD、INF、CG四項之間的相關關系,本文借助皮爾遜分析方法及皮爾遜相關系數。
如表4所示,INT和MIA、OMD、INF、CG四項之間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959、0.911、0.497、-0.478,均呈現0.01水平的顯著性。說明智能制造的集聚程度與制造業集聚程度、外需依賴程度、信息化水平三者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與人口規模等級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表4 主要變量的相關性分析(Pearson相關分析)
由此可見,制造業集聚程度、外需依賴程度、信息化水平及人口規模均與江蘇省智能制造集聚程度存在顯著線性相關性,初步驗證了上文提出的假說。
基于上文的分析,為進一步探討四個假說中的變量與智能制造集聚程度之間的深入關系,對江蘇智能制造7個細分產業進行回歸分析,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制造業集聚水平僅對造紙及紙制品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醫藥制造業、橡膠和塑料制品制造業的集聚程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外需依賴程度對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的集聚程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起正向的拉動作用。信息化水平僅對醫藥制造業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有利于醫藥制造業的產業集聚。人口規模對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金屬制品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醫藥制造業的集聚程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對其他三個產業的影響不顯著。

表5 江蘇智能制造相關細分產業集聚程度影響因素回歸分析表
5 江蘇智能制造的創新發展路徑建議
制造業企業在實現向智能化轉型升級的過程中,應站在總體視角,進行系統化、整合式的思考與創新,即綜合考慮對自身發展產生影響的因素,從戰略、技術、制度等方面進行系統性、創新性的規劃,整合式創新的提出對制造業轉型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本文借助整合式創新三大實現路徑的理論框架,構建江蘇智能制造創新發展路徑的總體模型。根據圖2理論模型,江蘇智能制造的創新發展路徑闡述如下。

圖2 江蘇智能制造的創新發展路徑模型
5.1 整合式創新視角下江蘇智能制造的戰略路徑
5.1.1 推動產業聚集
產業集聚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制造業的發展狀況,因此產業分散的地區尤其是高新技術開發區,要科學制定規劃、培育相關龍頭企業、構建產業發展平臺,并借助其先進的科技資源,吸引、引導、帶動產業集聚,進而推動制造業產業聚集,促進制造業智能化轉型升級。
5.1.2 加大開放力度
新冠疫情影響下,制造業外資流入大大減少,而國外貿易需求量對于智能制造的集聚具有拉動作用,因此必須加大開放力度,帶動制造業生產性需求,同時把握國外對我國產品的需求,有效改善并優化產業結構,吸引外資、確保外資回流中國。
5.2 整合式創新視角下江蘇智能制造的創 新及制度路徑
5.2.1 加強信息化建設
在制造業智能化、數字化發展過程中,信息化水平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針對江蘇制造業信息化發展不均衡、信息化市場不健全等問題,各制造業企業應借助云計算、“互聯網+”等高新技術,不斷進行自我創新與改革,穩定發展自身信息化建設、開拓信息化市場、形成自身核心優勢、拉動信息化水平的不斷提升,進而推動江蘇制造業信息化水平的整體提升與發展。
5.2.2 優化人口結構
人口規模等級越高,所容納與吸引的人才就越多,對于發展其經濟與信息化水平等方面就更有利,因而智能制造的集聚程度就越高。江蘇制造業要想取得突破性發展,實現智能制造的順利轉型,就要把握好人才這個關鍵因素,通過制定相關的人口發展與改革制度,合理擴大人口規模,吸引并引進制造業相關領域人才,不斷優化人口結構,提高人口規模等級,為制造業發展提供長久且不竭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