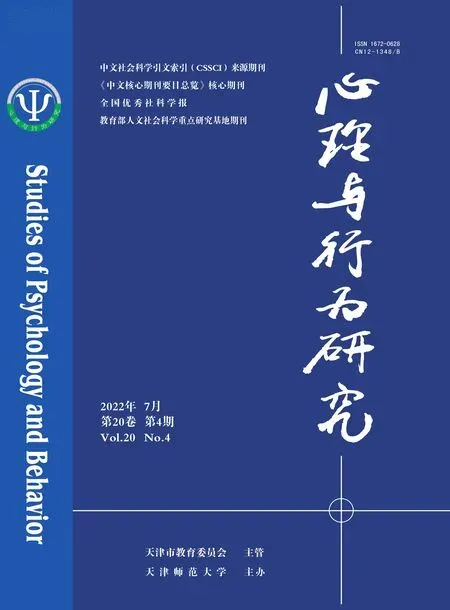高中生正念與學習倦怠:基于自我調節學習模型的視角*
靳 銘 曾練平 曾小葉 黃亞夫
(貴州師范大學心理學院,心理危機干預與矯治研究所,貴陽 550025)
1 引言
多項調查研究數據表明,在高考背景下高中生普遍存在較為嚴重的學習倦怠問題(陳維 等,2016; 吉彬彬 等, 2020)。教育部推出“雙減”政策,通過推進“減負提質”,提升學習效果,減少學習倦怠(周洪宇, 齊彥磊, 2022)。近年來,“終生學習”的理念逐漸被社會大眾所接納,而在青春期就出現學習倦怠情況,非常不利于個體長久保持學習動機并參與終生學習和發展。
學習倦怠最早由Pines 等人(1981)提出,指的是一種因學習壓力過重或缺乏學習興趣而產生的持續負性的心理狀態(連榕 等, 2005)。具體表現為:精力耗損和身體衰竭;喪失與學習有關活動的熱情、對學業持負面態度;學習成就感缺失等(吳艷 等, 2007)。學習倦怠不但影響學業成就,還會對個體的生理、心理、行為及人際交往層面帶來消極影響,嚴重的甚至可能導致自殺(Wang et al., 2015),因此學習倦怠是衡量學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標(何安明 等, 2019)。前人研究指出,正念可以減少學習倦怠(陶偉, 2017; Calvete et al., 2017),但以往缺乏正念影響學習倦怠的內部作用機制的探討。因此本研究基于自我調節學習模型,探討正念對高中生學習倦怠的影響及其內在作用機制,并引入未來時間洞察力和生命意義感兩個與時間觀念和幸福感相關的概念,為緩解高中生學習倦怠、促進高中生身心健康發展提供理論和實踐依據。
正念是一種關注當下的意識(Kabat-Zinn,2003),能夠更多保持正念的個體具有專注當下的能力,其類似于積極心理學中的性格優勢和長處(Park et al., 2013),即一種類特質。積極情緒的拓展-建構理論認為,體驗積極情緒拓寬了人們的瞬時思想,同時又有助于建立持久的個人資源,減少情緒耗竭,削弱學習倦怠感(Fredrickson, 2001)。而正念特質高的個體真實地感受世界,進而體會到更多的積極情緒。實證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正念訓練通過提升個體正念水平,增加個體的積極情緒體驗,有效減少倦怠感,并且這種正向影響在十個月后依舊顯著(Kinnunen et al., 2020)。學業情緒理論認為,積極的學業情緒可以減少個體的學習倦怠。實證研究證實,正念作為一種心理保護因子,能夠使學生保持積極良好的學業情緒,有效提升個體積極情感和生活滿意度,緩解倦怠(董妍, 俞國良, 2010; Calvete et al., 2017),對學習倦怠有直接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周虹, 2019)。鑒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設1:正念能負向預測高中生的學習倦怠。
正念對于學習倦怠的影響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通過其他因素而產生的間接效應。關于學習倦怠的內在影響機制,本研究認為未來時間洞察力和生命意義感是值得考慮的中介變量。
自我調節學習模型認為,自我調節學習是與外部調節學習相區別的一種學習形式,其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學習者對自己的學習有實際的控制,通過引導認知和動機過程實現學習目標(Boekaerts &Cascallar, 2006)。與外部調節學習容易導致的重復低效學習不同,自我調節學習會顯著減少學習倦怠,前人研究也支持了這一觀點(宋曉麗, 2009; 王立娜, 2012)。自我調節學習的成分可以分為認知和動機(Boekaerts, 1997),這樣更能完整闡述學習的過程機制,而認知和動機情感又是遞進的過程。正念是關注當下而不評判,將注意力放在對自己當下的覺知上,因此屬于元認知的范疇。未來時間洞察力是對未來時間的認知,屬于認知成分。生命意義感具有動機作用,屬于自我調節學習的動機成分。由此推測,未來時間洞察力和生命意義感可能在正念和學習倦怠之間起序列中介作用。
未來時間洞察力是一種對未來時間的認知和積極期望,與計劃能力有著密切的聯系,對于個體的發展有積極作用(黃希庭, 2004)。正念是對當下的意識和關注,與時間觀緊密聯系(Kabat-Zinn, 1990),因此,正念和未來時間洞察力分別代表著現在和未來的積極的時間觀念(Kabat-Zinn,2003),屬于積極時間觀念的兩個維度。根據最佳平衡時間觀念理論,個體對于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間觀存在一個三者的最佳平衡點,處于最佳平衡點的個體,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水平較高,倦怠水平較低(Zimbardo & Boyd, 1999)。正念特質高的個體具有更平衡的當下的時間觀念,具有這一當下觀念的個體,有接納過去、積極追求未來目標的特點。較少沉湎于對過去的后悔或對未來不切實際的幻想中,可以靈活轉換以適應生活(Zimbardo & Boyd, 1999),并且認為未來是可變的、有希望的而非“宿命論的”,對過去、現在、未來的觀念達到了一種穩態平衡(Zimbardo &Boyd, 2008)。因此當下積極的時間觀可以預測未來積極的時間觀念(R?nnlund et al., 2019)。據此推測,正念可以正向預測未來時間洞察力。這一推論也得到了前人研究的支持,葛靜靜(2020)的研究表明正念可以直接影響時間洞察力,而Kabat-Zinn(2003)也指出正念可以顯著正向預測未來時間洞察力。此外,根據期望-價值理論,個體的行為動機由結果期待和價值評估兩個因素決定(Wigfield &Eccles, 2000)。未來時間洞察力能促使個體認識到當前行為的有效性及未來結果,因而能更好地啟動當前學習行為,降低學習倦怠感(龐雪 等, 2014)。實證研究也表明,未來時間洞察力與學習倦怠呈現顯著負相關(王佳名 等, 2014)。文敏等人(2014)的研究發現,避免失敗的動機會通過未來時間洞察力減緩個體的學習倦怠。Mather 和Carstensen(2005)指出,未來時間洞察力使個體對當前時間和未來時間進行對比,進而產生一種差異,這種差異能為個體提供動力來源,從而降低學習倦怠。正念可能會通過未來時間洞察力降低學習倦怠,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2:未來時間洞察力在正念與學習倦怠之間起中介作用。
生命意義感是個體屬于自己的、具有實際價值的主觀體驗和感受(李偉, 陶沙, 2003) 。生命意義感從何而來?自我決定理論認為當個體在生活中融入真實的自我,生活的意義就會顯現出來(Weinstein et al., 2012),即以自我一致的方式參與生活的過程會為個體提供生命意義感。正念具有不評判和保持開放的特點,這有利于個體將真實的感受整合到自我中(Hodgins & Knee, 2002)。因此,正念水平高的個體根據真實自我的感受主導自己的行為,在行為和價值觀上保持一致性,會增加個體的生命意義感。Chu 和Mak(2020)通過元分析發現,正念可以顯著正向預測生命意義感,并且可以用自我意識的增強解釋這一過程(Allan et al., 2015)。此外,根據生命意義感的動機定義,尋求意義是人類的基本動機(維克多·弗蘭克, 1991)。人類有理解自己及其周圍世界的強烈愿望,會受生命意義感動機的驅使進行學習和認知探索活動(Heine et al., 2006)。因此,生命意義感能提高個體行為動機,增加工作投入,并使個體享受這一過程的快樂,減少壓力與倦怠感(Hooker et al., 2020)。實證研究也證實,學習倦怠程度的高低受個體生命意義感水平高低的影響(梁家鳳,李炳全, 2017),中學生的生命意義感與學習動機呈顯著正相關(覃麗 等, 2013),而學習動機對學習倦怠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徐興鴻, 2012)。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3:生命意義感在正念與學習倦怠之間起中介作用。
雖然同屬于中介變量,但是未來時間洞察力和生命意義感二者存在關聯。首先,高中生開始思考未來,更多探索生命的意義與未來發展方向。根據社會情緒選擇理論,隨著知覺到的未來時間不同,個體當前的目標也會隨之發生變化(Mather & Carstensen, 2005),當知覺到未來時間非常有限時,個體會優先選擇以情緒調節為目標;反之,則偏向選擇以獲取知識為目標。在未來時間洞察力高的情況下,個體知覺到未來時間充足,更多地關注未來導向目標,即以獲取知識為目標去探索世界(敖玲敏 等, 2011),尋求生命的意義。因此未來時間洞察力較強的個體可能擁有更強的生命意義感,積極地通過學習、工作來擴展對世界的認知。其次,認知-情感-行為意向-行為四者是一個遞進的作用機制。未來時間洞察力作為對未來時間的認知(黃希庭 等, 2005),讓個體有掌控感和效能感,能夠提升生命意義感這一動機變量。實證研究也證實,未來時間洞察力與生命意義感之間呈顯著正相關(姬云兵, 2013),未來時間洞察力可以顯著正向預測生命意義感(郝宇欣, 2015)。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4:未來時間洞察力和生命意義感在正念和學習倦怠間起鏈式中介作用,假設模型如圖1 所示。

圖1 假設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在貴州省遵義市選擇一所高中,采取整群抽樣的方法進行問卷調查,為控制同源偏差分兩次收集數據,第一次收取正念、生命意義感、未來時間洞察力三個變量的問卷,回收有效問卷1080 份,第二次回收學習倦怠問卷,共收到有效問卷1067 份,匹配姓名后得到有效問卷863 份,問卷回收有效率約為80.88%。其中男生408人(47.28%),女生455人(52.72%)。被試年齡范圍 為14~18 歲(M=15.89 歲,SD=0.87 歲)。獨生子女226人(26.19%),非獨生子女637人(73.81%)。來自單親家庭的樣本共133人(15.41%)。
2.2 研究工具
2.2.1 正念
采用正念注意覺知量表(Brown & Ryan, 2003),該量表共15個題項,單維量表,采用李克特5 點計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為方便理解,將結果反向計分。分數越高的個體在日常生活中對當下的覺知和注意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9。
2.2.2 生命意義感
采用生命意義感量表(MLQ)中文修訂版(王鑫強, 2013),共10個題項,采用李克特7 點計分(1=“完全不符合”,7=“完全符合”)。量表分為擁有意義感和尋求意義感兩個分問卷。分數越高代表個體的生命意義感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73。
2.2.3 未來時間洞察力
采用修訂過的中文版津巴多時間洞察力問卷(王晨, 2016),該量表為單維量表,共5個題項(如“我想完成某件事時,會設立目標并考慮達到目標的具體途徑”),采用李克特5 點計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分數越高代表未來時間洞察力越強。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3。為進一步澄清量表的信度,計算CITC 指數(corrected-item total correlation)作為Cronbach’s α 系數信度檢驗的補充(曾五一,黃炳藝, 2005),結果顯示該量表所有題項CITC值均大于0.5,說明在本研究中量表可信度較高。
2.2.4 學習倦怠
采用青少年學習倦怠量表(吳艷 等, 2007),該量表包括三個維度,分別是身心耗竭(如“最近感到心里很空,不知道該干什么”)、學業疏離(如“我覺得自己反正不懂,學不學都無所謂”)和低成就感(如“當學習時,我忘掉了周圍的一切”),一共 16個題項。采取5 級評分(1=“很不符合”,5=“非常符合”),其中部分條目反向計分,16個題項得分之和為量表總分,得分越高說明學習倦怠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78。
3 結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為了控制同源偏差,在研究程序設計方面采用多時點配對的紙質問卷收集方式分兩次收集數據,第一次收取正念、生命意義感、未來時間洞察力三個變量的問卷,間隔一個月后回收學習倦怠問卷。數據分析方面,用Harman 單因素法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結果發現,特征值大于1 的因子共有10個,且第一個因子解釋的變異量為19.2%,小于40%的臨界標準,結果表明本研究數據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和相關分析
本研究中,正念與生命意義感和未來時間洞察力呈顯著正相關,與學習倦怠呈顯著負相關。生命意義感與未來時間洞察力呈顯著正相關,與學習倦怠呈顯著負相關。未來時間洞察力與學習倦怠成顯著負相關。各變量的相關矩陣如表1所示。

表1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和相關分析結果
3.3 正念對學習倦怠的影響
使用Hayes(2013)提供的SPSS 插件PROCESS的Model 6,在控制性別、年齡、成績的條件下以正念為自變量,以學習倦怠為因變量,以未來時間洞察力和生命意義感為鏈式中介變量,分析未來時間洞察力和生命意義感的中介關系。各變量間的回歸分析如表2 所示。回歸分析結果表明,正念對于學習倦怠的負向預測顯著(β=-0.2 6,p<0.001),正念對于未來時間洞察力的正向預測作用顯著(β=0.06,p<0.001),正念對于生命意義感的正向預測作用顯著(β=0.15,p<0.01);未來時間洞察力可以顯著正向預測生命意義感(β=0.42,p<0.01),未來時間洞察力顯著負向預測學習倦怠(β=-0.41,p<0.001);生命意義感顯著負向預測學習倦怠(β=-0.09,p<0.01)。

表2 變量間的回歸分析
通過中介效應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未來時間洞察力和生命意義感在正念與學習倦怠之間起中介作用。具體來說,中介效應由三條路徑組成:通過正念→未來時間洞察力→學習倦怠的途徑產生的間接效應1(-0.023),通過正念→未來時間洞察力→生命意義感→學習倦怠的途徑產生的間接效應2(-0.002),通過正念→生命意義感→學習倦怠的途徑產生的間接效應3(-0.013),表3的數據顯示,三個間接效應依次占總間接效應的60.53%、5.26% 和34.21%,相對中介效應分別為9.27%、0.89%和4.51%。Bootstrap 95%置信區間均不包含0 值,表明三個間接效應均達到顯著水平。表明未來時間洞察力與生命意義感在正念對學習倦怠的負向效應中的鏈式中介作用成立。這一結果支持了假設4。

表3 未來時間洞察力與生命意義感在正念對學習倦怠影響中的中介效應分析
4 討論
前人研究大多聚焦于幸福感和核心自我評價等情緒情感變量在正念和學習倦怠間的中介作用(朱萌君, 常保瑞, 2021; Currie, 2020),鮮少從認知和動機的角度進行研究。本研究基于自我調節學習模型的視角,將正念對于學習倦怠的作用拓展到認知和動機層面。結果表明正念不但可以直接預測學習倦怠,還能通過未來時間洞察力和生命意義感的橋梁作用顯著負向預測學習倦怠。根據積極情緒的拓展-建構理論(Fredrickson, 2001),正念能夠增加個體的積極情緒體驗,從而有效減少倦怠感(Kinnunen et al., 2020)。同時,消極的學業情緒極易引發學習倦怠(董妍, 俞國良, 2010),而正念作為學業情緒有效的調節策略,可以減少負性學業情緒,增強自豪、放松、滿足和希望等正性學習情緒,減少學習倦怠。在教學以及課堂設計中,一線教師可以將正念融入課堂教學,以課前正念訓練等方式幫助學生們放松下來,保持積極的學習情緒,進而減少高中生學習倦怠情況的出現。本研究拓展了正念的再感知模型,該模型認為正念通過意識、注意和態度(Carmody et al.,2009)三個結構發揮作用,而本研究發現,正念也通過未來時間洞察力和生命意義感這兩個認知和動力特質發揮作用,為正念的理論模型研究提供新視角。
本研究進一步發現,正念能夠通過未來時間洞察力和生命意義感的鏈式中介作用預測學習倦怠。前人探討了未來時間洞察力對于學習倦怠的直接影響(張鋒 等, 2016),而鮮少探討個體通過生命意義感的目標指向的動機作用進而對學習過程產生影響。本研究基于自我調節學習模型,將正念、未來時間洞察力、生命意義感和學習倦怠這四個變量同時納入理論模型中,將時間心理學的概念引入了自我調節學習策略理論(Zimmerman &Martinez-Pons, 1988)。研究結果證實,自我調節學習模型的認知和動機兩個結構可能是按認知-動機的遞進作用機制發揮作用。這一發現有助于啟發正念的理論模型,對于研究正念在復雜認知過程中的作用機制提供思考。
本研究通過鏈式中介模型探討正念對學習倦怠的影響,揭示了生命意義感和未來時間洞察力的中介作用。研究結果回答了正念是如何影響青少年學習倦怠的。結果豐富了正念的再感知模型對于學習機制的理論基礎。同時對于自我調節學習策略理論(Zimmerman & Martinez-Pons, 1988)進行了一些擴展,啟示未來的研究可以考慮自我調節學習模型成分的遞進順序。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的數據都來自被試的主觀報告,可能存在誤差(如記憶偏差、社會稱許等),未來研究可以考慮通過多種來源(如個人、同伴、父母、教師等)收集數據,以更客觀地測量相關變量。其次,本研究采用的是基于問卷法的橫斷設計,雖然對假設模型的分析與討論是建立在已有研究基礎之上的,但是結果仍不能確定各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更無法確定變量之間的長期效應,未來的研究可以考慮采用縱向設計。
5 結論
正念不僅能夠負向預測高中生學習倦怠,也能通過未來時間洞察力和生命意義感獨立的中介作用,以及未來時間洞察力和生命意義感的鏈式中介作用間接預測學習倦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