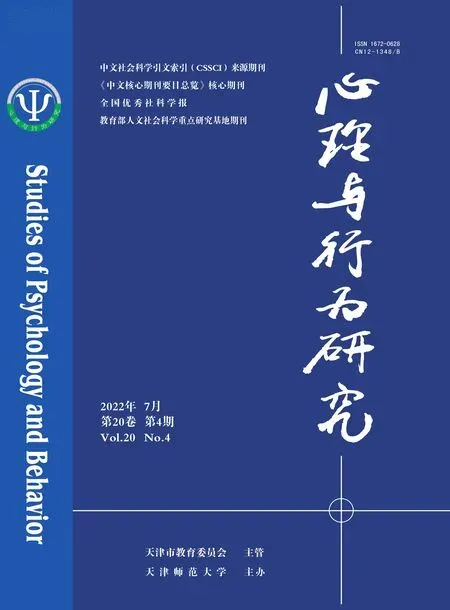感恩與聽障學生親社會行為的關系:有調節的中介模型*
田惠東 張玉紅,2 王 魁 孫昊翔 劉鴻鈺
(1 新疆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烏魯木齊 830054) (2 新疆教師教育研究中心,烏魯木齊 830054)(3 額敏縣第一中學,塔城地區 834600)
1 引言
親社會行為泛指一切符合社會期望,對他人、群體及社會有益的行為(Eisenberg et al.,1998),它反映了個體的積極傾向和健康特質,符合人們對成熟社會化個體的角色期望,是個體良好適應的重要標志(杜秀蓮, 高靜, 2019)。研究表明,表現出更多親社會行為的青少年會感受到更多的生活意義感、效能感(van Tongeren et al.,2016),建立更和諧的人際關系,擁有更高的自尊水平和心理健康水平(Laible et al., 2004)。聽障學生不僅要適應各種壓力和困擾,還要應對聽力和語言障礙給其認知與交流所帶來的挑戰,這給他們的社會適應帶來了極大挑戰(姜琨 等, 2018),也使其親社會行為的發展受限(魯玲, 2012)。培養聽障學生親社會行為,使其采用親社會的方式處理自身的內部沖突,同時協調好自我與他人及社會之間的關系,這也成為促進聽障人群自身適應社會、增強其自身主動融入社會的意識和能力的必然要求。
個體行為受認知和情感的影響,親社會行為更需要較強的認知和情感參與。積極情緒的拓展-建構理論(broaden-and-build theory)認為積極情緒可以拓展人們暫時性的認知與思維,建構持久性的心理資源,使其做出利他決策,即利用心理資源解決問題,建構人際關系(Fredrickson,2004)。感恩作為一種具有社會道德價值的積極情感,是個體感受到積極結果時,在理解他人善行并做出回應的過程中保持感激態度的心理傾向(Emmons & Shelton, 2002)。McCullough 等人(2008)認為感恩在激勵受惠者回報施惠者,并促進受惠者向除施惠者之外的他人慷慨解囊的同時,還會強化施惠者的助人行為。實證研究也表明感恩對親社會行為有重要作用(何安明 等,2014),一項為期4 年的縱向研究表明青少年的感恩增長可以預測親社會行為的增加(Bono et al.,2019)。然而,也有研究認為感恩與個體的虧欠感、責任感、利己動機等緊密相聯,如感恩可能基于虧欠感的償還義務,這種有償反饋不一定會引發親社會行為(Gray et al., 2001)。可見,有關感恩和親社會行為間的關系還需深入探討。
道德行為的社會認知模型提出親社會行為受道德自我圖式的激活與當下情景因素的共同影響(Aquino & Reed, 2002)。感恩作為與親社會行為相關的道德自我圖式(Yost-Dubrow & Dunham,2018),在解釋校園欺凌中的親社會行為時還需考慮幸福感這一情景因素的中介作用(García-Vázquez et al., 2020)。生活滿意度作為幸福感的重要組成部分(Alkozei et al., 2018),是否也可以在感恩與親社會行為的關系中起中介作用呢?一方面,生活滿意度高的個體會表現出更強的親社會意愿和行為,這可能是因為生活滿意度可以提高個體對善良人性以及他人善意的感知,從而產生親社會行為(Layous et al., 2017; Zhang & Zhao,2021)。另一方面,感恩的人更欣賞和享受積極的經歷(Baek & Lim, 2013),關注自己所獲得的或社會所給予自己的,更容易滿足現實生活(馬小紅,丁鳳琴, 2020),提升生活滿意度(田媛 等, 2017)。
盡管已有研究對感恩、生活滿意度及親社會行為兩兩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但鮮有研究關注這些關系模式在聽障群體中是否一致。聽障學生往往面臨溝通困難的問題,這對其情緒智力、認知能力和心理健康有所影響(Ummi Habibah,2018),進而造成隱喻理解、道德判斷等能力不足(李夢娜 等, 2020; 張志君 等, 2008),而這可能會影響他們認知感恩活動、形成感恩意識以及產生感恩行為。與此同時,聽障學生雖珍愛生命、熱愛生活,但又因聽力損傷而自我接納低,缺乏良好的人際關系甚至遭受歧視,他們的生活滿意度低于健聽學生(Rizkiana & Santoso, 2019)。那么,聽障學生在感恩與生活滿意度上的特殊性是否會使得這二者與親社會行為的關系模式異于健聽生?是促進還是無關系,亦或抑制?這有待實證研究予以探明。同時,為揭示其親社會行為的內在產生機制,本研究還將探討生活滿意度在感恩與親社會行為之間是否起中介作用。
此外,生活滿意度中介作用的性別差異也需進一步探討。一方面,有研究表明女生在感恩特質的強度上高于男生(丁鳳琴, 宋有明, 2017),也有研究認為男生比女生更懂得感恩(Kim, 2014);有研究認為男性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高于女性(鄧林園 等, 2016),但在其他研究中并未發現類似結果(You et al., 2018)。可見,感恩和生活滿意度是否存在性別差異以及具體差異表現如何仍需進一步考察。并且,以往研究多單獨考察感恩或生活滿意度的性別差異,較少探討二者關系中是否也存在性別差異,但這值得深入研究,因為有研究發現相比女生,高感恩的男生可以獲得更多的積極情感和社會利益(Froh et al., 2009)。相比聽障女生,聽障男生從感恩中可以獲得更多的社會支持,而社會支持可以提升他們的幸福感(王玉, 2015)。原因可能在于女生更容易表達和經歷感恩這一積極情緒,她們更易達到“情緒瓶頸”,因而幸福感的提升空間相對較小,而男生在表達感恩這一積極事件中可以獲得更多的情緒利益(喻承甫 等, 2010)。另一方面,性別圖式理論(gender schema theory)認為個體會按照性別角色的社會期望表現自我,女性會以善良、照顧他人的性別角色期待調整自己的行為模式,而男生則以獨立、自主、勇敢的形象塑造自己,在考慮問題時更加理性(Starr & Zurbriggen, 2017)。相比男性而言,社會文化期望女性可以具有更多的親社會特點,如助人、合作、有同情心等(Shigetomi et al.,1981),她們在需要表現親社會行為的情境中更易產生憐憫。女性在社會文化期待下會接受更多的親社會行為強化(Power & Parke, 1986)。即相比感性的女生在感恩影響下更易表現出親社會行為,理性、獨立的男生則需要更多的積極情緒(如生活滿意度)來啟動、激活親社會行為。因此,本研究還將檢驗性別對“感恩→生活滿意度→親社會行為”這一中介模型前半路徑的調節作用,以及該中介機制的性別差異。
基于此,本研究通過建構一個有調節的中介模型來考察感恩與聽障學生親社會行為的關系,以及生活滿意度的中介作用與性別的調節作用機制。假設模型如圖1 所示。

圖1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采取方便取樣,從新疆、廣東、江蘇、重慶等地的特殊教育學校和高等院校選取聽障學生,共發放問卷446 份,剔除無效問卷后得到有效問卷392 份,有效回收率87.89%。其中,男生193人,女生199人;初中生136人(M=16.12 歲,S D=1.6 0 歲),高 中 生1 2 9人(M=1 8.4 4 歲,S D=1.6 5 歲),大 學 生1 2 7人(M=2 1.2 0 歲,SD=1.84 歲);聽障等級一級(聽力受損大于90 dB)175人,二級(聽力受損大于70 dB 小于等于90 dB)134人,三級(聽力受損大于60 dB 小于等于70 dB)60人,四級(聽力受損大于50 dB 小于等于60 dB)23人。
2.2 研究工具
2.2.1 青少年感恩量表
該量表由何安明等人(2012)修訂。量表包括對自然恩惠的感知與體驗、表達與回報,對他人恩惠的感知與體驗、表達與回報,對社會恩惠的感知與體驗、表達與回報6個因子,共計23個條目,采用5 點計分,得分越高表明感恩程度越強。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9,依據模型修正指數修正后的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為:χ2/df=2.61,RMSEA=0.06,CFI=0.91,TLI=0.90,SRMR=0.05。
2.2.2 生活滿意度量表
該量表由Diener 等人(1985)編制。量表包含5個條目,條目簡單清晰,適合聽障學生作答。采用5 點計分,得分越高表明生活滿意度越高,在國內聽障群體相關研究中有良好的信效度(劉青等, 2017)。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76,依據模型修正指數修正后的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為:χ2/df=1.77,RMSEA=0.04,CFI=0.99,TLI=0.99,SRMR=0.02。
2.2.3 長處和困難量表
該量表由Goodman(1997)編制、劉書君(2006)修訂。量表包括情緒問題、行為問題、多動、同伴交往和親社會行為5個因子。由于本研究主要關注感恩與親社會行為的關系,故只采用了親社會行為部分,共5個條目,采用5 點計分,得分越高表明親社會行為越多。本研究中親社會行為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0,依據模型修正指數修正后的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為:χ2/df=2.71,RMSEA=0.07,CFI=0.99,TLI=0.97,SRMR=0.02。
2.3 施測過程
施測過程以班級為單位,由受過訓練的特殊教育專業本科生完成數據收集工作。要求被試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獨立完成,所有問卷當場回收。
2.4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鑒于研究數據均來源于問卷調查,故采用Harman 單因子檢驗法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結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 的因子共有5個,且第一個因子解釋的變異量為33.25%,小于40%的臨界標準,這說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明顯。
3 結果
3.1 描述性統計和相關分析
獨立樣本t檢驗發現,聽障女生在感恩[t(329)=4.39,p<0.001, Cohen’sd=0.45] 以及親社會行為[t(370)=2.32,p=0.021, Cohen’sd=0.22]得分上均顯著高于男生。生活滿意度的性別差異不顯著(p>0.05)。相關分析發現,聽障學生的感恩、生活滿意度與親社會行為兩兩正相關。平均值、標準差和相關系數見表1。

表1 聽障學生各變量的平均值、標準差及相關系數
3.2 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檢驗
將所有變量按標準化處理后,通過SPSS 宏程序PROCESS 進行有調節的中介效應分析。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 方法檢驗,重復取樣5000 次,對圖1 模型進行檢驗。
根據H a y e s(2 0 1 3)及溫忠麟和葉寶娟(2014)的觀點,首先通過Model 4 檢驗生活滿意度在聽障學生感恩與親社會行為之間的中介作用。結果如表2 所示,在控制性別、學段、年齡和聽障等級后,感恩顯著正向預測生活滿意度,β=0.34,p<0.001;生活滿意度、感恩同時進入回歸方程,感恩顯著正向預測親社會行為,β=0.56,p<0.001,生活滿意度顯著正向預測親社會行為,β=0.23,p<0.001。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 方法檢驗表明,生活滿意度在感恩與親社會行為之間的中介效應顯著,ab=0.08,BootSE=0.02,95%的置信區間為[0.04, 0.12]。感恩影響親社會行為的總效應為0.64,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比例為12.50%。

表2 生活滿意度的中介效應檢驗
隨后,采用Model 7 進行有調節的中介效應分析。控制學段、年齡和聽障等級,結果表明,性別和感恩的交互項顯著正向預測生活滿意度,β=0.12,p=0.027,△R2=0.01。PROCESS 程序進一步分析了調節變量不同取值下的中介效應。結果發現,在女生中,感恩通過生活滿意度影響親社會行為的中介效應為0.04,BootSE為0.02,Bootstrap檢驗95% 的置信區間為[-0.01, 0.09];在男生中,生活滿意度的中介效應為0.10,BootSE為0.02,Bootstrap 檢驗95% 的置信區間為[0.06,0.15]。這表明生活滿意度在感恩與親社會行為之間的中介作用只存在于聽障男生中。進一步的判定指標INDEX 顯示,性別對生活滿意度中介效應的調節判定指標為0.06,BootSE為0.03,Bootstrap檢驗95% 的置信區間為[0.01, 0.12],說明這個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是顯著的,即生活滿意度的中介效應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
為更直觀地描述生活滿意度中介效應的性別差異,依據不同性別學生感恩正負一個標準差對應的生活滿意度分值繪制交互效應圖(見圖2)。簡單斜率分析發現,感恩對生活滿意度的正向預測作用在聽障男生中顯著(B=0.42,t=6.85,p<0.001),在聽障女生中不顯著(B=0.17,t=1.95,p=0.052)。

圖2 性別對感恩與生活滿意度關系的調節作用
4 討論
4.1 感恩與聽障學生親社會行為的關系
本研究發現,感恩不僅與聽障學生親社會行為緊密相關,還能正向預測其親社會行為,這與健聽生的已有研究結果一致(何安明 等, 2014;Bono et al., 2019)。感恩作為一種積極情緒,其功能之一就體現在激發個體做出幫助、合作捐贈等親社會行為上(Bartlett & DeSteno, 2006),個體在感恩的觸發下,其善良行為會得到更大的激發(Layous et al., 2017)。本研究的這一發現也說明,盡管聽障學生經歷了嚴重的社會情緒困難(Mekonnen et al., 2015),但感恩作為一種親和性道德情緒,可以有效促使個體做出親社會行為(陳英和 等, 2015)。由此可見,感恩是促進其親社會行為產生的動力源。
4.2 生活滿意度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還發現生活滿意度在感恩與親社會行為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這與郭芳芳等人(2020)發現聽障青少年的感恩可以通過生活滿意度影響利他行為的結果相一致。這一結果表明感恩對聽障學生親社會行為的作用機制與健聽生一致。也說明積極情緒的拓展-建構理論在聽障群體中同樣適用,即積極情緒促使個體積極主動地參與活動,建構相對持久的多類資源,使其更易表現出親社會行為(李溫平 等, 2019)。感恩除其本身的積極情緒體驗外,還可以使個體獲得更多的生活滿意度這一心理資源(Nezlek et al., 2017),此時的他們也更容易與他人的正義行為產生共鳴,進而激發自身的親社會行為(Michie, 2009)。盡管聽障學生因聽力損傷造成溝通困難,遭遇社會心理問題,導致生活質量惡化(Haukedal et al.,2022),他們的社會歸屬感可能存在一定的問題(Cox et al., 2019)。但感恩的學生可感受到更多的社會支持,并經歷較少的情感困難,從而體驗到更多的生活滿意度(You et al., 2018),因此聽障學生的生活滿意度可以在感恩的觸發下有所提升。此外,近年來,聽障學生作為弱勢群體之一,接受來自社會各界捐贈、幫助的機會不斷增多(姜琨 等, 2022)。當他們具有感恩之心時,更容易將別人的饋贈視為一種善意和關懷之舉,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化解、減輕因為聽覺障礙所導致的各種不如意,產生更多的生活滿足感和幸福感,進而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境下也會更有意愿幫助他人。相反,當他們缺少感激時,外部支持和饋贈被視為理所當然,不易感受到周圍人的善良和關懷,難以紓解其自身的各種不如意,也就無法產生親社會動機或行為(Rizkiana & Santoso,2019)。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本研究發現感恩可以直接或間接影響親社會行為,但這一機制是否會因為求助者的不同而發生變化則尚未可知。如姚小雪(2015)發現當求助者為群體內成員時,聽障大學生的親社會行為并未受影響,而當求助者為群體外成員時,其親社會行為明顯減少。
4.3 性別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還發現生活滿意度的中介作用只在聽障男生中顯著。其原因是感恩對生活滿意度的預測作用只在聽障男生中顯著。這與Tian 等人(2015)發現男生在感恩中會產生更強的學校滿意度相似。在聽障學生中也有類似發現,即感恩對社會支持的影響在聽障高中男生中更強(王玉, 2015)。這表明感恩與性別對生活滿意度的共同作用模式在聽障學生和健聽學生中是相似的。究其原因,可能有兩點。其一,與感恩的性別特質有關。當感恩與對他人的依賴產生聯系時,感恩會影響男性社會地位與男性氣質(Ingoldsby et al., 2005),由此,感恩更容易被視為一種社會化女性特質。當男生表現出感恩時,所附有的雙性化特質使得他們在表達感恩之后會產生更好的積極取向,比如幸福感(Skalski & Pochwatko, 2020)。這也符合雙性化假設,即具有雙性化特質的個體比只擁有單一的男性化或女性化特質的個體更加健康(Lefkowitz & Zeldow, 2006)。其二,與感恩對生活滿意度的作用機制有關。研究表明感恩對生活滿意度產生影響時,還需要通過自尊和積極情緒的中介參與(劉松 等, 2017)。然而聽障男生的正面情緒優于聽障女生(劉敏, 馮維, 2016),自尊水平也高于聽障女生(沈潘艷 等, 2015)。相比聽障男生,聽障女生在社交、競爭中會感受到更多的矛盾與沖突并表現出害怕情緒,容易采取回避方式應對,進而產生更多的自卑感(王淑榮, 2013),而男生則更加獨立自主,他們喜歡參與各類運動與游戲,能夠獲得更多的快樂與積極情緒(張枝梅, 李慶功, 2008)。此外,女生在性別角色的社會期望作用下,人際交往中的敏感性和情緒性使得她們更容易做出親社會行為,而男生出于獨立自我的認知傾向,可能理性地認為個體應該學會自己解決問題,而不是等待他人幫助(Starr &Zurbriggen, 2017)。可見,女生在感恩這一積極情感的影響下,可能更容易表現出親社會行為,而男生可能需要更多的積極情緒激發“感性”觸動,以削弱其“理性”約束,從而表現出親社會行為。
5 結論
(1)感恩顯著正向預測聽障學生親社會行為;(2)生活滿意度在感恩與聽障學生親社會行為間起中介作用;(3)生活滿意度的中介作用只存在于聽障男生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