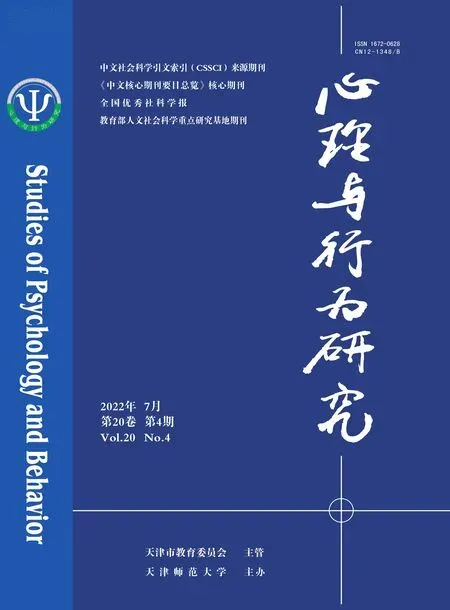特質焦慮與青少年冒險行為的關系:基于雙系統模型的機制探討*
李曉明 劉小丹 戴 婷
(1 湖南師范大學心理學系,長沙 410081) (2 湖南師范大學文化與社會心理研究中心,長沙 410081)
1 引言
冒險行為(risk-taking behavior)指個體面臨趨避沖突時,為尋求某種利益或需求滿足,明知有潛在風險或消極后果卻仍去實施的行為(Ben-Zur &Zeidner, 2009)。雙系統模型是解釋青少年高冒險行為的經典模型,該模型從神經生物學的視角提出青春期的高冒險行為緣自負責抑制沖動的認知控制系統以及與獎賞、情緒相關的社會情緒系統的非同步發展(Shulman et al., 2016; Steinberg, 2008,2010)。青春期中期快速成熟的社會情緒系統會增強青少年對新異刺激的感覺尋求傾向,而發展較慢的認知控制系統還未成熟到足以抑制這些冒險沖動的水平(Casey et al., 2008; Steinberg, 2008),兩種系統在發展時間上的差異導致處于青春期中期的個體在心理層面具有相對偏弱的自我調控能力和更高的感覺尋求傾向,從而使青少年比成人及兒童表現出更高的冒險行為(Ellingson et al.,2019; Figner et al., 2009)。
研究者從人格、環境或認知評估角度探討了青少年冒險行為的成因(田錄梅 等, 2018; 吳云龍等, 2017)。另外,青少年的情緒、情感強烈,其高冒險行為也往往易受情緒因素的驅使(Botdorf et al., 2017)。以往研究多從情緒效價角度探討情緒對冒險行為的影響(Hu et al., 2015),但對具體情緒的探討相對缺乏。
焦慮是青少年最常見的情緒問題之一(孫麗萍 等, 2018),它是人類預感到潛在威脅時,主觀上感到緊張、憂慮、煩惱,也包括自主神經系統活動同時出現亢進的一種情緒反應(Etkin, 2010)。焦慮分為兩種形式:特質焦慮與狀態焦慮(李文利, 錢銘怡, 1995)。以往研究發現,焦慮與風險認知及決策關系密切(Nash et al., 2021),這些研究多集中于成人群體。例如,以往研究發現,焦慮會使個體更傾向做出保守行為,并提出認知資源因素、信息加工因素以及概率偏向因素等解釋(古若雷, 羅躍嘉, 2008)。但也有研究發現,高特質或狀態焦慮者的冒險水平反而更高(Miu et al.,2008; Xia et al., 2017)。少量涉及青少年群體的研究發現,高特質焦慮者更愿意交往吸煙的朋友,也更傾向于表現出強烈自殺想法等危險性冒險行為(Soleimani et al., 2017),但相關研究并未針對青少年群體深入探討焦慮對冒險行為的作用機制。
本研究將基于青少年冒險行為領域的雙系統模型,嘗試從自我調控和感覺尋求角度探討特質焦慮與青少年冒險行為間的關系。自我調控指個體有意識調控自己的認知、情緒以及行為以服務于當前目標,自我調控能力與大腦中負責認知控制的腦區及其功能有關(Shulman et al., 2016)。自我調控能力與人們應對復雜風險情境下的決策行為具有密切關系,對青少年的冒險行為具有直接預測作用(Duell et al., 2016; Figner et al., 2009),表現為低自控者更容易實施賭博、吸煙、飲酒、網絡成癮或犯罪等冒險行為(田錄梅 等, 2018; 吳云龍 等, 2017; Cheung, 2016; Ha & Beauregard,2016)。以往研究發現,高焦慮會損傷個體的中央執行功能,降低其認知控制及自我調控能力(Pacheco-Unguetti et al., 2010; Wegbreit et al., 2015),這種損傷對于青少年而言尤為明顯(Cohen et al.,2016)。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設1:對于自我調控能力尚未成熟的青少年而言,高焦慮可能會通過削弱個體的自控力而提高其冒險行為,即自我控制可中介焦慮對青少年冒險行為的影響。
感覺尋求是一種尋求和探索新奇環境刺激的傾向(Zuckerman et al., 1978)。隨著青春期荷爾蒙分泌增多,青少年的社會情緒系統會快速成熟發展,社會情緒系統的喚醒集中表現于大腦對獎賞的高敏感性,增強了青少年對刺激、新異及危險行為的追求(即高感覺尋求傾向)(Smith et al., 2013),由此導致青少年會表現出高冒險行為(Agilonu et al., 2017)。另一方面,感覺尋求或可調節自我控制對冒險行為的影響。例如,青少年的感覺尋求水平越高,自我控制對其藥物濫用的影響力會越大(Castellanos-Ryan et al., 2013)。雙系統模型也認為青少年社會情緒系統的高度激活會削弱尚未成熟的認知控制系統的調控,即強烈的感覺尋求傾向會使青少年更易跨越理性認知系統的控制,表現出更強的冒險行為(Shulman et al., 2016;Steinberg, 2010)。對于高感覺尋求的青少年而言(相比于低感覺尋求者),其冒險行為會更易因其未發展完善的自控能力而增強(Peeters et al.,2017)。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設2:在特質焦慮通過自我控制影響青少年冒險行為的中介過程中,感覺尋求調節了后半段路徑,即對高感覺尋求的青少年而言,自我控制能力對其冒險行為的影響更大。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采用方便整群抽樣方式,選取重慶市和湖南省長沙市城區三所普通中學(初一至高三)的1720名青少年(年齡范圍12~18 歲)參與本次調查研究,共回收問卷1654 份(回收率為96.2%),剔除無效問卷后共得到有效問卷1549 份(有效率為93.7%)。其中,男生746人,女生803人。初一261人,初二276人,初三228人,高一273人,高二282人,高三229人。平均年齡14.51±1.64 歲。其中父母婚姻狀況(4 類評分):穩定1393人(89.9%),離婚87人(5.6%),單親17人(1.1%),再婚52人(3.4%)。自評家庭經濟狀況(5 類評分):好219人(14.1%),較好538人(34.7%),一般723人(46.7%),差43人(2.8%),較差26人(1.7%)。
2.2 研究工具
2.2.1 特質焦慮問卷
特質焦慮問卷(Spielberger et al., 1983)是狀態-特質焦慮問卷的分量表之一。該問卷共20個項目,例如“當我考慮我目前的事情和利益時,我就陷入緊張狀態”。采用4 級評分,評分標準從“幾乎沒有”“有些”“經常”到“幾乎總是如此”,個體的得分越高表明其特質焦慮程度越高,其中文版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8(李文利, 錢銘怡, 1995)。本研究采用中文版特質焦慮問卷(汪向東 等, 1999)測量青少年的特質焦慮水平,其中1、3、4、6、7、10、13、14、16、19 題描述正向情緒體驗,需反向計分。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5。
2.2.2 簡版自我控制量表
采用Unger 等人(2016)修訂的自我控制量表中文簡版測查青少年的自我控制水平,共13個項目,例如“我能很好地抵制誘惑”,其中2、3、4、5、7、9、10、12、13 題負向描述自我控制,需要反向計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75。采用5 級評分,評分標準從“非常不符合”“不符合”“不確定”“符合”到“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明其自我控制能力越好。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0。
2.2.3 感覺尋求量表
采用Wang 等人(2000)修訂的第五版感覺尋求量表的中文版, 4個維度的重測信度為0.70~0.94(Wang et al., 2000)。本研究主要探討與冒險行為相關的感覺尋求,因此只選取第五版感覺尋求量表中的興奮與冒險尋求維度(TAS)測查青少年的感覺尋求傾向,共10個項目,量表為迫選形式,采用0、1 計分,每個項目包括兩個選項,例如“A. 我很想自己能成為一名登山運動員;B. 我不理解為什么有人冒險登山”,選擇感覺尋求的一項計1 分。得分越高,表明個體的感覺尋求傾向越強。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70。
2.2.4 青少年多領域冒險行為問卷
青少年多領域冒險行為問卷由尚麗和張麗錦(2011)根據Weber 等人(2002)提出的冒險領域特殊性理論編制而成。該量表共33個項目,例如“公開表明你的品位或觀點與朋友們的不同”,無反向計分題,Cronbach’s α 系數為0.90。分4個維度:社會冒險、娛樂冒險、安全冒險和道德冒險,采用5 級評分,評分標準從“非常不可能”“比較不可能”“不確定”“比較可能”到“非常可能”,得分越高表明其從事冒險行為的傾向越高。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91。
2.2.5 流調中心用抑郁量表
Radloff(1977)編制的流調中心用抑郁量表,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在病人組及正常人組中均為0.90 以上,共20個項目,例如“我被一些通常并不困擾我的事困擾”,其中4、8、12、16 題負向描述抑郁水平,需反向計分。采用0~3 點的4 級評分,總分越高表示個體的抑郁程度越高。本研究采用中文版流調中心用抑郁量表(汪向東 等,1999)測量青少年的抑郁水平,以排除抑郁對研究結果的影響。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91。
2.3 研究程序
本研究采用統一的指導語,通過團體測試的形式,在課堂上進行,現場發放并回收問卷。此外,調查問卷的呈現順序如下:指導語、特質焦慮問卷、簡版自我控制量表、感覺尋求量表、青少年多領域冒險行為問卷、流調中心用抑郁量表、人口學信息(性別、年齡、年級、父母婚姻狀況及自評家庭經濟狀況)、致謝。
3 結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為了防止預測變量與效標變量之間的人為共變,本研究采用Harman 單因素檢驗法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結果顯示:有19個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其中第一個因子可以解釋的最大變異量為18.54%,小于40% 的臨界值(Podsakoff et al., 2003),說明本研究對各變量雖均采用問卷法進行測查,但不存在明顯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如表1 所示。因抑郁與特質焦慮和冒險行為存在顯著正相關,而與自我控制存在顯著負相關,因此抑郁也將作為控制變量納入到隨后的中介和調節分析中。由于性別、年齡、年級、父母婚姻、家庭經濟狀況顯著影響青少年冒險行為(Crandall et al.,2017; McCoy et al., 2019; O’Brien & Mindell, 2005),因此,本研究也將這些變量作為控制變量納入后續分析。

表1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結果
3.3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
首先,采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 法,通過Hayes(2013)編制的SPSS 宏程序PROCESS(www.afhayes.com)進行自我控制中介效應分析,具體操作步驟如下:在描述統計中先將各變量進行標準化處理,再選擇PROCESS 宏程序,將性別、年齡、年級、父母婚姻、家庭經濟狀況、抑郁放入控制變量中,選擇簡單的中介模型Model 4,設置Bootstrap Samples 為5000,置信區間為95%。
中介效應檢驗的結果(見表2)表明:特質焦慮對冒險行為具有顯著預測作用,當放入自我控制這一中介變量后,特質焦慮不能顯著預測冒險行為(β=0.06,t=1.94,p=0.052)。由此可見自我控制在特質焦慮對冒險行為的影響中具有中介作用。

表2 自我控制的中介模型檢驗
中介分析的結果表明,自我控制中介效應的Bootstrap 95%置信區間為[0.09, 0.16],不包括0,說明自我控制的中介效應顯著,中介效應值為0.12;此外,在引入自我控制后,特質焦慮對冒險行為的影響不顯著,直接效應值為0.06,Bootstrap 95%置信區間為[-0.00, 0.12],包括0,說明特質焦慮不能直接影響冒險行為,自我控制在特質焦慮和冒險行為間起完全中介作用。即特質焦慮通過自我控制間接影響冒險行為,具體表現為,個體的焦慮程度越高,自我控制能力越差,個體從事冒險行為的傾向越高。對自我控制的中介效應進行分析發現,自我控制在焦慮與冒險行為間的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比例為66.67%。
其次,在自我控制中介效應顯著的基礎上,為檢驗感覺尋求在特質焦慮通過自我控制影響青少年冒險行為中后半段的調節作用,同樣采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 法進行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具體操作步驟同上,選擇模型M o d e l 14(Model 14 假設中介效應的后半段受到調節,與本研究理論假設模型一致),將性別、年齡、年級、父母婚姻、家庭經濟狀況、抑郁作為控制變量,檢驗結果見表3。將感覺尋求放入模型后,自我控制與感覺尋求的乘積項對青少年冒險行為的預測作用顯著(β=-0.07,t=-3.58,p<0.001),表明感覺尋求能調節自我控制對冒險行為的影響。

表3 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檢驗
進一步分析感覺尋求的調節效應,如表4 所示,隨著個體感覺尋求水平的不斷增加,自我控制在特質焦慮對冒險行為影響中的中介作用也不斷增大。簡單斜率分析表明(見圖1),對于高感覺尋求者(M+1SD)而言,自我控制對其冒險行為存在顯著負向預測作用(βsimple=-0.59,t=-18.34,p<0.001);對于低感覺尋求者(M-1SD)而言,自我控制雖對冒險行為具有顯著預測作用,但其預測作用相對降低(βsimple=-0.42,t=-14.00,p<0.001)。

圖1 感覺尋求對自我控制與冒險行為的調節作用

表4 感覺尋求對自我控制的中介效應的調節效應分析
4 討論
本研究發現,個體的特質焦慮水平能負向預測其自我控制水平,并正向預測其冒險行為,而自我控制水平又可負向預測個體的冒險行為,進一步中介分析表明,自我控制可中介特質焦慮對青少年冒險行為的影響,支持了假設1。同時,這一中介過程的后半路徑又被個體的感覺尋求水平所調節,支持了假設2,主要表現為:個體的感覺尋求水平越高,自我控制對其冒險行為的預測作用越高,這可能因為低感覺尋求者整體上的冒險傾向偏低,因此自我控制對其冒險行為的抑制作用會降低,相對而言,自我控制對高感覺尋求者冒險行為的約束作用會更突顯。本研究發現,特質焦慮可提高青少年的冒險行為水平,同時也支持了雙系統模型假設(Steinberg, 2010),表明個體的自我控制能力(認知控制系統)及感覺尋求傾向(社會情緒系統)有助于解釋特質焦慮與青少年冒險行為間的關系。
本研究通過大樣本數據證實了焦慮對青少年冒險行為的負面影響,這也表明青少年的高冒險行為易受情緒因素所影響,高焦慮會削弱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能力,進而提高了其冒險行為(尤其是高感覺尋求者)。本研究基于雙系統理論探討了焦慮對青少年冒險行為的影響機制,豐富了對焦慮與冒險行為之間關系的理解,也為在焦慮這一典型負性情緒背景下檢驗雙系統模型提供了重要證據,本研究也表明自我控制與感覺尋求傾向對青少年的風險行為存在交互影響(Castellanos-Ryan et al., 2013),但也有研究發現,二者對青少年風險決策的影響是相互獨立的(Duell et al.,2016),這可能因為二者對青少年冒險行為的影響存在文化差異,正如Duell 等人提出西方文化更鼓勵青少年去自由探索與冒險,相對忽視個體對其行為的自我約束,由此導致在西方文化下,自我控制難以影響感覺尋求與青少年冒險行為間的關系,呈現出二者相互獨立的影響模式。Duell 等人也提出東方文化更強調個體對行為的自我約束,使二者更易出現交互作用,本研究也發現這種自我約束的優勢尤其表現于高感覺尋求的青少年群體中。
本研究也提示教育者應重視焦慮對個體心理行為的這一負面影響,尤其是對于處于特殊時期的青少年來說(如初三及高三時期的學生),此時除了情緒及學習問題外,教育工作者也應重視有效規避學生可能因高焦慮所誘發的高冒險行為,并思考如何通過提高青少年的自控力對其進行有效干預(Rosenbaum et al., 2017)。另外,本研究發現,個體的感覺尋求水平除了可直接影響青少年的冒險行為外,還可調節自我控制對其冒險行為的影響。雙系統模型認為相比于成年人,青少年會對環境中的情緒信息更加敏感,例如,當青少年處于令人激動的環境或有他人在場時,其社會情緒系統更易被激活,此時更容易受限于其尚未成熟的自我調控能力而表現出高冒險行為(張瑋瑋, 朱莉琪, 2021),這也表明教育工作者可通過營造舒緩的外部環境來抑制其冒險行為。
本研究雖具有一定的理論和實踐價值,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的被試取樣在地域及學校類型的代表性上存在不足,未來可以選取更具代表性的樣本,以進一步檢驗相關結果的可靠性和普適性。其次,本研究通過問卷法初步探討了特質焦慮與青少年冒險行為的關系及可能的影響機制,未來可采用實驗法客觀操縱青少年的焦慮狀態或通過自我損耗任務操縱其自控狀態以進一步考察狀態焦慮及狀態自控與青少年冒險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最后,未來可進一步基于雙系統模型探討其他具體負性情緒(如憤怒、恐懼、悲傷)對青少年冒險行為的影響,以檢驗在其他情緒背景下,雙系統模型是否仍能成為其有效的解釋機制。
5 結論
(1)特質焦慮能正向預測青少年的冒險行為,自我控制在特質焦慮與冒險行為間的關系中起中介作用。(2)個體的感覺尋求水平可調節特質焦慮與冒險行為間的關系,即個體的感覺尋求水平越高,自我控制對冒險行為的預測作用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