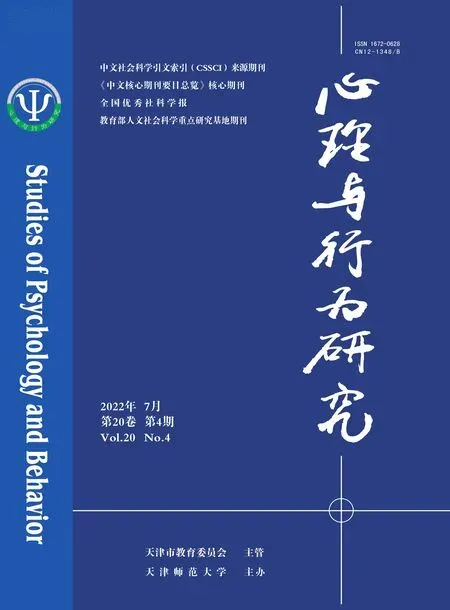家庭環境和教師支持對中學生學業拖延的影響:基本心理需求滿足與心理資本的鏈式中介作用*
曾玲娟 江麗晶 彭 葉
(1 南寧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南寧 530299) (2 湖南省殘疾人康復研究中心,長沙 410300)
1 引言
學業拖延是指在學習過程中,學生的學業任務計劃和執行之間存在差距,表現為不合理利用時間而不及時完成或匆忙完成學習任務的一種非理性行為(左艷梅, 2010),在中學生群體中普遍存在(陳貴 等, 2012)。學業拖延易導致學習者學業成績下降(李瑛, 崔樹軍, 2017),產生焦慮、內疚、自責等消極情緒(Kim & Seo, 2015)。“雙減”政策落地推進過程中,如何引導學生減少學業拖延、提高學習質量給家長和教師帶來了更大的挑戰(馬開劍 等, 2021)。
1.1 家庭環境、教師支持與學業拖延
生態系統理論認為家庭環境是個體發展最持久和最重要的系統(Bronfenbrenner, 1992)。父母作為家庭教育中的主要執行者,其言行舉止直接影響學生學習習慣和品質的養成(孫小堅 等,2021)。研究發現,父母教養方式與中學生學業拖延具有顯著相關(楊青松 等, 2017),父母的關懷和溫暖能降低孩子的學業拖延,父母控制、拒絕和懲罰則加重學業拖延(鄭治國 等, 2018)。此外,隱性家庭環境因素如父母文化程度(雷曉梅等, 2019)、家庭教育模式(Pinxten et al., 2019)、婚姻狀況(Pi?eiro et al., 2019)均能顯著影響孩子的學業情況。
中學生的微觀系統主要存在于學校和家庭環境中(陳英敏 等, 2019),關于學生學業的影響因素,除家庭環境外,學校環境中的教師支持也是重要因素。教師支持是指在學習活動中,教師為學習者提供行為、策略、情感的支持和幫助,包括自主支持、情感支持和認知支持三個核心成分(柴曉運 等, 2011; 劉斌 等, 2017)。研究發現,當學生感知到教師的自主支持時,會表現出更多的學習興趣,得到學校生活的愉悅體驗,在學習上有更高的努力和堅持性(Jang et al., 2010),教師支持可促進學生學習動機的內化(羅云 等, 2014),減少拖延行為。
Epstein 和Sanders(2006)基于生態系統理論和社會資本理論提出了重疊領域理論,強調家校協同在孩子教育、成長等方面發揮累積作用,認為當家庭、學校協同支持學生的學習和發展時,學生會獲得更大程度的成功。因此,有必要整合家庭環境與教師支持兩方面因素來研究對中學生學業拖延的影響及其內部作用機制。
1.2 基本心理需求滿足的中介作用
自我決定理論認為,個體天生具有自我發展和完善傾向,自主性、勝任和歸屬這三種基本心理需求是個體健康成長與功能發揮的必需營養,在社會環境與個體互動中起中介作用(Ryan & Deci,2017),支持性的環境能夠通過滿足個體的基本心理需要(鄧林園 等, 2020)激發學生學習的內部動機,促進主動管理并負責相應學習任務(Ryan &Deci, 2000)。實證研究也發現,基本心理需求滿足在家庭環境與學習投入(譚諍 等, 2021)、學業倦怠(張俊, 高丙成, 2019)間起部分或完全中介作用。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H1:基本心理需求滿足在家庭環境對中學生學業拖延的影響中起中介作用。
此外,基本心理需求滿足也可以在教師支持與學業倦怠(羅云 等, 2014)、學習內部動機(邢強 等, 2021)之間起部分或完全中介作用。因此,結合自我決定理論,本研究提出假設H2:基本心理需求滿足在教師支持對學業拖延的影響中起中介作用。
1.3 心理資本的中介作用
社會認知論認為,環境因素要通過個體的內部因素才能作用于行為(Bandura, 1977)。資源保存理論也認為,個體會不斷爭取和保持對自己有價值的個人資源,并利用這些資源幫助自身應對并處理各種問題(如學業拖延)(Hobfoll, 2002)。心理資本是個體在成長中逐漸形成的一種積極心理能量與內部資源,教師支持和家庭環境作為環境因素,將學業拖延視為個體行為,可以推測心理資本為本研究的另一個中介變量。研究發現,家庭環境中的親密感和知識性維度能顯著預測中學生的自我效能感(張蕓蕓, 2010)。作為心理資本的重要維度,學生自我效能感越強,學習態度就越積極(石雷山 等, 2013)。另外,心理資本在教師支持和學業投入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陳鳳至, 盧小陶, 2021)。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假設H3:心理資本在家庭環境與學業拖延之間起中介作用。假設H4:心理資本在教師支持與學業拖延之間起中介作用。
1.4 基本心理需求滿足與心理資本的鏈式中介作用
基本心理需求滿足能正向預測心理資本(Carmona-Halty et al., 2019)。結合生態系統理論(Bronfenbrenner, 1992)可知,當處在有益、支持性的家庭及學校環境中時,學生的基本心理需求較能得到滿足,他們會體驗到更多的希望、效能、復原力和樂觀(即積極心理資本),進而提高其學習自主性(Carmona-Halty et al., 2019)。根據資源保存理論(Hobfoll, 2002)和積極情緒拓展-建構理論(Fredrickson, 1998),個體將努力根據外部環境資源(如家庭環境和教師支持)來構建和積累內部心理資源,以維護和促進自身進步。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假設H5:基本心理需求滿足和心理資本在家庭環境與學業拖延之間起鏈式中介作用。假設H6:基本心理需求滿足和心理資本在教師支持與學業拖延之間起鏈式中介作用。
綜上所述,本研究在已有研究成果和研究理論的基礎上,探究家庭環境和教師支持對中學生學業拖延的影響機制,假設模型如圖1 所示。

圖1 假設模型圖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采用整群抽樣方式,在3 所中學(完中、高中、初中各1 所)選取初中生和高中生共781名為研究對象,剔除作答不完整等無效問卷后,最終回收有效問卷740 份,有效率為94.75%。其中,男生304名,女生436名;獨生子女256名,非獨生子女484名;初中生360名(初一137名、初二109名、初三114名),高中生380名(高一160名、高二158名、高三62名)。
2.2 研究工具
2.2.1 中學生家庭環境問卷
采用陳暉(2009)編制的中學生家庭環境問卷,共28 題,分為和睦性、親密性、溝通性、文化性、修養性、民主性共6個維度。采用5 點計分,得分越高表示家庭環境越好。本研究中該問卷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91,驗證性因素分析顯示:χ2/d f=2.9 1,G F I=0.9 2,C F I=0.9 2,RMSEA=0.05。本研究中該問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2.2 學生感知教師支持行為問卷
采用歐陽丹(2005)編制的學生感知教師支持行為問卷,共19 題,分為學習支持、情感支持和能力支持3個維度。采用6 點計分,得分越高,說明學生感知教師支持行為越高。本研究中該問卷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90,驗證性因素分析顯示:χ2/df=4.37,GFI=0.92,CFI=0.91,RMSEA=0.07。本研究中該問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2.3 基本心理需求量表
采用劉俊升等人(2013)修訂的基本心理需求量表,共21 題,分為自主性需求、勝任需求和歸屬需求3個維度。采用7 點計分,得分越高,說明基本心理需求滿足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該問卷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4,驗證性因素分析顯示:χ2/df=3.36,GFI=0.93,CFI=0.90,RMSEA=0.06。本研究中該問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2.4 積極心理資本問卷
采用張闊等人(2010)編制的積極心理資本問卷,共26 題,分為自我效能、韌性、希望、樂觀4個維度。采用7 點計分,得分越高,表明構建的心理資本越積極。本研究中該問卷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91,驗證性因素分析顯示:χ2/df=3.51,GFI=0.91,CFI=0.90,RMSEA=0.06。本研究中該問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2.5 中學生學業拖延問卷
采用左艷梅(2010)編制的中學生學業拖延問卷,共17 題,分為延遲計劃、延遲執行、延遲補救、延遲總結4個維度。采用5 點計分。該量表是一個整體的負向計分量表,得分越高,學業拖延程度越低。本研究中該問卷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90,驗證性因素分析顯示:χ2/df=4.02,GFI=0.93,CFI=0.93,RMSEA=0.06。本研究中該問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3 數據處理與分析
采用SPSS22.0 進行描述性統計和相關分析;使用Amos24.0 建立結構方程模型進行鏈式中介效應檢驗。
3 結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由于研究數據均來自被試自我報告,為控制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采用Harman 單因素檢驗進行統計分析。結果顯示,特征根大于1 的因子共有23個,第一個因子的變異解釋率為19.67%,小于臨界值40%,說明本研究不存在明顯的共同方法偏差(熊紅星 等, 2012)。
3.2 描述統計與相關分析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見表1。結果顯示,家庭環境、教師支持、基本心理需求滿足、心理資本與學業拖延兩兩之間具有顯著正相關(其中,學業拖延得分越高,表示被試學業拖延程度越低),相關系數在0.35~0.73 之間,為假設檢驗奠定了基礎。

表1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
3.3 基本心理需求滿足與積極心理資本的鏈式中介效應檢驗
3.3.1 路徑分析
依據研究假設構建結構方程模型,具體參數結果見圖2。該模型擬合指標為:χ2=733.40,df=156,p<0.001,χ2/df=4.70,GFI=0.90,CFI=0.93,TLI=0.91,RMSEA=0.07。指標均達到模型適配標準(吳明隆, 2010),表明該模型擬合指數良好。
測量模型結果顯示:家庭環境上的因子載荷為0.30~0.92,教師支持上的因子載荷為0.76~0.87,基本心理需求滿足上的因子載荷為0.70~0.78,心理資本上的因子載荷為0.72~0.82,學業拖延上的因子載荷為0.55~0.81。所有的載荷值均在0.3 及以上,且均達到0.001 水平上的顯著性,表明這些因子均能較好地表征所需測量的各個潛在特征(吳明隆, 2010)。
圖2 呈現了結構方程模型中各個變量之間路徑的預測值及其顯著性情況:(1)家庭環境可以顯著預測基本心理需求滿足(β=0.30,p<0.001)和學業拖延(β=0.17,p<0.001);(2)教師支持可以顯著預測基本心理需求滿足(β=0.50,p<0.001)和學業拖延(β=0.23,p<0.001);(3)基本心理需求滿足可以顯著預測心理資本(β=0.81,p<0.001);(4)心理資本可以顯著預測學業拖延(β=0.65,p<0.001);(5)其余路徑不具有顯著預測性。這一結果提示,以基本心理需求滿足和心理資本為鏈式中介的路徑成立,但分別以基本心理需求滿足、心理資本為單一中介的路徑可能不成立。

圖2 結構方程模型
為深入探究已成立的三條指向學業拖延的標準化路徑系數之間的差異,檢驗其兩兩之間的系數差值顯著性,結果見表2:心理資本對學業拖延的作用顯著高于家庭環境(95%CI[0.16, 0.71],p<0.01),心理資本對學業拖延的作用顯著高于教師支持(95%CI[0.23, 0.76],p<0.001);而家庭環境與教師支持對學業拖延的作用無顯著差異(95%CI[-0.11, 0.20],p>0.05)。

表2 學業拖延的影響因素效應值顯著性比較
3.3.2 鏈式中介效應檢驗
為進一步檢驗可能存在的中介效應,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 法,設置迭代次數為5000,如果平均路徑系數95%的置信區間不包含0,效應值顯著;如果包含0,則不顯著(溫忠麟,葉寶娟, 2014)。結果顯示(見表3),在總效應上,家庭環境、教師支持對學業拖延的總效應值分別為0.28、0.44,95%CI 分別為[0.20, 0.36]、[0.36, 0.52],總效應值顯著。加入了兩個中介變量后,家庭環境和教師支持仍然能直接地顯著預測學業拖延,直接效應值分別為0.17、0.23。但分別以基本心理需求滿足、心理資本為單一中介的4 條路徑(ind1-1、ind1-2、ind2-1、ind2-2)的95%置信區間包含0,均不顯著。以家庭環境、教師支持為自變量的鏈式中介路徑成立,鏈式中介效應值分別為0.16、0.27,占總效應比值分別為57.14%、61.36%。

表3 鏈式中介模型的效應分解表
4 討論
4.1 個體心理資本比家庭環境和教師支持更能預測學業拖延
本研究結果發現,家庭環境和教師支持均對學業拖延有顯著性影響,其中教師支持對學業拖延的預測作用略大于家庭環境,但并未達到顯著差異,說明教師支持和家庭環境對學生學業拖延的影響力相當,與前人的研究中把對學生學習投入(李維, 2021)、學習倦怠(張俊, 高丙成,2019)等的影響更多歸因于教師因素的結果并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學業拖延的影響機制比學習投入、學習倦怠等的影響機制更為復雜,且以往研究并未進行效應值的差異檢驗。本研究還發現,心理資本對學業拖延的預測作用比家庭環境和教師支持都大,說明學生自身積極心理資本的建構更加重要。學生的學業發展更多依賴于內部心理資本發揮的作用,促使他們在面對逆境時能去克服困難,以更積極的態度在學業上投入精力與時間,及時、主動地完成學習任務。
4.2 基本心理需求滿足不能直接預測學業拖延
本研究并未發現基本心理需求滿足在家庭環境/教師支持與學業拖延之間的中介作用,基本心理需求滿足不能直接顯著預測學業拖延。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是中學生學習動機的特殊性與學業的復雜性。根據驅力理論(岑國楨, 1994),基本心理需求滿足屬于內驅力,能促進外部動機向內部動機轉化,從而可能產生相應的行為。但中學生的外在動機內化整體發展水平一般,以認同調節為主(劉艷, 2011),即學生認識到學習的重要性,并將學習納入自我決定的一部分,但只是將這種行為的價值與自身興趣進行整合并作為自我的一個獨立部分保留(即個體的自主性需求滿足),并沒有將其內化整合到自我中去,與自我中的其他部分仍然是相互分離的(王思, 2015),故難以直接驅動行為去減少學業拖延。有研究也發現,基本心理需求的滿足會影響內在動機,而內在動機又與更主動或被動的學習行為有關,強調了內在動機的中介作用(Pelikan et al., 2021)。故單純通過滿足個體基本心理需求不能直接影響學業拖延。
4.3 家庭環境/教師支持對心理資本并非直接預測
本研究并未發現心理資本在家庭環境/教師支持與學業拖延之間的中介作用,更準確地說是家庭環境/教師支持不能直接地顯著預測心理資本。中學生所處的家庭-學校聯合的微觀系統對于其積極心理資本的構建與積累并非是直接形成的,研究也發現支持性的環境會完全通過影響初中生的自尊、心理一致性體驗和認知評價方式來間接影響其內部心理資源的構建,而并非直接影響(高曉彩 等, 2019)。心理韌性動態模型表明,學生獲得良好的外部資源后會促成其內部資源的養成(王秋英 等, 2020)。也有研究者基于社會資本理論發現,不同家庭、學校、社區等環境會給孩子提供不同的社會資本,進而對于構建其心理資本產生不同的影響(Tang & Zhao, 2020)。
4.4 基本心理需求滿足與心理資本的鏈式中介作用
結構方程模型顯示,基本心理需求滿足與心理資本在家庭環境/教師支持與學業拖延之間起鏈式中介作用,驗證了研究假設H5、H6。即家庭環境和教師支持滿足了中學生的基本心理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其積極心理資本的構建,從而促進學習主動性與及時性,減少學業拖延。以往研究也證明了在養育子女過程中,基本心理需求的滿足是提升孩子心理資本的重要因素(Ataee &Bagheri, 2019)。教師支持也能為學生創造一種有益的教育環境以滿足學生的心理需求(Rahmadani et al., 2019),進而發展其心理資本以推動自主學習(Sava et al., 2020)。總之,良好的家庭環境與教師支持均能夠通過滿足學生的基本心理需求,進而構建心理資本,減少學業拖延。
4.5 實踐意義與研究局限
本研究對于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協同改善中學生學業拖延具有重要啟示。首先,教師支持要發揮對中學生學業發展的主導性作用,良好的家校合作能夠充分促進學生的學習動力(白學軍 等,2022)。父母應當配合學校教育構建積極、文明、和諧的家庭環境,以滿足中學生的基本心理需求并提升心理資本,提高其學習主動性和及時性。其次,重視多種方式來構建學生的積極心理資本,形成正向、積極的學習態度。最后,學校教育的“共性”與家庭教育的“個性”之間的優勢互補、互利共贏促進學生學習習慣的養成。
本研究仍存在以下局限。首先,模型構建的結果顯示基本心理需求滿足與心理資本并不能起到單一中介作用,未來可進一步探究其與其他變量的內部作用關系。其次,中學生學業行為受諸多因素影響,本研究僅從家庭和教師兩方面探討了學業拖延發生的內部機制,未來還可以納入同伴關系、社區環境等變量進行更為全面的探討。
5 結論
家庭環境、教師支持和心理資本均對學業拖延有顯著影響;家庭環境和教師支持對學業拖延的影響力相當,而個體心理資本的影響作用力更大;家庭環境和教師支持還能通過基本心理需求滿足與心理資本的部分鏈式中介作用來影響學業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