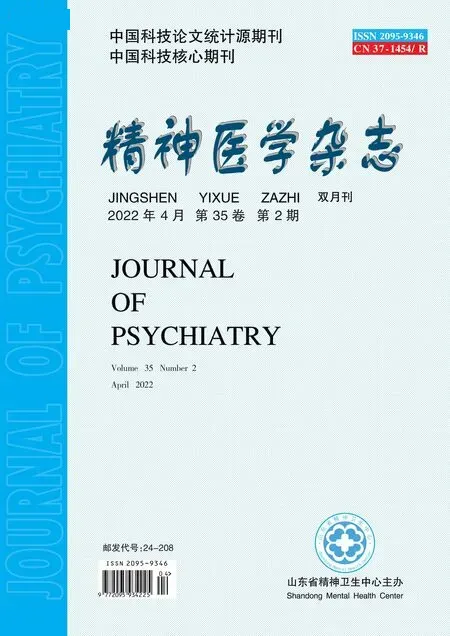有自傷行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狀態及相關因素分析*
青少年時期獨特的心理生理過程,使個體的身心發展呈現顯著的不平衡性及偏激性,更易導致一系列的心理危機。國內外針對青少年自傷行為的流行病學調查均顯示其發生率高達40%以上[1,2]。自傷行為是指故意造成對自己身體進行傷害的行為,借此宣泄一時的不良情緒,其目的并不是要造成死亡,屬于情緒調節行為。國外對社區青少年自傷行為進行的研究發現,將反復紋身作為一種自傷行為時,71.4%的有反復紋身行為的青少年是為了體驗紋身導致的皮膚疼痛,因而得出反復紋身行為是青少年具有非自殺性自傷(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的獨特表型[3]。國內的一些調查顯示,青少年自傷行為中使用最多的自傷方式也是“故意在皮膚上刻字或畫畫”,最初的自傷理由就是“調節情緒與釋放壓力”[1]。自傷行為是NSSI發生的最強預測因子[4],而NSSI又是自殺的獨立危險因素[5]。其可能機制是自傷行為往往會導致個體對疼痛的耐受性增加和對死亡恐懼的減少,從而出現反復自傷行為。青少年自傷行為日益增多,并呈全球性增長的趨勢,也早已經成為威脅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主要原因之一。
來自英國諾丁漢大學自我傷害研究小組的Townsend E[6]曾呼吁,鑒于許多死于自殺的人被評估為低風險,這就意味著必須認真對待所有自傷的想法和行為,并為其提供具有循證證據的心理療法,幫助他們應對這種想法和痛苦。在英國,自我傷害的預防已列入國家預防自殺戰略的優先事項。而影響青少年自傷行為的重要因素包括遺傳易感性和精神心理、家庭、社會以及地域文化等[7]。本研究聚焦面臨這些問題的青少年,篩選出有自傷行為的青少年群體,充分評估其心理健康狀態(包括焦慮抑郁水平、睡眠質量、自殺風險等)、家庭相關因素和個性特征(包括一般自我效能感及特質應對方式等),并對上述三者之間潛在的關系進行探討。以期能夠幫助監護人或管理者及臨床醫生盡早識別并干預未來可能出現自殺企圖的青少年。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2018年12月~2019年1月,采用橫斷面調查的方法在蘇州市某城區設立的全部18所中學對12 798名中學生展開心理健康問卷普查。最終獲得12 354名學生同意參加該普查,并完成了相關調查問卷。435名學生的問卷被判為無效問卷并排除在外,最終獲得11 919份有效問卷,有效率為 96.5%。在所有有效問卷中,篩選出具有自我傷害行為的中學生問卷作為研究對象,因此本研究共納入1 482份調查問卷進行統計分析。
1.2 方法
1.2.1 自編一般人口學問卷 包括姓名,性別,年齡,民族,是否為獨生子女,居住方式(“與父母同住”“與爺爺奶奶或外公外婆同住”“與親戚同住”“其他,請說明”),父親及母親的文化程度,父母關系如何(不清楚,非常好,很好,一般,很差,非常差)等。
1.2.2 心理健康狀態評估 (1)7條目廣泛性焦慮量表(7-item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GAD-7)中文版[8]:自評量表。共7個條目,采用0(完全不會)~3(幾乎每天)級評分,總分0~21分。本研究中GAD-7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4。(2)9條目患者健康問卷(9-item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9)[9]:自評抑郁癥狀群量表。共9個條目,采用0(完全不會)~3(幾乎每天)級評分,總分范圍0~29分。本研究中PHQ-9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2。(3)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中文版[10]:自評量表。采用參與計分的18個自評條目組成7個成份,每個成份按照0~3級計分,累計各成份得分為PSQI總分。總分范圍為0~21分,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質量越差。刪除量表中需要被試者填寫的通常上床時間和起床時間兩個條目,計算本研究中PSQI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1。(4)當前的自殺風險(Suicidal Risk,SR)采用簡明國際神經精神訪談(Mini-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view, MINI)自殺篩選問卷[11]進行評估:內容涵蓋了自殺意念、自殺計劃及自殺未遂等多個方面,總分從0~33分,劃分為低、中、高3個風險等級。
1.2.3 青少年個性特征評估 (1)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中文版[12]:包含10個項目。采用4點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評分,“完全錯誤”計1分,“有點正確”計2分,“多數正確”計3分,“完全正確”計4分。總分越高,表示被試的自我效能越高。本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數為0.88。(2)特質應對方式問卷(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TCSQ)[13]:分為積極應對方式(Positive Coping, PC)與消極應對方式(Negative Coping, NC)。各包含10個條目,每個條目采用1~5級計分,“肯定不是”計1分,“肯定是”計5分,“大部分不是”計2分,“中等”計3分,“大部分是”計4分。本研究中積極應對方式和消極應對方式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是0.85、0.86。
1.2.4 “有自傷行為”的評定方法 在調查問卷中詢問:“在過去的一個月內,是否存在故意傷害自己,但并不真的希望自己死去?”,將回答“是”判為“陽性”,均納入分析。
1.2.5 普查方法及質量控制 以班級為單位,在班主任的協調下,由受到培訓的該學校老師向學生及學生家長發放知情同意書及進行問卷填寫,填寫完成后當場收回。本次調查所有被調查者均為自愿填寫問卷,由學生和家長簽署知情同意書。本研究獲得蘇州市廣濟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核通過(批準號:2017037)。
1.2.6 統計學方法 調查問卷通過EpiData 3.0建立數據庫,采用SPSS 23.0統計學分析軟件進行數據整理及分析。統計學方法主要采用描述性統計,計數資料主要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主要采用t檢驗,方差分析或者非參數檢驗等,以及Pearson或Spearman相關,Harman單因素檢驗,SPSS宏程序PROCESS 3.5進行中介模型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 由于本研究所有變量的測量均來自被調查者的自我報告,采用Harman單因素檢驗法檢驗共同方法偏差。結果表明,因子分析后得到12個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最大因子方差解釋率為19.2%(小于40%的臨界值)。因此,可以認為此調查結果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人口學特征 普查結果顯示,在11 919份有效問卷中(男生共5 248名),根據“有自傷行為”評定方法,共納入1 482份問卷,陽性檢出率為12.4%,平均年齡(14.96±1.44) 歲,其中,男生為12.3%(644/5 248),女生為12.7%(838/6 671),性別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23,P=0.63)。具體見表1。
2.3 不同人口學特征的心理健康狀態、個性特征差異
2.3.1 不同性別、不同年齡段心理健康狀態、個性特征差異 在心理健康狀態方面,有自傷行為青少年GAD-7均分為(9.37±5.77)分,PHQ-9均分為(11.59±7.14)分,PSQI均分為(7.37±3.28)分,SR均分為(12.17±10.68)分。不同性別的這部分青少年心理健康狀態差異不具有統計學意義。具體而言,在睡眠質量上,以PSQI得分≥8分為睡眠質量問題的標準[14],則存在睡眠質量問題的人數占比為42.5%。MINI自殺篩選問卷中報告有自殺意念者占58.9%,報告有自殺行為者占23.3%。且對比不同年齡段的這部分青少年報告自殺行為時,低齡組(≤15歲)有自傷行為青少年報告出更多的自殺行為(χ2=6.67,P=0.01)。而不同性別GSES、TCSQ積極和消極應對方式評分比較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0.01)。其中,有自傷行為的男生GSES稍高,但低于同一水平的健康青少年男生GSES常模[(2.49±0.54)分][15](t=-3.2,P=0.0014)。與同一水平的健康青少年群體TCSQ常模[積極應對方式、消極應對方式評分分別為(28.88±9.35)分、(23.79±7.00)分][13]相比,有自傷行為的青少年積極應對方式評分無明顯變化(t=-0.60,P=0.55);但消極應對方式評分增加(t=-10.28,P<0.01),且女生往往采用更為消極的應對方式處理生活事件。見表2,表3。

表1 有自傷行為青少年人口學特征及家庭相關因素
2.3.2 不同家庭環境心理健康狀態、個性特征差異 有自傷行為青少年不同戶口、不同居住條件、不同父母受教育水平GSES評分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是否為獨生子女TCSQ消極應對方式評分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父母關系GAD-7、PHQ-9、PSQI、SR、GSES、TCSQ積極應對方式評分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2 不同性別的有自傷行為青少年心理健康狀態和個性特征

表3 不同年齡層自殺意念及自殺行為[n(%)]

表4 不同家庭環境的有自傷行為青少年心理狀態和個性特征
2.4 有自傷行為男、女生心理健康狀態與個性特征及家庭因素的相關分析 相關分析結果顯示,有自傷行為男生的父母關系與其GAD-7、PHQ-9均呈正相關(P<0.01),與其GSES、TCSQ中積極應對方式均呈負相關(P<0.05);有自傷行為男生GSES與SR、TCSQ消極和積極應對方式均呈正相關(P<0.05)。有自傷行為女生的父母關系與其GSES、TCSQ積極應對方式均呈負相關(P<0.01),與其GAD-7、PHQ-9、PSQI、SR、TCSQ消極應對方式均呈正相關(P<0.01);有自傷行為女生的GSES與GAD-7、PHQ-9均呈負相關(P<0.05),與TCSQ積極的應對方式呈正相關(P<0.01)。具體見表5,表6。
2.5 一般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應模型檢驗 根據相關分析矩陣和溫忠麟等[16]研究的中介效應檢驗法,對不同性別的有自傷行為青少年的個性特征與父母關系和自殺風險間進行中介效應模型檢驗。依據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抽取5 000個樣本),以自殺風險為因變量,父母關系為自變量,GSES與積極應對方式為多重中介變量,選擇模型4進行中介效應模型檢驗。模型結構見圖1。中介效應模型檢驗結果顯示,以自殺風險為被測變量,自變量父母關系及中介變量GSES及積極應對方式為預測變量,在不同性別的這部分青少年中預測作用均顯著,但起中介作用的變量不同。男生表現為GSES中介效應Bootstrap 95%置信區間的上下限不包含0,中介效應存在,但中介效應值與總效應及直接效應值均異號,說明GSES在父母關系與自殺風險間發揮遮掩作用,效應量為10.99%。在這部分青少年女生群體中,中介變量積極應對方式在父母關系與自殺風險之間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效應量為7.5%。見表7。

表5 有自傷行為青少年的男生心理健康狀態與個性特征及家庭因素的相關分析(r)

表6 有自傷行為青少年的女生心理健康狀態與個性特征及家庭因素的相關分析(r)

注:*P<0.05,**P<0.01,上述均為標準化后系數

表7 不同性別的有自傷行為青少年個性特征中介效應檢驗
3 討論
在我國中學生心理健康狀況逐年下降的現實背景下[17],本研究發現蘇州市某城區有自傷行為中學生檢出率為12.4%。而我國中西部某地區報告有自傷行為中學生檢出率高達40%[1]。造成明顯差距的原因,分析可能是由于調查過程中選擇測量工具的不同而引起,還可能跟當地的經濟水平以及是否存在較多留守兒童青少年這一社會現象有關。有研究顯示留守兒童的心理問題高于非留守兒童[18]。而本研究中這部分青少年的居住方式主要與父母同居住(92.7%)。
本研究結果顯示,有自傷行為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狀態為中度焦慮抑郁水平,存在睡眠質量問題的占比為42.5%。報告自殺意念者占58.9%,且低齡層(≤15歲)的這部分青少年報告出更多的自殺行為。不同性別的這部分青少年心理健康狀態無差異,而差異主要體現在個性特征方面,即不同性別的有自傷行為青少年的一般自我效能感以及應對方式具有明顯的差異。
本研究結果發現,與國內常模比較,有自傷行為青少年的一般自我效能感普遍降低,負性應對方式增多。一般自我效能感指的是個體面對新環境或應對新事物時所具有的一種總體性自信心[19],既往的研究發現一般自我效能感與抑郁、狀態焦慮、特質焦慮等[20,21]呈負相關,與情緒智力、積極的應對方式呈正相關[22~24]。本研究結果顯示,一般自我效能感的這些相關性主要在有自傷行為青少年女生群體中,與既往的研究發現較一致;但在這部分男生群體中,一般自我效能感僅與自殺風險以及積極和消極的應對方式呈正相關。
在有自傷行為青少年的家庭相關因素中,家庭客觀環境(包括居住條件和方式、獨生子女、戶口等)與心理健康狀態的相關性不強。父母雙方的受教育程度主要影響這部分青少年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值得注意的是,在家庭相關因素中,對有自傷行為青少年心理健康狀態及個性特征影響最廣泛的因素為父母關系和睦程度;它不僅影響這部分青少年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積極的應對方式,也對這部分青少年的焦慮、抑郁情緒以及睡眠質量和自殺風險有影響。且不同性別在三者之間表現出不同的相關性。
在既往自傷行為與精神障礙關系的研究中,青少年自傷行為是將來發生精神障礙的行為標志和風險因素[7]。兒童青少年的自傷行為與情緒障礙[25](包括焦慮癥、抑郁癥、雙相情感障礙等)和外化性行為問題[26](包括注意缺陷多動障礙、品行障礙以及對立違抗性障礙等)均有著密切聯系。雙相情感障礙的青少年群體情緒反應過高或過低,甚至是處于疾病緩解期的個體,可能更容易發生蓄意性自我傷害行為,這可能跟個體的沖動控制能力下降有關[2]。但青少年因出現自傷行為而求助于醫生的人數仍為冰山一角[7],故目前基于學校篩查的有自傷行為青少年群體仍需要進一步更為專業的臨床評估,以明確其能否作為自殺風險的高危人群施行干預,以及明確其精神障礙的發生率。
為考察家庭相關因素與有自傷行為青少年個性特征及心理健康狀態的相關性,本研究還以這部分青少年的父母關系為自變量,自殺風險為因變量,以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積極應對方式為中介變量,構建了中介模型。中介效應分析結果發現,父母關系的和睦程度均可以直接預測有自傷行為青少年的自殺風險水平,但由于一般自我效能感及特質應對方式的性別差異,不同性別的青少年起中介作用的變量又不盡相同。在這部分男生中,由于一般自我效能感的遮掩作用,出現一般自我效能越高自殺風險越高的結果,這似乎有違客觀現象。這種現象被稱為“高于平均水平效應”(Better Than Average Effect, BTAE),在男性群體中是一種廣泛存在的心理現象[27],推測可能與認知偏差有關。而這部分女生中,積極的應對方式在父母關系與自殺風險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總之,父母親之間的關系和睦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有自傷行為青少年的自殺風險,推測父母關系的改善可以降低有自傷行為青少年的自殺風險。但由于個性特征在性別方面的差異,不同性別的這部分青少年在自殺風險影響上有著不同的途徑。故針對有自傷行為青少年心理健康評估及自殺風險的干預,需要根據不同的性別,尋找不同的切入點。同時更需要關注這部分青少年的家庭環境中父母親關系的和睦程度。
本研究因存在一些局限性,目前仍無法形成有自傷行為青少年的家庭相關因素與其個性特征及心理健康狀態之間強有力的證據鏈。分析其原因,首先在于目前研究結果均來源于橫斷面研究方法,且所有評估方法為自評方式進行。其次,由于青少年對自傷及自殺行為的隱藏,風險評估為低風險時并不等同于青少年自殺風險低。故在將來的研究中,需要進一步完善評估內容,并進行縱向研究,隨訪目標人群,從而對有自傷行為的青少年做出更加全面、客觀的評估,指導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