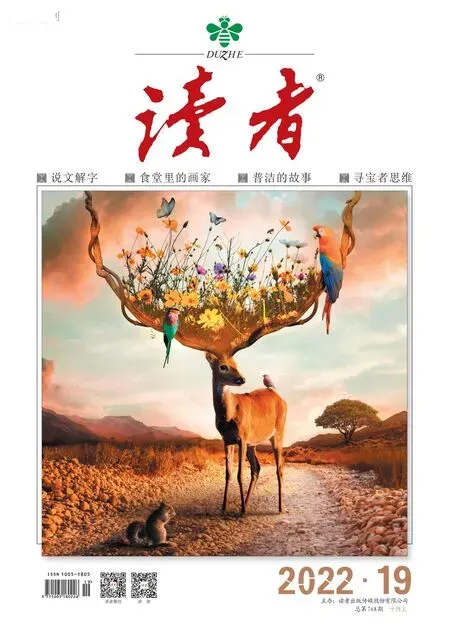一只不抓耗子的貓
☉張 潔
我常對人說,我們家的貓出身于書香門第。這不僅因為它是宗璞同志送給我的,還因為它有書癖。只要書櫥上的玻璃門沒有關嚴,它肯定會跳進去,把每本書挨個兒嗅一遍,好像它能把書里寫的事,嗅個一清二楚。那情景和人在圖書館瀏覽群書,或在新華書店選購圖書沒什么兩樣。
每當我伏案寫作的時候,它不是在我的稿紙上走來走去,便是安靜地蹲在我的稿紙旁,看我寫作。兩個眼珠子隨著我的筆尖移來移去,好像能看懂那些字……直到夜深,它困了,困得直打盹兒,可還是不肯回窩。
它是一只自覺性很差的貓,除了兩次例外的情況,沒有一次按時就寢。一次是吃多了,胃里不舒服,一次是受傷了。
那次受傷全怪我。因為我關門不注意,夾了它的一只前爪,那只爪子腫得很厲害,還流黃水。
我在床上鋪了一張報紙,讓它躺在那張報紙上養息。在這之前,我是不允許它上床的。它很乖,一直恪守這條不成文的規定。
但從此便開了先例,在上午九點到十一點之間,它總要上床睡一覺,我只得每天在床上鋪一張報紙。它很有規矩,從不越過我給它規定的這一方報紙的界限。
應該說,它的記性和悟性都不差。第一次來我家時,一進家門,我只把它在一個裝了煤灰的紙盒子里放了放,它便領悟那是給它準備的廁所,當即舉行了“開幕典禮”。它的下巴齊著紙盒的邊沿,只露出小腦袋和豎著的尾巴,然后神色莊重地撒了第一泡尿。我們被它那專注、嚴肅而又認真的神情逗得哈哈大笑,它卻不為所動,眼睛眨也不眨,依舊瞧著正前方。
以后我注意到,它每每上廁所,都是這副神態。
它還很有好奇心。要是有人敲門,它總是第一個跳到門口去看個究竟。若是我們宰雞,或釘個釘子,或安裝個小玩意兒,它比誰都興奮。
只要紙盒里換了新的煤灰,它準跳進去撒泡尿,哪怕剛剛上過廁所。
家里不論有了什么新東西,它總要上去試一試。有一次,我從櫥柜里找出一個舊網籃,它立即跳進去,臥了臥,將它設為自己的第二公館。
它喜歡把土豆、辣椒、棗子什么的叼進痰盂,或把我們大大小小的毛巾叼進馬桶,然后蹲在痰盂旁或馬桶沿上,腦袋歪來歪去地欣賞自己的杰作。
要是大家都在忙活,沒人注意它,或大家有事出了門,只丟下它自己在家,它便會站在走廊里,一聲接一聲凄涼地嚎叫。
它聽得出家里每個人的腳步聲。盡管我們走路很輕,并且還在門外樓梯上踏步的時候,它便早早守在門旁。它知道玩游戲的時候找誰,吃食的時候找誰,并且像玩雜耍的乞討人,在你面前翻幾個滾。

有時它顯得心浮氣躁,比方逮不著一只飛蛾或蒼蠅的時候,就像那些意識到自己無能的人一樣,神經質地在地上來回扭動,嗓子眼兒里發出一連串痛苦、無奈、帶著顫音的怪叫。
它會一個小時接一個小時地蹲在窗臺上,看窗外的飛鳥、風中抖動的樹葉、院子里嬉戲的孩子、鄰家的一只貓……那時,它甚至顯得憂郁和凄涼……
它的花樣實在太多了,要是你仔細觀察,說不定可以寫出一部小說。
我們都很愛它,要是有人說它長得不好看,那真會傷我們的心。記得有位客人說:“這貓的臉怎么那么黑?”
客人走后,母親翻來覆去地念叨:“誰說我們貓的臉黑!它不過是在哪兒蹭臟了。”于是,母親給它洗澡洗得更勤了,并且更加用力洗它的臉。
逢到我寫作累了,或是心緒不好的時候,我就和它玩上一陣,那是我一心一意、徹徹底底的休息。
但是,它長大了,越來越淘氣,過去我們認為萬無一失的地方,現在都不安全了。而且它鬼得很,看上去睡得沉沉穩穩,可你前腳出門,它后腳就干壞事:咬斷毛線,踹碎瓷器,把眼鏡、筆、手表、鑰匙不知叼到什么地方去,害得你一通好找,或是在我那唯恐別人亂動的書桌上馳騁一番……然而,只要一聽見我們的腳步聲,它便立刻回到窩里,沒事人兒似的假寐起來。
我們就說:“這貓太鬧了,非把它送人不可。”
不過我們說說而已,并不當真。最后促使我下決心把它送走的原因,是它咬碎了一份我沒留底稿的文章。再加上天氣漸漸熱了,一進我們家的門,就能嗅到貓屎、貓尿味兒。還有,給貓吃的魚難買。于是我們決定把它送給鄰居。
它像有第六感,知道大難臨頭,不知躲進哪個旮旯兒,怎么找也找不到。我把眾人請出屋子,因為它平時最聽我的招呼。費了好大勁兒,終于把它引了出來。
母親說:“給它洗個澡再送走吧,它又蹭黑了。”那幾天,母親的血壓又上去了,沒事待著頭都暈。
我說:“您歇會兒吧,這又不是聘閨女。”
它走了,連它的窩、它的廁所,一起搬走了。
屋里安靜了,所有怕碰、怕磕、怕撕的東西,全都安全地待在它們該待的地方,然而我們都感到缺了點兒什么。
那一整天,我心里都很不是滋味。老在想,它相信我,超過了相信自己絕對可靠的直覺,由于感情用事放棄了警覺,以為我招呼它,是要和它玩耍。當它滿心歡喜地撲向我時,我卻把它送走了。
我嘗到了一點兒“出賣”他人的滋味。
欺騙一只不知奸詐的動物,就跟欺負一個天真、輕信的兒童一樣,讓人感到罪過。
第二天一早,母親終于耐不住了,去鄰居家看看情況如何。鄰居抱怨說,一進他們家,它就不見了。一點兒動靜也沒有,已經二十四小時沒吃沒喝、沒拉屎沒撒尿了。
可它聽見母親說話的聲音,立刻從遁身之處鉆了出來。母親抱住它,心疼地說:“我們不給了。”
鄰居大概也看出來這是一只難對付的貓,巴不得快點兒卸下這個包袱。
母親抱著它和它的窩、它的廁所又回來了。一進家門,它先拉了一泡屎,又撒了一泡尿,依舊神色莊重,依舊在眾目睽睽之下。
然后它在沙發上、床上、書桌上、柜子上,跳上跳下,猛一通瘋跑,顯出久別重逢后的興奮和喜悅。母親一面給它煮魚,一面叨叨:“他們連人都喂不好,還能喂好貓?以后就是送人,也得找一家疼貓的。”
現在,七十多歲的母親,依舊為給貓買魚而四處奔波,我們家里依舊有一股貓屎、貓尿的臊味兒和煮魚的臭味兒。而且這次懲罰,并未對它起到什么教育作用,它依舊不斷惹我們生氣,生氣之后我們還是會說:“這貓太鬧了,非把它送人不可。”
可我知道,除非它自己不愿在我們家待下去,不然,它一定會老死在我們家。
(楊賀勤摘自人民文學出版社《我那風姿綽約的夜晚》一書,本刊節選,陳 曦 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