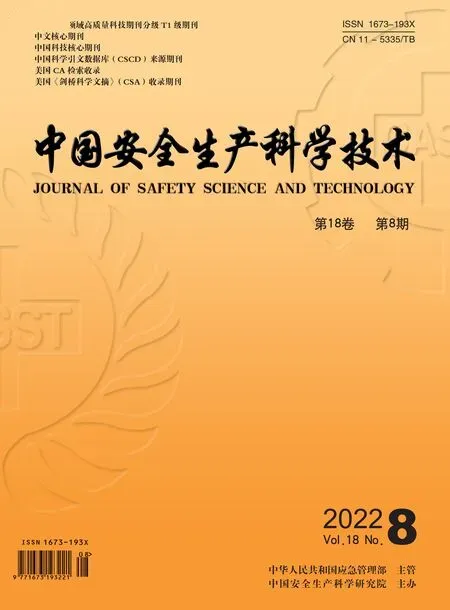基于風險評價的核應急分區疏散規劃*
謝秉磊,毛明珠,2,趙金秋
(1.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 建筑學院,廣東 深圳 518000;2.常熟市交通運輸應急指揮中心,江蘇 常熟 215500)
0 引言
我國能源需求量巨大,傳統能源已經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和愈發嚴格的環保要求,發展核電成為必然趨勢。在核電設施快速發展同時,核事故災難預防和應對,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1979年美國“三里島核事故”、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以及2011年發生的“日本福島核事故”[1-3],給人們生命財產安全造成的損失不可估量。我國始終將核安全放在核事業發展首要位置[4],強調核應急是確保核安全的最后屏障。
核事故應急疏散是最常見的應急措施之一,按啟動模式可分為整體疏散和分區疏散。整體疏散是指同時向應急計劃區發布疏散命令,疏散需求呈多點迸發式加載;分區疏散,也稱分階段疏散,是事先將疏散人員按區域分組,按照緊急或危險程度安排各分區按順序啟動疏散的組織策略。我國核電站大部分建于沿海地區,在沿海經濟發展和核電站區域經濟促進的雙重作用下,核應急計劃區內人口持續增長。大規模人員的整體疏散會導致道路擁堵,使核心區域人員滯留在高輻射風險區域,缺乏時效性和安全性,儲備物資和應急人員數量無法在短時間內滿足需求。同時,核事故風險在一定條件下具有可傳遞性,發生核泄漏或核爆炸事故時,高風險人員由于吸入過量輻射物質或衣物沾染核物質,導致其成為類輻射源,混合運輸高、低風險人員,可能會導致輻射二次傳播。分區疏散可有效緩解疏散擁堵問題,提高疏散效率,保證高風險區域人員的優先疏散,避免高、低輻射人員間的輻射傳播。
目前,針對分區疏散的研究體系尚不成熟:Liu[5]基于元胞傳輸模型對分階段疏散過程展開研究,確定各疏散階段最佳啟動時間;Chen等[6]采用基于Agent的仿真方法,研究同時疏散和分階段疏散策略的有效性,并使用Paramics微觀模擬系統,對不同人口密度下的3種路網結構進行模擬;Li等[7]建立雙層隨機規劃模型,評估應急疏散流量相關潛在規劃風險,以確定最佳分階段緊急疏散計劃;華東師范大學地理信息科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8]提出1種創新方法,用以制定分階段應急疏散計劃,利用算法調度每個疏散組的啟動時間。現有研究以理論模型為主,旨在建立時間窗口完成分階段疏散工作,忽略空間維度劃分在提高疏散效率和保障疏散安全方面的積極作用。疏散區域劃分方法較少,且缺乏結合事故特征的定量化分區方法,對制定實際疏散方案的指導十分有限。
《核電廠應急計劃與準備準則 第1部分:應急計劃區的劃分》(GB/T 17680.1—2008)[9]將核反應堆10 km范圍內區域定義為核事故煙羽應急計劃區,本文將基于該區域開展。相較于核電站場內疏散,場外人員規模相對較大,不確定性較強,疏散組織難度更大,因此,本文將其作為主要研究對象。
1 基于風險評價的分區方法
1.1 風險評價
核事故應急場景下的主要風險因素為核輻射暴露風險[10],表示人在無防護措施情況下,暴露在核輻射環境期間所承受的輻射傷害風險。本文將核輻射濃度作為暴露風險的空間量化指標,體現應急計劃區內各集中點和不同路段的風險差異,并結合疏散時間,對暴露風險進行時空量化,最終得到核應急疏散總暴露風險。
典型的核輻射擴散模型有高斯煙羽模型、拉格朗日模型、三維模型和煙團模型等[11-12]。本文研究事故源點10 km范圍區域,屬于中小尺度擴散問題,因此采用高斯煙羽模型對核物質擴散情況進行分析。考慮在未知事故數據和場景數據情況下,評價不同位置核輻射風險參考高斯公式法[13],計算場外應急計劃區內各點核輻射相對濃度和風險值,如式(1)~(2)所示:
(1)
fvi=kdC(R,t)
(2)
式中:C(R,t)指t時刻與事故點距離R的評價點vi的核輻射濃度,m-3;Kr,Kz分別為徑向擴散系數和垂直擴散系數,分別取值3.6×108,1.8×104m2/h;zc為計算濃度點的高度,m;fvi是評價點vi的風險值,m-3;kd表示決策系數,取決于決策者態度,保守的決策者往往會選擇更大的決策系數,以充分考慮核輻射風險,激進型決策者會弱化風險,做出以時間效益為主要導向的決策。
在路段風險評價方面,取路段兩端點作為路段風險評價點,以端點平均風險值作為路段時空暴露風險值,用于指導疏散路徑規劃,追求最小化疏散風險。
風險評價目的是確定疏散路網中各點或路段的相對風險程度,指導公眾選擇風險較低的路徑進行疏散。為更好地評價各點間相對風險,對風險值進行歸一化處理,將絕對風險轉換為相對風險,映射為[Δf,1+Δf]范圍內的無量綱值,如式(3)所示:
(3)
式中:fmin,fmax是評價點中的風險最小值和最大值;Δf為歸一化修正系數,用以保證在路段風險值差距較小的情況下,模型能選擇風險較低的路段疏散,提高模型優化效率。
1.2 分區方法與疏散優先級
文獻[14-15]設置5 km范圍內區域作為核事故應急疏散區,并同時組織整個區域的公眾撤離。現有核應急疏散分區方法比較粗糙,未結合實際事故場景,參考其他事故疏散分區方案,核應急疏散分區不應局限于傳統方法:Hasan等[16]將疏散分區定義為來自同一居住區的疏散人員,并分配單一路線疏散;黃靜等[17]應用GIS技術分析應急疏散需求分布、疏散空間可達性以及疏散優化歸屬等疏散特征,最后以社區為基礎,劃分居民避震疏散區。
疏散策略的可操作性是比較重要的評價因素之一[18],應急狀態下的疏散組織比較困難。作為城市行政單元,行政區是疏散規劃中可操作性較強的區劃單元[19]。因此,本文將行政區劃法和風險評價結果相結合。首先,使用行政區劃法對疏散區域進行初次劃分,以便于政府組織公眾疏散,降低疏散混亂程度。考慮到各行政區疏散需求量和集中點數量過多,為保證分區疏散效果,減少輻射二次傳播風險,對行政區進行二次劃分。完整的分區包括以下3個流程:
1)參考核應急管理體系中政府組織管理的行政區劃,或規劃與自然資源局給出的行政區劃,對核應急計劃區場外部分進行劃分,并隨機編號為Ⅰ,Ⅱ,Ⅲ,Ⅳ,…。
2)根據風險評價方法,計算集中點相對風險指數,針對各分區集中點按照風險值進行排序,據此對行政分區進行二次劃分。例如,以分區Ⅰ中風險排序50%作為分隔位,將分區Ⅰ劃分為2個新分區。考慮到分區數量過多不利于疏散組織,一般不直接以單個集中點作為最終分區結果。
3)獲得最終疏散分區方案,分區風險取分區內集中點風險的平均值,并將分區z(z=1,2,3,…)按風險排序進行編號。風險排序越靠前,疏散優先級越高。
2 分區疏散路徑規劃
元胞傳輸模型(Cell Transmission Model,CTM)可以模擬動態交通流,再現真實路網時空狀態。本文將充分考慮疏散路網和核事故疏散時間限制,以動態網絡流為基礎,構建基于元胞傳輸理論的分區疏散路徑規劃模型。
2.1 疏散總暴露風險
在突發事件應急情景下,疏散路徑規劃主要目的是減少疏散時間。分區疏散中的疏散時間由行駛時間和等待時間組成[20],如式(4)所示:
(4)

本文以路段疏散行駛時間與路段輻射暴露風險值的乘積表示暴露風險,并將其作為疏散效率評價指標,指導路徑規劃。分區z總暴露風險如式(5)所示:
(5)

2.2 模型假設
核應急疏散是較為復雜的應急響應行為,疏散前期、中期和后期均涉及組織優化。為突出本文研究重點,將基于以下2種假設條件構建模型:不考慮疏散車輛的前期調配工作;場外疏散需求數量及分布已知。
2.3 基于CTM的分區疏散路徑規劃模型
為確定各集中點人員的最優疏散路徑方案,本文以系統最優為原則,最小化總疏散效用為目標,構建基于CTM的分區疏散路徑規劃模型。目標函數如式(6)所示:
(6)

終點元胞表示1個虛擬的安全點,到達該點的人員可視為已完成疏散,在計算總疏散效用時不考慮終點元胞的疏散效用值。模型約束條件如式(7)~(19)所示: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式(7)~(9)依次為疏散路網中普通元胞、終點元胞以及源元胞的流量守恒約束條件,以保證t時刻路段車輛數為t-1時刻車輛數與流入元胞車輛數之和再減去t時刻流出元胞的車輛數;式(10)~(11)是對流入、流出車輛數的限制;式(12)是對連接器通行能力的約束,限制其不能大于連接器上游元胞的可發送能力,且不大于下游元胞的最大接受能力;式(13)表示t時刻疏散路網中全部車輛數等于截止t-1時刻加載到源元胞中的疏散需求;式(14)~(15)是對路網元胞和連接器的非負約束;式(16)~(17)為初始化約束;式(18)表示設置源元胞的流入車輛限制等于疏散需求加載值;式(19)表示源元胞和終點元胞的可容納車輛數為無窮大,集中點和終點無容量限制。
路徑規劃模型求解實質屬于整數線性規劃問題,規模是決定求解難度的主要因素。核事故的突發性和災難性對應急響應速度要求較高,模型求解速度也是考量其優劣性的重要評價指標。因此,在滿足求解規模和速度前提下,本文采用Python語言搭建疏散路網及基本框架,使用Gurobi求解器進行優化求解,獲得疏散路徑規劃方案。
3 案例分析
3.1 疏散場景描述
案例共32個集中疏散點,隸屬于5個行政區。核輻射物質擴散與風向、風速等氣候條件密切相關,晝夜疏散需求差異較大[21]。因此,本文做出以下假設:核事故達到場外應急等級且發生在旅游旺季晝間;疏散人員嚴格遵守分區疏散規劃,不存在非計劃疏散。
3.2 分區疏散方案設計
本文采用“政府組織疏散+私家車自行疏散”的組合疏散模式,疏散交通工具由自行疏散的小汽車和政府組織疏散的公交車或大巴車組成。參考現有研究中最佳比例[22],本文將小汽車和大巴車的數量比例設置為6∶4。
本文采用綜合分區法,首先按行政區劃法對場外疏散區域進行初步劃分,得到行政分區Ⅰ~Ⅴ,如圖1所示。本文事故風向為正南方向,按照風向對研究區域進行風險等級劃分,由圖1可知,不規則區域為行政分區Ⅰ~Ⅴ;區域1-1~1-3為核輻射風險最高的下風向區域,扇形區塊風險向兩側遞減;區域2-1~2-7風險等級次之,屬于煙羽內區;3-1~3-7為第3風險等級區域,屬于煙羽外區。考慮到疏散需求和集中點數量較多,基于風險評價結果,對行政區Ⅱ~Ⅴ進行二次劃分,假設在各行政區風險排序50%處進行劃分。由于同一集中點人員不能屬于多個分區,Ⅱ區取排序前3的集中點構成分區8,最終得到9個疏散分區。

注:不規則區域為行政分區Ⅰ~Ⅴ;1-1~1-3區域為風險1級,2-1~2-7區域為風險2級,3-1~3-7為風險3級圖1 核電站場外疏散區行政區劃Fig.1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f off-site evacuation zone of nuclear power plant
本文將采用上文所述風險評價方法,參考疏散起始時間的核輻射濃度,計算輻射風險值和相對風險指數。其中,風險決策系數kd取1×1012,歸一化修正系數Δf取0.1。具體分區結果和集中點相對風險指數見表1。

表1 疏散分區及需求分布Table 1 Evacuation zones and demand distribution
3.3 仿真與模型求解


表2 分區疏散模型求解結果Table 2 Solving results of zoning evacuation model
最后對比2種方案的疏散效果,2種方案下疏散時間指標見表3,方案具體評價內容見疏散方案評價章節。表3中疏散時間包括疏散行駛時間和等待時間,而分區和整體疏散時間則對應分區內集中點疏散時間最大值。對比表3中數據可以發現,分區疏散策略顯著縮短疏散時間,最大優化比例達82.91%,雖然疏散等待時間的疊加,導致部分風險較低的分區疏散時間增加,但應急計劃區總疏散時間始終呈下降趨勢。

表3 整體與分區疏散時間Table 3 Entire and zoning evacuation time
4 疏散方案評價
1)疏散時間與總暴露風險
整體與分區疏散交通狀況如圖2所示。由圖2 可知,整體疏散最大疏散時間達到62.82 min,分區疏散最長時間為38.00 min,較整體疏散下降39.51%。風險排序前3個分區疏散時間明顯縮短,分區1疏散時間下降30.20%。部分分區疏散時間較整體疏散方案有所增加,這是由于疏散等待時間的疊加,導致部分分區疏散時間增加。但分區疏散總疏散時間更短,尤其大幅度縮短高風險區域人員疏散時間,保障疏散安全。基于風險評價結果和疏散時間,計算整體疏散和分區疏散總暴露風險分別為2.694×109,2.325×109(輛·min)。結果顯示,分區疏散較整體疏散的總暴露風險降低13.7%。總的來說,分區疏散在疏散時間和疏散總暴露風險方面,均優于整體疏散。

圖2 整體與分區疏散交通狀況Fig.2 Traffic conditions of entire and zoning evacuation
2)疏散交通狀況分析
為更直觀地對比整體疏散和分區疏散方案下的疏散交通狀況,利用TransCAD對2種方案進行仿真模擬,得到2點結論:整體疏散模式下,主要疏散路段擁堵嚴重,飽和度高達2.18,交通幾乎處于癱瘓狀態;部分人員被阻塞在高風險區,增大公眾的疏散風險。
相較于整體疏散,分區疏散時路網更加通暢,交通擁堵現象局部短暫出現,主要疏散道路飽和度峰值下降到1.38。分區疏散使得需求分階段加載,緩解道路擁堵問題,同時解決高風險區域人員滯留問題,最大程度地保障公眾安全。
5 結論
1)相較于整體疏散,分區疏散優化疏散需求加載過程,特別是我國人口基數較大,疏散效果顯著。當核事故較為嚴重,核心區域人員對疏散時間要求較高,分區疏散能優化資源分配,在保證疏散區最低疏散時間下,盡量將資源優先提供給疏散優先級更高區域的人員,并針對不同分區特征,設計配套疏散組織與管理方案。
2)提出的基于風險評價的綜合分區方法和分區疏散路徑規劃模型,有效縮短應急計劃區總疏散時間和降低總暴露風險,大幅度減少高風險級別分區疏散時間,對于我國核事故應急體系建設具有一定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