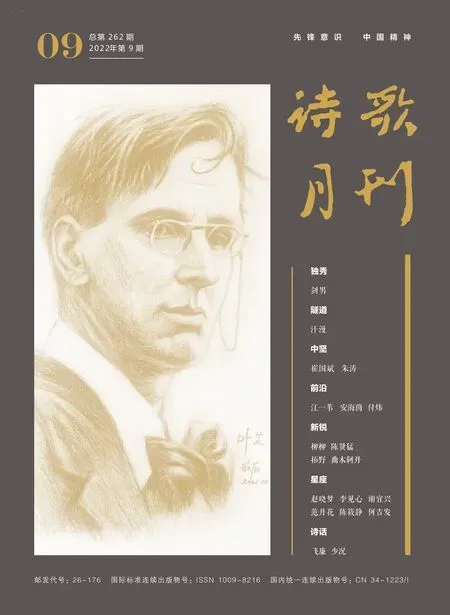缺席者的自我(組詩)
崔國斌
岸上:一個地址
許多詩詞里,都有“岸上”。這一點
啟發了我。景致一旦按心情劃分
就不再是景致。它是讀后感的一部分:
想象一下,才能看見。如同往事
讓我又老了一歲。欣賞過的詩詞
經歷了遺忘。記住的,是其中的自己
如果換一種說法,就叫自我虛構
最早靠死記硬背,后來在遺忘中完成
如今,“岸上”已是我的地址
當年的背誦,讓我赴約。而重溫
拒絕聲音的期限。而望上一眼
終點就有了名義。它屬于斷言
通過朗讀,把古人的地址
抄進腦海。但那些時刻,我不知
從何談起。我會根據日歷喝茶
數心中的漣漪,與詩句建立聯系
我其實是記憶力不好的讀者
能做到的就是混淆,將這句與那句
錯配成另一種意思。我終于
懂得了“岸上”:他們的地址
也是我的。這不是爭奪,而是
我常常用到它——
或不露聲色地等人
或在眾多的意象里找回自己
論時間
太晚了。只是多坐了一會兒
便難以自拔。有惰性的人
膠水附身,重力來自天賦
但我不會記住自己:適應性
給我帶來重生。空地作為
一種跡象,繼續空著。直到
開滿鮮花,才似曾相識
這將夸大覆蓋的作用,而無論
什么地方,都將長出植物
它等候的狀態,在發光的瞬間
統計灰塵。但時間的登記表
不接納影子,也不許填寫
信心或迷茫。“相信你!”
就是一道命令。邏輯環環相扣
懷疑得不出結論。匿名的樹
因長出新葉,而被認出
缺席者的自我
別針上,一個遁詞。兩個故事
從描述講起,最后改變人稱
講自己不可更改的過去
必要的轉折,讓另一個軼事
進入隱藏的主題。他就此
大談修辭,談得令人吃驚
而停頓,也是言語的一部分
也要記錄,并在此處給予
恰當的回聲。一個更早的自己
敗給瞬間,不知道怎么回頭
正如失誤一言為定。所謂更正
只是一個午后,來自相遇的
期許。當微笑被看成挑戰:
不錯,它就是挑戰。只不過
它弄錯了日期,撕毀了一份
與忐忑達成的協議。它混淆的
視覺,帶著季節的風聲
往心里補充情誼。誰也攔不住
碰撞,以逃逸的名義發生
而勇敢之所以稱之為勇敢
在于能夠停留,像平常那樣
擺正自己。心里的遙遠
既然看得見,就要去凝視
這不是重復某種好奇,也不是
為了抵達,而是為了存放
那掩飾之下的自己

有聲詩歌
它是一個盡頭
用傲慢的神態比直接用貶義詞
更加傷人。我自己也一樣
用不同的角色迷惑自己
當火車開出早晨的視線,我們
坐下來,看河邊的夕陽
恍然大悟。這是留存于世的腳本
目光被色調改變。風吹向
尚存的邊界,無法收回
當它停止,就是唯一的地方
而所謂以前,只是經過。至今
我不知道一分為二的思維
怎么運用。鮮明的句子寫滿
整頁,其中只是假設
沒有承認。回旋的余地
也要構思。我一次次寫信
在夜晚,做收音機的聽眾
我的習慣,就是把同一個問題
在大腦里拋來拋去
從四月起……
下午,山水忽遠忽近。天氣采取這種形式
讓我變樣。半邊街,每天重新開張
它提供過去:遙遠的場景
荒涼已不夠用。現在,這里即將下雨
放走徜徉的人群。人們接著相信
明天就是四月的開頭。事實上,的確如此
而且這一天將迎來農歷的三月
而且,冬天的印象,將與它一并加深:
那時,我不會拒絕,因為我不懂。詞匯表
也沒有準備就緒。但我是那么敏銳
用臨時的表情,回應紫羅蘭的推論
當一切都已過去,我將用零碎的時間
整理風雨。微笑的保安員,“小心臺階”的
逐級提示牌,以及三樓紅色的消防栓
讓沿途的老路再一次翻新。我用幾何圖形
藏書,聽取窗外的意見。定時的微風
被談論成假設,什么都難以斷定
是的,斷定:也許更像猜測,易于牢記
經驗教給我們的歧義。人都在乎自己
在他人眼里的重要性,但我最終
用距離改變了自己。在追憶的邊緣
只有回頭,才能識破一重關系
解除另一重關系。我承認我的糊涂
用一次慰問的經歷瓦解自己
讓揭曉謎底的方式,抱著一個約定
過去,就是這樣:匿名的人,曾把各種念頭
寫進不同的文體,慢慢屈服于責任的含義
而耐心,反復失效。這正是我所想的:
真實不是來自凝視,而是因為更多的混淆
我重返市中心,形式多樣的路上
不再有我。我在陽光下尋覓雨水的弧線
在另一個地點現身:像一次失而復得
或者,只是我想象如此。不斷變換的身份
不是自己與自己的區別,而是一個詞
覆蓋另一個詞,適應身份的突變
——幾十年了,經過的地點,被我放在一起
置疑人生的漫長。當櫻花在梧桐樹下
以怒放呼應新葉,披頭散發的垂槐
也將回到它帶葉子的模樣。交換的存在
無須區分:我正是為此而來
清晨
一
清晨,我被信賴。任務是,替妻子去一趟
房產證上的家。新撒的種子在后院
想舉手發言。我要用一場雨,去傾聽
從南一環,向東。我目睹日出
交通臺的播報伴著我,行駛懷舊的里程
設卡的路口:空空。疫情防控人員
從帳篷里突然跑出,把我關進他的眼睛
二維碼矩陣,掌握著我的多重秘密。
它用綠色恢復了我到達目的地的慣性
二
后院的土壤有礦化的質地。它終于可以
憑自己的興趣,背誦重新整理的篇章
而我的晨讀,則是一次比較。往表象的頁面
添加決定,翻動已有的伏筆
品種不同的梅花,都過了花期,只有烏梅
與石榴同步吐葉:像宣誓的拳頭
迎接著晨曦。被挪了幾次的映山紅
在用它的學名開花,把假山選進自己的意境
高矮不一的茶花,像安插在院中的
偵探,站著失眠。而獨立的桂花樹一再
朝地上扔葉子,我多么盼望它
盡快修復去冬的傷情。其實,映山紅
也曾用枯萎制止我打它的主意
當我們都停下來,正如石頭的氣質
在于擺放。而不是蓄意的指定。
三
我走進院落。用炊煙的一幕收回自己
我曾一遍遍畫過示意圖,給花草樹木標上
具體的位置。我想,要去別處挖它們
就要在自己的情景里,先愛上它們。
現在,它們都來到了這里
在雨水里放棄一次過去。
分開栽種的兩株銀杏,遲疑地復蘇。它們把
鮮綠的小葉子運往空中,讓陽光就近閱讀。
——這是我的遠景:葉子借著上方的光
消失于我的仰視
當草木在雨水中起立,重拾蔥蘢的臺詞
“香水貴妃”卻在焦慮中,書寫曲折的紀事
新植的紅花玉蘭,并不介意先來后到
而芍藥與草坪卻仿佛重生
唯有靠邊的橘樹,在原貌中
悄悄生長,但它又不同于附近的矮松
保持造型的特征
四
溺愛的言詞讓事物煥然一新
這是改寫。換個角度,就可以愛它們
匍匐的青蓼,露出溜走的企圖
也可能帶有渙散的目的。而低矮的黃菊花
一叢叢,守著自己小小的天地。
至于茶花,它一直用密實的樹葉抱緊自己
越是拍打,就抱得越緊
紅花玉蘭與其中的一株離得很近
它伸張的枝丫,讓人想到歡迎儀式
它們從不模仿。擁擠也改變不了
彼此。一群鳥,嘰嘰喳喳,棲落玉蘭的枝頭
似乎在召開以菜地為天空的會議
五
是澆水的時候了。我看了看手表里的清晨
整飭一新的菜地撕下昨天的日歷
它曾隨著圖紙改來改去,如今總算
有了持久的樣子
試種的萵筍和菠菜,獻出遲到的收獲。
像一個舊夢,抓住想要的名字
一束被妻子執意鏟掉的小蔥,努力翻身
最終還是放棄了倒立。
澆水:往土里灌輸種子的漫談
一小時后,我將在另一個方向上班
種子的語言會讓我過目不忘
* 借用特朗斯特羅姆“把他關入眼睛的檢疫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