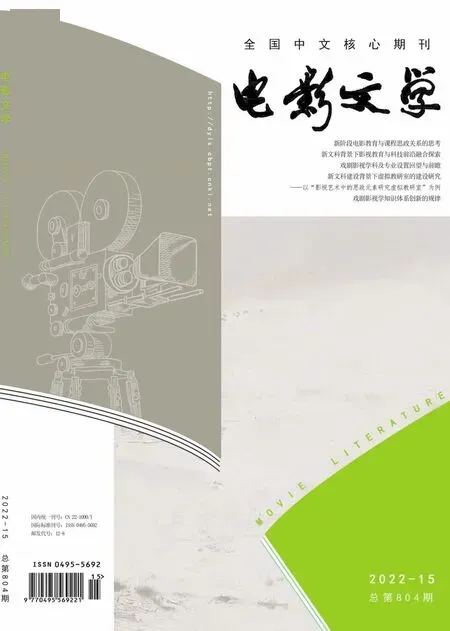論當代國產喜劇主體性與人文精神的復歸
王秀麗
(平頂山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河南 平頂山 467000)
長期以來,喜劇電影都是觀眾最喜聞樂見的類型片之一。如果對當代國產喜劇片的發展稍做梳理,便不難發現,其在約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由于大量跟風“馮氏喜劇”“寧氏喜劇”電影的出現,部分作品暴露出了一定的喪失主體性,人文關懷缺席的問題,電影整體上顯得乏善可陳,也影響了觀眾對整個喜劇類型片的消費傾向。而電影人也迅速在這方面進行調整,以統一電影的娛樂屬性與人文精神,提升電影的藝術品質。在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國產喜劇片的整體面貌有所改觀。應該說,消費時代下,這種類型片的自我糾偏,創作環境的自我凈化是可喜的,也是值得我們加以總結的。
一、批判現實主義與后現代主義中的國產喜劇片
在談及當代國產喜劇片就主體性與人文精神表達方面的轉變之前,我們有必要對當代國產喜劇片的兩大文化背景稍做梳理。
盡管自先秦以來的中國正統文化并不高揚喜劇精神,超越現世苦難,享受生命快樂依然是國人不可磨滅的內心需求。這也就使得在電影藝術進入中國后,人們就有了拍攝與欣賞喜劇電影的需要,早在1922年,上海明星影片股份公司就推出了《勞工之愛情》,這可以視為是我國喜劇電影的發軔之作。其時“諷刺批判精神的張揚則是現代喜劇史上最為亮麗的風景,這有深刻的現實政治與文化語境因素”,當時籠罩于中國的黑暗時代陰影,以及根深蒂固的“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藝術傳統,使得人們在拍攝喜劇時,也是直面社會矛盾,表達對舊思想的懷疑與批判的。一百年來,盡管時代變遷,國運更易,但電影人在喜劇中關注、批判和改造現實的主觀努力都是清晰可辨的。如20世紀50年代呂班諷刺不良現象的《新局長到來之前》中,牛科長是典型的只顧溜須拍馬,不惜為討好新局長而大肆鋪張浪費,而對普通職工的生活困難不聞不問的官僚,他的作風最終也為新局長所不齒;在王家乙的《五朵金花》中,白族青年阿鵬尋找自己意中人“金花”的過程,恰恰也是電影展現云南地區煉鋼煉鐵、拖拉機生產、畜牧業等各項熱火朝天事業的過程。在這一類喜劇中,觀眾不難看出電影人無論對現實秉持的態度是贊譽抑或諷刺,他們都對現實傾注了最大的熱情。
在20世紀90年代,隨著電影產業化的進一步成熟,“賀歲檔”等概念應運而生,人們逐漸建立起于特定檔期觀看喜劇電影的消費習慣,這一時期屢屢獲得票房成功的馮氏喜劇,也都是立足于現實的。《甲方乙方》中,姚遠等“好夢一日游”的員工們致力于幫書店老板、川菜廚子等人短暫地營造“夢境”;《不見不散》聚焦的則是漂在美國的中國人的生活;《沒完沒了》中主人公則是被欠薪所困而不惜綁架他人的大巴車司機。其后如寧浩的“瘋狂”系列等,更是體現著“草根式”小人物的生活悲辛和生存智慧。《瘋狂的石頭》中包世宏等人面對的是工資被拖欠,工廠要被地產商兼并的困境;《瘋狂的賽車》中人們則道德滑坡,丈夫不惜雇兇殺妻,毒販喪心病狂,農民也為換婚鋌而走險當上殺手。喜劇碎片最終拼湊成沉重的,引起觀眾共鳴的民生現實。
而另一方面,當代國產喜劇又深受后現代主義的影響。誕生于20世紀60年代,并迅速影響了文學藝術以及商品消費的后現代主義有著去中心、多元論,以及消解元敘事的文化特征,其也影響著中國的喜劇電影創作,讓國產喜劇出現了有別于《五朵金花》《父子老爺車》甚至《沒事偷著樂》時代的“強調消費性能指,盡量滿足觀眾的視聽快感,稀釋人文內涵,填平美學深度,疏離權力話語”的面貌。如在《人在囧途之泰囧》中,觀眾忽視了“油霸”概念的不合理性,以及王寶去泰國動機的牽強,而被王寶和徐朗在異國他鄉一個緊接一個的狀況吸引了注意力,為主人公的狼狽而開懷大笑。相對于此前涉及農民工討薪的《人在囧途》,電影人有意讓電影的崇高感和使命感淡出,而是盡可以讓觀眾進入一場異彩紛呈的游戲之中。與之類似的還有如敘事起點都高度脫離現實(神奇手機與“分歧終端機”),滿足了男性觀眾女色凝視欲望的《愛情呼叫轉移》《非誠勿擾》等。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觀眾擺脫現實重壓,暫時進入一個另類時空的消費需求,文化的經濟意義得以實現,如《泰囧》就曾創下昔年令人驚嘆的12億元票房紀錄。
但對后現代主義精神的盲目追求,其負面影響也是十分明顯的,正如學者指出的那樣:“所謂凸顯平面模式、生命本能,以及深度意義、歷史記憶、主體意識的消失等,都是從一種解構的視角來看待當今的電影文化的。”受后現代主義影響的喜劇電影在質量上良莠不齊,而其中劣者的缺陷就在于只有解構而沒有建構,這正如人們只拆除了舊房卻不再搭建新房,其最終結果便是人無處棲居,人的精神無處安頓,喜劇電影中主體性的失落由此日益明顯。
二、主體性的失落與重建
“主體性思想源于古希臘哲學,在‘人是萬物的尺度’命題的啟發下,蘇格拉底又提出了一個嶄新的哲學命題:‘認識你自己’,他從萬物之中抽取出‘自己’,即‘人’。”隨著人類在實踐活動中對自然的認識與征服,人們的自我意識也漸漸覺醒,隨即人的中心位置,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作用成為共識。在藝術創作中,主體性則體現為創作者本人的身份意識,包括其獨一無二的認知結構、文化修養、道德標準與審美取向,以及其作為個體對其他個體的情感和態度。中國電影長期以來都是屬于“精英”的“獨白”,其主體性是一直未缺席的,如“第五代”導演張藝謀、陳凱歌等人便被認為是執著于書寫民族文化心理,矚目于傳統文化者,其作品帶有某種與歷史和民族緊密相關的厚重感,導演本人作為知識分子的啟蒙意識在其中清晰可辨;而“第六代”導演如賈樟柯、管虎等人與前輩們略有不同,他們是以展現同樣是有一定文化的年輕人的個人生活空間和精神世界登上影壇的。兩代電影人展現了或是屬于群體的,或是屬于個體的主體性,而殊途同歸的是都進行著嚴肅性的,幾乎不妥協于市場的話語陳說。而在“第六代”后從事喜劇創作的電影人,則處于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大眾接觸電影的門檻進一步降低,隨之而來的便是語言狂歡,游戲敘事和低俗審美對電影“精英”性的剝蝕。
在談及當代流行的“大話文學”時,有學者對充斥于其中,被廣為追捧的游戲、戲說態度進行了批判,認為在當下,“這種叛逆精神或懷疑精神采取了后現代式的自我解構方式,由于沒有正面的價值與理想的支撐,因而很容易轉向批判與顛覆的反面,一種虛無主義與犬儒主義式的人生態度”。而這一觀點之于對當代國產喜劇的批評也是適用的。毋庸諱言的是,在新世紀的前十年左右,一批喜劇電影暴露出了放棄考問心靈,規避現實矛盾的特質,這一類電影中不乏解構、戲仿和惡搞手段,但其目的僅僅是為了暫時性地取悅觀眾,而非進行某種文化抵抗或深度思考,影片從整體上給人以強烈的虛無主義和主體失落感,觀眾無法從中分辨出創作者的面目,也不會因電影而生出長久的記憶與回甘。例如在周星馳解構《西游記》拍攝了經典之作《大話西游之月光寶盒》之后,《越光寶盒》則又對周的電影進行了解構,電影中同樣有紫霞仙子、紫青寶劍等元素,越光寶盒也有著和月光寶盒一樣的讓人穿越時空的法力,同時又套用了《三國演義》中的赤壁故事,只是將曹操、劉備等人的形象完全改寫。如曹操請出自周星馳《功夫》里總是講“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火云邪神前去刺殺劉備,不料火云邪神一槍打死了華佗等,觀眾固然會對名著和周星馳電影中的人物被調侃而感到有趣,但卻不能在其中發現任何文化價值。電影在對舊的偶像和話語進行拆解之后,既沒有保留國產喜劇的批判現實主義美學特質,又沒有提出新的理念,沒有建構起超越娛樂性的正面意義。與之類似的還有讓人物操持各地方言的《十全九美》,讓隋朝人物掉入冰川冰封千余年后來到現代社會鬧出種種笑話的《隋朝來客》,戲仿了金庸武俠小說的《大笑江湖》等,它們與觀眾的現實生活是有一定距離的,并且“不再像中國傳統的喜劇電影那樣,直面尖銳的社會難題并予以反諷與揭露,而是運用一些無關痛癢的、無害的影像符號不斷消解這種文化對抗性,并拒絕創造新的價值符號體系”。
這一類喜劇片在票房與口碑上的不盡如人意很快便讓電影人意識到了改易創作思路,回歸表達個人觀察與思考的必要性,自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后,國產喜劇片的主體性又逐漸鮮明起來。
首先,觀眾得以在電影中看到電影人自覺的身份與敘事立場標識。如韓寒在幾部喜劇片中反復刻畫與自己親身經歷相關的小鎮青年與賽車手形象。其《乘風破浪》與《飛馳人生》更是有著明確的對自己已故的摯友徐浪的紀念性。在《飛馳人生》中,主人公拉力賽車手張弛一度因為被禁賽五年而經歷了從天堂跌落到谷底的人生變遷,在五年的臥薪嘗膽后,他努力實現各項條件重回念茲在茲的巴音布魯克賽場,并最終為比賽而付出生命。很顯然,張弛的心理結構與身體意識,其對賽車的執念,是屬于韓寒本人(以及韓寒眼中的徐浪)的,韓寒以這樣一部喜劇電影來在公眾面前重建了自己導演之外的賽車手身份,且將自己有關于賽車的個體感受具象化、合理化,并上升到了某種高度。與之類似的還有如大鵬講述個人搖滾夢想的《縫紉機樂隊》,賈玲根據自己與母親的故事創作的《你好,李煥英》等。
其次,觀眾可以看到,喜劇電影中的主人公擁有了話語主體地位,換言之,他們是表達電影人獨立自由意志的代言者,而非是被輕浮搞笑話語凌駕于其上的工具。如韓寒在《后會無期》中借由劉鶯鶯與自己同父異母兄弟浩漢的對話表達了“喜歡就是放肆,但愛就是克制”這一觀念,這也是韓寒對塞林格“愛是想要觸碰卻又收回手”一說的個人理解;其后的《四海》中,周歡頌亦詢問戀人吳仁耀“愛與喜歡有什么區別”,而吳仁耀為周歡頌點的歌中,歌詞則是“不愛那么多,只愛一點點”。這些對話或配樂本身已與搞笑無關,而是代表導演的思考與感情。與之類似的還有如在電影中反復出現的,或曰已消融在其思維方式中的個體經驗,如尷尬的父子關系,看似深厚卻不堪一擊的友情等。電影人將喜劇橋段用來做表達主體話語的載體,而非為了營造喜劇而填充各式陳舊的話語模式。
最后,這一時期的喜劇電影還尤為強調主體被異化的過程或與他者的對抗過程,激發觀眾的思考。這其中較為典型的便是如周申、劉露的《驢得水》。觀眾實際上未必會認同張一曼對性自由的追求,但卻能同情她遭受身邊人一而再、再而三的侮辱,最終在精神恍惚中開槍自殺,對于軟弱的、一再喪失原則的校長的做法也可以理解;觀眾不會認可原來只是精打細算,但后來站在道德制高點借機羞辱張一曼的裴魁山,不會敬佩一度充滿正義感,但在子彈面前瞬間變成磕頭如搗蒜,甚至為虎作倀的周鐵男,以及在擁有知識以后反而更接近“牲口”的銅匠,但是對他們的蛻變都并不陌生。在人物發生沖突時,觀眾也不再麻木,而是主動代入到異化人的社會關系中,進行歸因和類比。由此,喜劇電影的主體實現了“在場”。
三、人文精神的再度張揚
“人文精神指的是對人的價值、尊嚴、權利,亦即人的生存意義的關注,它著眼于對人類命運的歸宿、痛苦與解脫、幸福與追求的思索。”在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喜劇電影又開始表現出了對人,對人生活的現實世界的關注,尤其是開始多角度地探討人性,人的尊嚴與價值,人的或優或劣的生存環境等問題。一言以蔽之,人文主義精神得到了再度張揚,觀眾在笑過之后,往往能感受到電影人的赤誠與悲憫之心。
在這一批喜劇電影中,當代普通人本真的生活狀態得到呈現,盡管為了達到喜劇效果,電影主人公的生活狀態是被夸張處理了的,但這并不影響電影給予觀眾的真實感,讓觀眾感到某種“在場”。如在由寧浩、徐崢等導演共同完成的,由五個喜劇短片連綴而成的《我和我的家鄉》中,張北京等人就成為時代的縮影或地域精神的象征,電影的敘事完全從這些普通人的視角出發,經由一個個小人物的喜怒哀樂,其對困境的突破,帶出了如醫保、山區交通,農村教育與經濟等問題。如張北京是一個典型的北京“頑主”,有些貧嘴、愛吹牛的小毛病,但是在他人有求于自己時,又會熱情地伸出援手。在《北京好人》中,張北京就絞盡腦汁地想出種種方法讓在北京做外賣員的表舅用自己的身份看病,在自己也要攢錢買車的情況下,唯恐表舅因病而傾家蕩產。電影沒有進行刻板的說教與直露的宣揚,而是選取了現實生活中具有典型性的人(普通市民與進城務工的農民)與具有代表性的事(看病),在展露中國社會進步的同時,也委婉地暗示出當代人在這一進步潮流中理應秉承的奉獻、助人等價值觀。類似如《神筆馬亮》中的馬亮,《最后一課》中的老范等,也都是身份普通,但靈魂深處閃耀人性光輝,在張揚人性善后,以實踐改變了世界的典型人物,寄托著電影人的生存理想。
并且,觀眾還可以在這一批喜劇電影中,看到電影人一種對現實進行嚴峻省視乃至考問的態度。如在陳建斌的《一個勺子》中,用有一絲善念收留了傻子的拉條子夫婦成為“傻子”,而傻子在各路前來認親的人眼中則是可以謀利的工具,對楊警官來說傻子則是被冷漠推脫的對象。社會缺乏對傻子這樣的人的有效救濟,村長、胡老三等人代表了大眾的麻木與自私,而大頭哥等人則暴露出法律的灰色地帶。與之類似的還有如黃信堯的《大佛普拉斯》中,有錢人黃啟文可以草菅人命,底層游民肚財的死沒有掀起任何波瀾。在《四海》中,女性求職與在職場中時都極易遭遇性騷擾等。電影人已明確厘清:后現代主義的藝術特征,如荒誕、戲仿、游戲化等,與直面現實之間并不矛盾。如在饒曉志明顯有著效仿寧浩多線交錯敘事與黑色幽默的《無名之輩》中,多時空蒙太奇,快節奏敘事和犯罪人物的娛樂化再次讓觀眾眼前一亮,同時與寧浩“瘋狂”系列一樣,電影中的主要人物都是“草根”,身有殘疾的女性馬嘉旗失去活著的欲望,保安馬先勇一心想立功當上協警,笨賊眼鏡帶著大頭自以為能在犯罪的道路上“做大做強”,結果卻一開始就成為全市人的笑柄。他們因在教育、福利保障以及工作機遇上的缺失而生存艱難,讓觀眾在笑過之后又感到某種苦澀與辛酸。
也正是在這種對社會不公的嘲弄,對人性殘缺的直面中,原來國產喜劇電影中存在的敘事空洞化、碎片化的弊病得到克服,這是國產喜劇電影重拾人文精神后的另一收獲。由于依托于不無規律和理性意義的現實而非零散的,只為胳肢觀眾的網絡流行段子或惡搞后的舊文本,觀眾能感受到,當下的國產喜劇電影有著更為清晰的敘事邏輯。如在《尋漢計》中,一貫逆來順受的王招在離婚后還懷上前夫的孩子,但在姥爺的鼓勵下,決定生下這個孩子,于是不得不盡快給孩子找個爸爸,其后的整個“尋漢”過程,都受王招搖擺于軟弱和堅強間的個性影響,整個喜劇情境的建立是完整而可信的。還有如周申、劉露的《半個喜劇》中,莫默、孫同、鄭多多三人的情感變遷也是合情合理,具有可信度的,孫同一度為了工作與北京戶口而接受鄭多多的威脅放棄愛情,這在之前的敘事中已經加入了足夠的鋪墊。這些電影完全不需要用對其他文本的戲仿與拼貼來吸引觀眾,其符合現實邏輯的笑點(如鄭多多本身就是一個腳踏多船、謊言連篇的人,這才會導致兩個女友高璐和莫默的狹路相逢)就已經足夠逗樂觀眾。
毫無疑問,人們需要喜劇來獲取歡樂,需要喜劇來感受人類的自由、自信與精神超越。新世紀以來,喜劇電影不斷振奮國內電影市場,以其低投入高回報的特征吸引著電影人與投資者的目光。國產喜劇電影人以對自己,對觀眾,對喜劇類型片負責的態度,再度為作品尋求現實與思想建構的支撐,實現了主體性與人文精神的復歸。而我們也有理由相信,這也是未來國產喜劇片的創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