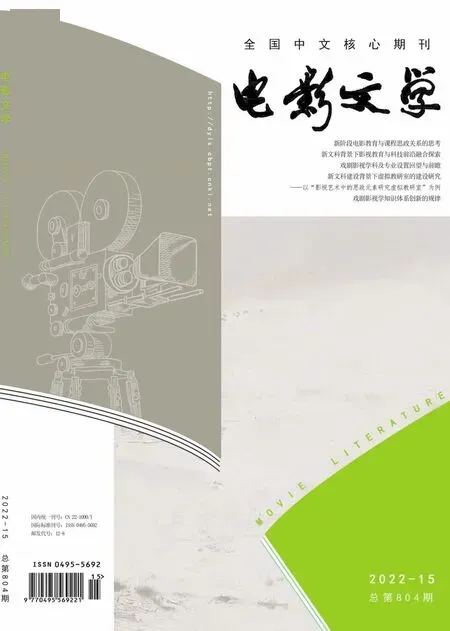論新世紀國內喜劇電影批評的三大維度
張乾坤
(湖南理工學院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湖南 岳陽 414006)
基于市場需求、現實語境等諸多因素,新世紀以來中國喜劇電影事業突飛猛進,大放異彩,涌現出了馮氏喜劇、黑色幽默喜劇、都市愛情輕喜劇與囧系列喜劇等喜劇亞類型。作為一種文化層面的積極回應,喜劇電影批評大量涌現,呈現出了一片火熱的景象。回顧與檢視國內二十年來喜劇電影批評文本,不難發現,批評的對象千差萬別,批評的維度多種多樣,很難做同一化處理。為了理解與把握新世紀以來國內喜劇電影批評實踐,論文取樣探幽,嘗試對現實性、敘事性與創新性等最常見的批評維度進行分析。
一、現實性維度
在傳統寫實或現實主義電影觀念的長期浸染與有力支撐之下,從現實性的維度分析與評價電影作品成為一種較為常見的模式,也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模式。尤其是作為一種類型元素,現實題材的喜劇電影與日常生活之間的天然親近關系,更容易促成評論者從這一維度切入。
按照周星的說法,“電影的現實性既要表現現實,更要表現現實的本質精神,即滲透在作品中對于生活的態度和思考意義”。電影的現實性與真實性是彼此關聯的,但絕不能簡單王畫等號。只有面向生活的電影作品,才可能具有生活的真實性。倒過來說,具有藝術真實性的電影作品,未必具有現實性。因為現實性表達未必是電影反映世界的唯一方式。在這里,現實性批評維度指的是評論者從喜劇與現實生活之關系角度,考察喜劇電影是否具有扎實的生活根基與強烈的現實關懷,是否折射與介入蕓蕓眾生的家長里短與喜樂哀愁。倘若某一部喜劇作品正視現實人生,及時審美轉換甚至巧妙介入生活中的熱點與焦點問題,那么該作品容易獲得評論界的較多認可甚至高度評價。從1997年的《甲方乙方》到2004年的《天下無賊》,再到2009年的《非誠勿擾》,雖然評論界見仁見智,褒貶不一,但馮氏喜劇還是在國內影壇獨樹一幟,“成就了內地喜劇第一品牌”,形成了自己的“江湖地位”。究其原因,不少評論者認為,這主要得益于他的喜劇“對生活的悉心提煉”“草根的幽默”與“世俗情懷”,他本人也被陳旭光加冕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社會風俗畫家”。長期以來,尹鴻是馮氏喜劇的主要辯護者之一,其理由是他的作品與現實焦慮之間具有緊密聯系,甚至直言“在這方面是個典范”。無獨有偶,還有評論者分析說,馮氏喜劇之所以能夠廣獲人心,備受追捧,其原因是它“好似一面鏡子,直接折射出我們生活的酸甜苦辣”。作為自稱“無惡搞”“無網絡串燒”“無山寨”的小成本公路喜劇代表之作,《人在囧途》自2010年上映以來,直面國內外商業大片的長期“肆虐”局面,奇跡般地成功突圍,成為票房與口碑俱佳的一匹“黑馬”。其“黑馬”面相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決定的。其中之一就是該片蘊含的生活氣息。“正是對當下中國社會和普通大眾生活現狀的關注,使這部現實主義題材影片得到了大多數觀眾的認可,認為其‘有誠意’‘靠譜’。”
與之相反,一些喜劇電影創作者急功近利,心浮氣躁,熱衷于混搭、拼湊、戲仿,為搞笑而搞笑,結果本末倒置,“不斷向脫離現實生活、一味追求熱鬧滑稽的方向發展”。針對喜劇電影創作上的“懶漢”行為,饒曙光分析說,“其根源是沒有對本土現實的審視、關注和滲透”,喜劇電影作品“應該建立在對現實生活境遇的滲透和輻射上”。
至于如何“滲透和輻射”現實生活,有的認為,要有俯視感,往下看,更多地關注底層的普通人群體;有的認為,要敢于針砭時弊,觸碰社會矛盾;還有的認為,要善于捕捉生活中的熱點與焦點。生活是五彩繽紛、豐富多彩的,不同的評論者關注的生活領域不一樣,強調的側重點也不盡一致,但都從不同的層面呼吁喜劇電影應該力求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
二、敘事性維度
借助畫面、字幕、畫外音和人物語言等要素,敘事是電影塑造人物形象、推動劇情發展、表達主題思想的主要手段。敘事的質量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影片質量的優劣。一部優秀的電影作品,通常敘述一個優秀的故事。鑒于敘事在影片中具有至關重要的位置,很多批評者倚重從敘事性維度切入喜劇電影批評,甚至將故事敘述水平提升到國產電影發展的高度。“只有確立故事為王的原則,才能幫助國產影片獲得提升。”“只有真的好故事才能幫助中國喜劇電影突破瓶頸,迎來真正的繁榮。”
在當下中國電影普遍存在不擅長講故事的情形下,講好一個故事對于喜劇電影在票房收入與藝術質量等方面取得突破至關重要。2012年《泰囧》在內地上映以來,取得了高額的票房收入,獲得了不少獎項。有評論者指出,它“不是靠笑料段子的拼貼”來迎合與取悅觀眾,而是憑借“整體上的戲劇化敘事”。毋庸諱言,《泰囧》與《西游·降魔篇》確實沿襲了傳統喜劇類型片熱鬧歡快、噱頭紛呈的“陳規”,但依然有評論者指出,兩部影片最主要是“在敘事上有所突破,使受眾獲得更豐富的‘意外’體驗”。2015年以來,開心麻花團隊參與出品的《夏洛特煩惱》《驢得水》《羞羞的鐵拳》《西虹市首富》在票房號召力上大放異彩,出盡了風頭,在藝術上也獲得了不同程度的好評。至于其“異軍突起”的秘訣,有評論者分析說,“開心麻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敘事策略的成功”。需要警醒的是,從講好故事這一角度來說,《泰囧》《西游·降魔篇》《夏洛特煩惱》《驢得水》《羞羞的鐵拳》《西虹市首富》等并非完美無缺,只能說這些影片在敘事上做了有益的探索,沒有積極的敘事探索,它們在白熱化的市場競爭中不可能脫穎而出。
倘若從敘事性維度檢視國產喜劇電影,可發現仍存在不少的問題,其中有兩大問題最為突出:一是小品化傾向嚴重。何謂小品化,按照饒曙光的理解,是指“喜劇電影如同舞臺上的小品,在短時間內組接一系列相互之間未必有強烈邏輯關聯的搞笑橋段,帶來‘笑’果”。誠然,電影與小品本是兩種文藝類型,兩種文類之間的互滲不僅無可厚非,反而有可能是創新之途。但跨文類畢竟還是有限度,超越了限度,導致一種文類堙沒了另一種文類,容易形成四不像。喜劇電影的小品化就是典型的“四不像”。饒曙光批評說,“東拉西湊將一些小品段子拼在一起”,“變成了一種大雜燴”。羅群分析說:“小品化敘事策略盛行,致使國產喜劇電影故事的邏輯性與人物性格的完整性頻頻出現敘事斷裂。”二是“無厘頭”泛濫。所謂“無厘頭”,暫無明確界定,但大致可理解為將一些無關的語言強行組合在一起,通過惡搞,達到引人發笑的目的。作為華語喜劇的“一面旗幟”,周星馳的“無厘頭”喜劇對于內地喜劇電影的影響是巨大的。由于港式喜劇北上“帶來了壞風氣”,“許多國產喜劇電影都在套用香港的無厘頭模式”。對此,黃式憲提醒說,連周星馳都在試圖擺脫的無厘頭模式,內地一些投資人與創作者亦步亦趨,全盤照搬,破壞了電影市場,不利于電影的長遠發展。饒曙光認為,退一步來說,“‘無厘頭’風格的喜劇電影也以敘事為核心”,問題在于,“眼下的一些喜劇電影充其量只是學到了他們電影表面的‘無厘頭’而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講故事的重要性”。“殊不知,他們恰恰忘了最根本的東西——喜劇片也要講故事,也要源自生活。”
喜劇電影不僅要有邏輯與根據地講故事,而且在講故事時,要緊扣特定的世界觀來進行。否則,即使講故事,也是混亂的,讓人摸不著頭腦。 “喜劇首先是一個世界觀”,“但當下中國電影,導演們為了票房,換不同角度看世界,最后拼湊出一個誰也不信的世界,即使技術上不錯的作品也是世界觀混亂”。在表達世界觀時,既不能太含混,也不能太直白,更不能“說教意味比較濃,褒貶的傾向很明顯”,不要“把自己心中的價值觀強加給觀眾”,否則適得其反。
喜劇電影不僅要講述故事,而且還要通過故事的敘述,以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方式傳遞正確的價值觀念。就中國喜劇電影的發展現狀而言,這方面的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引起了部分評論者的警惕。2006年以來,《瘋狂的石頭》《瘋狂的賽車》《心花怒放》等影片創造了票房神話,寧浩也因此躋身于億元俱樂部導演。有評論者指出,這些影片憑借巧妙的敘事,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小人物的各種“欲望”狂歡;但又造成了“人性探尋的缺失”“價值觀的虛無”。還有評論者指出,一些喜劇電影雖然僥幸通過了監管部門的審查,但仍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錯誤甚至價值觀的扭曲。尤其是顛倒黑白,硬是把克己忍讓、甘于奉獻的優良品質宣揚成了“傻帽”,把斤斤計較、善于算計的不良品行包裝成為“精明”能干之人的標配,傳遞了負能量,造成了消極效應。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通過文藝作品傳遞真善美,傳遞向上向善的價值觀,引導人們增強道德判斷力和道德榮譽感,向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在新時代,喜劇電影如何正確地講述故事,自覺地“傳遞真善美,傳遞向上向善的價值觀”,從而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時代賦予中國電影人的神圣使命。為此,中國電影人仍需繼續努力。
三、創新性維度
從1962年瞿白音《創新獨白》力主電影“破陳言”,要求創“一代之新”的作品,到1979年張暖忻、李陀《電影語言現代化》呼吁“加快我國電影語言現代化的步伐”,又到1986年邵牧君《中國電影創新之路》主張當代電影“超越技巧層,涉足題材、哲理層”“超越電影觀念層,探首文化觀念層”“突破再現層,接觸表現層”,再到2008年國家廣電總局副局長趙實在《求是》雜志上撰文要求廣大電影工作者“必須”付出艱苦努力,“推動藝術創新,繁榮電影創作”。在中國電影批評史的線索中,創新問題一直是電影界極為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這是因為,作為一種舶來藝術類型,“中國電影注定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模仿時期”。在這一過程中,“電影創新之路崎嶇難行”,但唯有創新,才能闖出一條生存之路,市場角逐激烈的新世紀喜劇電影更是不能例外。
從創新性的維度審視中國當代喜劇電影的現狀,不難發現,雖然電影市場表面上一片繁榮,但“盲目跟風、缺乏創新性、同質化嚴重”等弊病不少。概言之,主要有四:一是喜劇要素陳舊。當下泛生活喜劇“人物故舊”,出現了“人物沒性格,城市沒特色,職業無區別”。語言上“簡單套取流行語言”,以至于出現了“不用網絡流行語,演員都不知道怎么開口說臺詞”,山寨喜劇“都在向網絡流行語獻媚”的尷尬局面。二是敘事模式老套。2012年夏天,國產中小成本喜劇電影密集上映,但市場效果沒有達到預期,甚至遭到了冷遇。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敘事線索簡單”,故事套路不斷重復,敘事方式缺乏“更新”。《西虹市首富》力求講述愛情高于金錢的故事,但本土化改編時在情節的搭建上卻相當滯后,甚至“依然停留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好萊塢、香港電影的老套類型、模式”。三是主題陳舊。《泰囧》“借助喜劇外衣與異國元素講述了財富與真情之間的抉擇”,但可惜“主題比較老套”。《煎餅俠》的“故事立意俗不可耐”。四是缺乏本土創新。內地喜劇無視文化差異,盲目模仿、復制、翻拍港式喜劇,導致“喜劇創作轉向慢性自殺”。寧敬武借用類比說是“木耳化”,認為“現代喜劇不好看跟港式喜劇有一定關系”,內地喜劇是木耳,它是生長在港式喜劇朽木之上的。喜劇電影沒有本土創新,就沒有長久的生命力。國產喜劇電影創新乏力,不僅嚴重影響行業聲譽,以至于有人將喜劇視為“低俗”“爛片”的代名詞,而且還嚴重制約了國產電影的健康長遠發展。很多評論者呼吁本土創新。有人認為,應該“在已成功的基礎上往前走”,而不是一味模仿導致“被迫退回”;還有人認為,應該在系列、品牌意識以及題材等方面下功夫。但總的來說,究竟如何進行有效的本土創新,仍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問題,需要深入地探討。
結 語
從學術史來看,中國新世紀喜劇電影批評是中國電影批評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鮮活的時代氣息與濃郁的當下氛圍。從現實性、敘事性與創新性維度切入電影批評,與其說是中國新世紀喜劇電影批評實踐的范式創新,不如說是先在電影批評實踐的有效展開與拓展,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它將馮氏喜劇、黑色幽默喜劇、都市愛情輕喜劇與囧系列喜劇等新興的喜劇亞類型納入批評視域,不僅延伸了批評的觸角,擴充了批評的邊界;而且還將現實性、敘事性與創新性這三大維度對象化,在實踐中再次證明了這些先在批評范式的效力與活力,彰顯了其歷史價值與現實意義。
也許新世紀國內喜劇電影在時間跨度上并不算長,但就其亞類型與內在規定而言是極其復雜的。由于對象的多面性,主體的復雜性,導致不同的評論者在批評時選擇的維度存在很大的差別,現實性、敘事性與創新性僅是其中三個最常見的維度而已。即便如此,也并不是意味著每一個評論者在每一次批評時都同時采用了上述三個維度,反而是因人而異,有側重地擷取其中的一個或兩個。另外,三個維度之間不是彼此割裂,毫無關聯,而是內在地聯系在一起。作為內容方面的要求,現實性是敘事性的必要條件,否則敘事可能無明確的指向;作為表達技巧方面的要求,敘事性是現實性進行藝術轉化的必要手段,否則現實可能無法進行藝術升華。只有現實性與敘事性的有機結合、完美統一,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