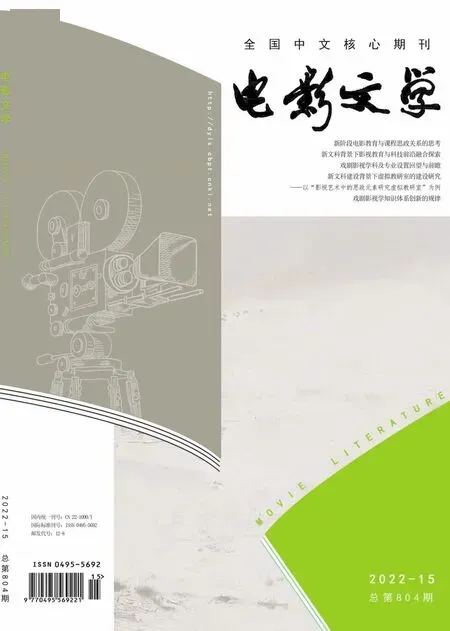王家衛電影與現代鏡語下的東方思維
徐 昕
(青島電影學院,山東 青島 266520)
“東方”不僅是一個方位概念,還是一個文化概念,有別于以古希臘為源頭的西方文化,中、日以及古埃及、印度和波斯一帶起源的文化,被統稱為東方文化,體現著東方人獨特的、富有詩性的思維方式與日常行為系統。這也就使得,盡管電影藝術誕生并興盛于西方,但電影人同樣可以賦予其東方烙印,這既包括了在內容上,電影人對本土風情地貌的細膩捕捉,對本地人精神世界的細致關懷,也包括了在形式上,對東方美學概念如“意境”“物哀”“風骨”等的充分運用。導演王家衛出生于上海,五歲時隨父母移居香港。在20世紀80年代,原本以平面設計為專業的王家衛開始以編劇身份踏入影壇,最終憑借執導《旺角卡門》讓觀眾記住了他的導演身份。隨后,其《春光乍泄》《東邪西毒》等電影更是頻頻獲獎,逐漸樹立起了獨具一格的表達風格,也讓世界觀眾以一個不同于內地導演提供的視角來觀照東方世界。王家衛電影之所以能引發國內觀眾的共鳴和贊譽,與其風格的東方化,與其文本和影像中體現出來的東方思維,尤其是中式思維是密不可分的。
一、王家衛電影的東方哲理思維
在王家衛電影中,觀眾可以看到其在對情節和人物關系的設計上,流露出的東方哲理思維。
一是圓融整一思維。東方哲學被認為是原始思維的延伸,而后者則是一種混沌型的,傾向于從整體上來認知、把握對象的思維。在原始人看來,如若對對象的觀察與表現是部分性的,那么這一對象依然是陌生的,是令人感到不安的。這一思維有兩大特征,其一便是“物我不分”或“物我同一”,即模糊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界限;其二則是強調人與人,人與客觀外物乃至有生命或無生命的物與物之間存在一種相互作用、轉化或相互激發情感的關系。即使是在人們逐漸加深了對外部世界的了解后,依然會以這一思維來進行思考或審美創造。這種整體思維既存在于銀幕內電影中人的意識中,也體現在導演本人對劇情的處理上。如在《一代宗師》中,當武林門派林立,各自都有不傳之秘時,宮羽田則表示:“拳有南北,國有南北嗎?”他對女兒宮二也曾有過學武有三重境界的教誨,即“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人被納入國家、天地與眾生這一整體之中。并且,在王家衛電影中,人物故事常常呈現割裂的狀態,如若仔細推敲便不難發現,它們其實存在共通之處,“它們總是勾搭連環、糾結纏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法拆解、難以廓清,表現出一種普適性和不可分析性,只有在其圓融整一的有機聯系之中才能做出完整、全面的把握”。如在《重慶森林》中,人物生活于魚龍混雜,猶如一個微縮版世界的重慶大廈,看似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彼此不認識,沒有交集的人們在這里擦肩而過,正如警察223何志武所說:“每天你都有機會與每個人擦肩而過,你也許對他們一無所知,但他們將來都有可能成為你的知己或朋友。”他和金發女殺手之間的露水情緣,與警察663和小吃店阿菲的戀情,看似毫無關系,但是都可以被納入生活富有隨機性,人溝通有困難性這一主題下。而人將感情與罐頭和小吃,將自己與大頭針、無腳鳥等建立聯系,663把漏水的房子形容為“房間哭了”等,也是一種“物我同一”思維的體現。
二是超驗與非理性思維。如前所述,東方哲學保留了原始思維的一部分,其中就包括了一種對彼岸世界的觀望,以及對于神秘、超驗,難以實證者的不排斥。人們在不以怪力亂神為主流之余,也并不認為理性與邏輯可以指導一切。如在“中國美學中的‘天籟’‘作詩如悟禪’‘頓悟’‘妙悟’等范疇和命題都是非理性的、神秘主義的,也是西方理性主義美學所無法清晰闡明的、難以理解的”。王家衛也有意為電影涂抹一層非理性色彩,其并非為宣揚官能體驗或迷信,而只為間接地表現人物處境或思緒的復雜,試圖激活觀眾的“妙悟”。如在《東邪西毒》中,歐陽鋒每日看皇歷,看上面各種宜忌事項,“有血光,忌遠行”,“沖龍煞北”云云;又如自稱自己命書上有一句話“尤忌七數,是以命終”等,在電影中,與之相關的字幕或人物對此的喃喃自語反復出現。這些關乎歲星神靈的話語是缺乏科學依據的,歐陽鋒本人以殺人為買賣,本身就是為他人制造混亂與災禍者,他對皇歷與預言的態度也是曖昧的,似乎處于將信將疑間,他對日期與皇歷的關注,實際上反映出的是他飽受妒忌煎熬后內心的極度孤獨和茫然,同時這些非理性話語也能幫助生活在當代的觀眾進一步向電影中的時空靠攏。
二、王家衛電影的東方道德思維
王家衛電影中,還體現著較為鮮明的東方道德思維,盡管他并不會直白表露本人的道德判斷或追求,但是卻往往讓人物成為道德主體,在敘事中演繹著中華文化中的道德內涵。
這其中較為典型的有人物在兩性情感關系中“發乎情,止乎禮”的自我道德約束。“發乎情,止乎禮”出自《詩大序》對《詩》的解讀,其原本討論的是關于詩、樂、舞等藝術創作中的起點與目的,情感與理性的比例問題,其后被引申為某種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道德指導,即主張人物在情感萌生之際,有必要以理性進行調和節制,最終達到一種理想的“以理節情”,維護人際關系和諧的狀態。在儒家思想的引導下,人們普遍性地認可這一道德觀,以確保秩序的穩定。這體現在王家衛的電影中,主要便是人物因婚姻或其他人倫關系,強行抑制自己對他者的感情。例如在《花樣年華》中,蘇麗珍與周慕云因為各自配偶的出軌而相識,在接觸中也漸漸對彼此產生了感情,但兩人因為已婚的身份而始終自我控制,提醒自己和對方“我們不會像他們一樣的”。王家衛以大量的鏡頭表現了人物內在欲望的萌芽,同時又飽受內心的道德束縛,擔心鄰里流言蜚語,因而處于痛苦掙扎之中。也正因為彼此給對方留下了保守、克己、被動的印象,因此直到最后兩人都多弄到了一張船票,卻都心存疑慮,擔心對方不愿意接受“如果多一張船票,你會不會跟/帶我一起走”的邀約;與之類似的還有《一代宗師》中,葉問與倔強秀美的宮二彼此不打不相識,產生了情愫,但是葉問已經有妻子張永成,而宮二則要為報父仇而奉道獨身,兩人始終只保持友誼,直到宮二臨死前才對葉問表白:“喜歡不犯法,可我也只能到喜歡為止了。”在《東邪西毒》中,即使是個性離經叛道的黃藥師,在愛上歐陽鋒的嫂子之后,也選擇遠遁。在東方思維中,“自我意識對倫理世界的維護,建立在心與身之間的互動關系之上,心雖然是善性的能動或自為的表現,但身又有情欲的沖動,二者之間存在一種‘樂觀的緊張’關系”,人物在欲望與道德倫理間的博弈,人物形象因克制而發散的魅力,正是王家衛電影反復觸動觀眾之處。
除此之外,還有人物堅守正義底線,或是秉承某種行俠好義、濟困扶危的道德理想。與古希臘神話中諸神胡作非為、縱情任性不同,早在孟子時代,“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的觀念就已被提出,而《史記》中亦有了對“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者的褒獎,這些道德理念深切地沉淀于民族心理中,成為一種在進行是非判斷時的穩定思維。在《一代宗師》中,投降日寇,擔任奉天協和會會長的馬三無疑就是放棄正義底線者,宮二立誓要殺死馬三,這既是為父報仇,也是為國除害。與之相對的,葉問寧可出走香港也絕不投日,原本家境富庶的他表示:“現在國難當頭,困難人人有,窮一點也沒什么。我這個人喝慣了珠江水,這日本的米,我吃不慣。”而一線天更是深入敵后鋤奸,成為“一代宗師”。在《東邪西毒》中,東邪黃藥師與西毒歐陽鋒都算不得俠,只有從鄉下剛出來闖蕩江湖的洪七甘愿為一個貧苦得只剩下一頭驢子和一籃雞蛋的村姑出頭復仇,即使最后身受重傷,失去了一個手指,他也毫不后悔。而洪七行俠仗義的回報便是,相比于黃、歐陽、慕容等人的終日痛苦,只有他成為一個快樂的人。在此,王家衛書寫的是自先秦兩漢時便已深入人心的思維:讓人超越生理生命的脆弱與短暫,擁有充盈的精神世界的,絕非武功,而是高尚的道德。
三、王家衛電影的東方審美思維
正如學者指出的,電影這一藝術形式是西方的舶來品,西方的藝術經驗與理論成果對中國電影人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電影人在經受中國傳統美學多年的哺育之后,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在電影中糅入中國美學的精粹。而東西方在審美思維上的差異體現在,西方古典美學的基礎被認為是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亞里士多德認為藝術便是模仿,而從《詩》《樂記》《禮記》上生發出來的中式審美則是與模仿論不同的言志論:“在創作方法、藝術風格和美學理想上,模仿論趨于寫實、再現、逼真,言志論趨于寫意、表現、境界。”如在繪畫中,當西方畫家采用焦點透視法來再現對象時,中國畫家則反其道而行之,并不嚴格地遵循固定視角與物體間的客觀比例。又如在文學中,以“楊柳依依”“雨雪霏霏”(《采薇》),“黃河流水”“燕山胡騎”(《木蘭辭》)等營造出未必真實存在的意象空間,其目的都是為了能完成某種情志或理想的表達。
電影藝術亦是如此。王家衛在電影中踐行著對意象的營造,力圖實現王夫之所說的“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的理想目標,其電影中的景物,往往是綜合了光影、構圖以及色彩處理后的情愫表達。如在《東邪西毒》中,桃花在夜里靜靜地站在波光粼粼的水中撫摸著一匹黑色的馬,讓人備感怪異。而歐陽鋒則身處沙漠之中,舉目皆是黃沙,空氣干燥之極,一片蒼涼之景,并且“沙漠的那邊是另外一個沙漠”,熾烈陽光透過旋轉的鳥籠照在歐陽鋒臉上,使得他的臉顯得時陰時陽,這又引發觀眾某種焦躁、畏懼的情緒。而在對人物關系稍加了解后,觀眾便能意識到,前者情欲的無處釋放,后者關閉內心,情感高度荒漠化的狀況,都借由景物得到表現。又如在《一代宗師》中,宮二在皚皚白雪中練拳,與馬三生死相搏時也是天降大雪,火車站白氣蒸騰,這固然與宮家原本就在東北有關,但更重要的是,人物一身黑衣,置身于極寒、冷硬的景觀之中,宮二心堅如石,雖九死而無悔的意志,與馬三之間情義的斷絕得到襯托。在這里,客觀的外部意象實際上都承載了超越其原有能指的意義,觀眾自然而然地便會根據自己的生活與審美經驗,產生更加廣闊和深遠的遐想。
此外,王家衛還一直以電影來展現東方思維中根深蒂固的對含蓄蘊藉的推崇。“中國審美意識上的含蓄觀念,可以追溯到‘周禮’的委婉性和《周易》的尚象性,并成為儒、道、禪美學共同推崇的審美理想。”其電影中的畫面、形象往往包含了豐富的、暗示性極強的意蘊,吸引著觀眾去探求、交流。如在《花樣年華》中,蘇麗珍即使是在家里,也總是身著緊身旗袍,頭發梳得一絲不亂,妝容也十分精致,這固然顯得人物身姿優雅,氣質過人,但實際上這是不便于日常生活的,而王家衛正是以這樣的形象設計委婉地暗示人物的心靈世界:蘇麗珍始終盡力維系著自己端莊克己、優雅從容的形象,身處狹窄的居住空間,又穿著修身旗袍,其肢體活動大大受限,同時受到限制的,還有她對周慕云的感情,她唯一能做的,便是更換不同顏色的旗袍呈現自己的情緒。與之類似的還有《阿飛正傳》中,伴隨蘇麗珍出現的時鐘和柵欄,賭徒出門前與旭仔幾乎一模一樣的對鏡梳頭動作等,都是含蓄的,具有解讀空間的設計。在此不贅。
四、王家衛電影東方思維的多重啟示
當中國人急于走向世界,卻在運用中式元素上不無誤區,或是在堅持個性還是追逐票房間搖擺不定的當下,王家衛電影提供了寶貴的啟示。首先,對于王家衛對東方思維的闡釋,我們無疑是要給予肯定的。毋庸諱言,人們身處全球化進程之中,而以好萊塢為代表的西方電影則來勢洶洶,在數十年中幾近建立起某種指向文化趨同性的霸權。同時,國產電影中也不乏為達到票房目標,過分重視感官刺激而輕忽民族精神內涵的平庸潦草之作,使得國產電影在與西方電影的競爭中更顯弱勢。在這樣的情況下,國產電影顯然有必要規避被西方同化,保持自身在美學表達上的獨特性和異質性,也有必要避免其他人奪走對于東方風情或華夏精神的定義權,同時讓民族電影產業擁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維持一種健康、穩定、可持續的發展狀態。
其次,我們有必要注意到的是,王家衛電影浸潤了東方思維卻是非“東方主義”的。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電影人就開始了有關于電影“民族化”的探討,希望建立起某種具有民族特色的美學傳統。就目前的作品來看,一般來說,被認為電影具有鮮明中式標簽的電影,或是表現出了某種舊式的詩情畫意,如費穆的《小城之春》,吳貽弓的《城南舊事》,以及霍建起的《秋之白華》等,在這一類電影中,觀眾能較為直接地看到人物身處一種靜美悠然,情韻綿長的古典審美景致中;或是如個別第五代導演,為了打入國際電影市場而或多或少地迎合西方人獵奇心理,在電影中大量復現了一些中式民俗甚至是偽民俗,加深了其他國家觀眾對中國的“他者”想象和落后偏見。
而王家衛與前者截然不同,他能夠讓電影中高度國際化、現代化的都市生活來展現東方思維,包括凸顯人物在現代都市生活中空間上的陰暗逼仄、嘈雜喧囂,人生存狀態的漂泊不定、顛沛流離,以及在與異性交往時的躁動不安、充滿隔閡等,這也正是王家衛電影很早就能以一種“世界性”得到外部認可的原因之一。正如之前所提到的,后現代主義是談及王家衛電影時難以回避的特征之一,他正是將自己對后現代主義的理解,與自己文化積淀中的東方思維進行了結合,并未自然主義式地呈現現代都市人生活的各種苦悶無趣之處(如婁燁的《蘇州河》等),亦不曾兜售某種苦難景觀,而是通過如聲畫蒙太奇,顛覆線性敘事等手段讓原本并不舒心適意的現代生活具有了某種值得人品味的詩情。盡管我們并不能說王家衛電影就代表了“民族化”的方向,但其中所具有的傳統文化內涵與審美價值取向,的確是對電影“民族化”的一種補充,而其關注現代都市,融會后現代主義的創作方向,對于部分傾向于通過回看古代或凝望鄉野來完成“中式”書寫,很容易滑向“東方主義”陷阱的電影人來說,無疑是有啟發的。
最后還要提及的是,王家衛電影還基本上實現了對經濟規律與藝術規律的兼顧,原本極富個人色彩與詩性氣質的東方思維,能夠被他納入商業美學實踐中來,盡可能避免贏得口碑失去票房的窘境,這也是值得有意走出國門的中國電影人借鑒的。只要對王家衛電影稍加注意,便不難發現,已被好萊塢商業片確立起的三項原則,即明星制、類型片與大片廠制度,都是王家衛樂于接受的。如他不僅熱衷于選用明星,讓如梁朝偉、張曼玉等知名演員貢獻出具有可識別性的,讓觀眾熱議不休的表演,還善于在特定角色上,如《旺角卡門》中的烏蠅、《重慶森林》中的阿菲等,挖掘出本業并非演員的明星的表演潛質,實現了明星與影片的相互成就;又如在表達上的特立獨行中,王家衛依然注意保留電影基本的,能發揮娛樂效果的類型特征,如《東邪西毒》《一代宗師》中精心設計的動作場面,《花樣年華》中纏綿悱惻的兩性糾葛,以及人物讓觀眾賞心悅目的外形等。這也就使得人們普遍認可:“看他(王家衛)的影片是一種享受,既有帥哥美女主演,也有他們彼此之間的演技大比拼,再加上導演強烈的新浪潮的電影風格,使觀眾不論是在感官或思想上都有驚喜,是現在極少數拍片兼具娛樂與藝術價值的導演。”
毫無疑問,王家衛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電影“作者”,其電影中各基于王家衛本人生命體驗和思想的特征,乃至其無劇本創作,超長拍攝周期等特立獨行的拍片方式,都是他人難以復刻的。但其電影對于東方思維的繼承,其對傳統與現代關系的處理,依然對當代中國電影人有重要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