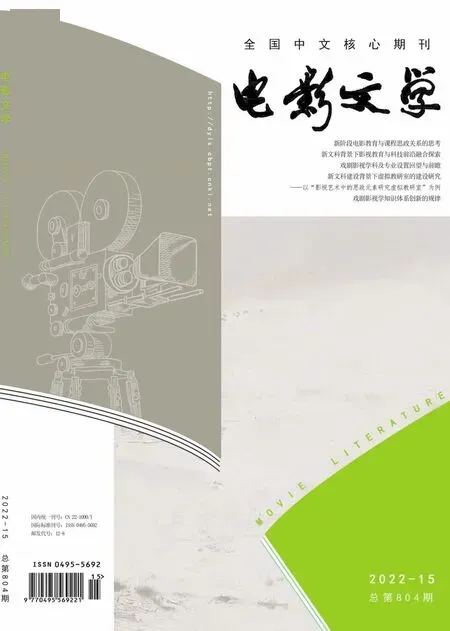濱口龍介:“身份-影像”錯位敘事的情節建構
仝斯宇
(中央戲劇學院,北京 100006)
濱口龍介作為日本新生代導演,自其碩士畢業作品《激情》引發熱議以來,成為各大國際電影節爭相邀約的對象。2022年執導的電影《駕駛我的車》更是摘得第94屆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獎。日本東京大學前任校長、電影評論家蓮實重彥在日本《經濟新聞》曾表示,濱口龍介的出現代表“日本電影已進入第三個黃金期”。阿部嘉昭在論文《濱口龍介:身體感覺論》中指出,“濱口龍介在早期作品中將角色與演員的雙重身體納入以戀愛敘事為核心的情境中”,這種特質一直延續到近年來濱口龍介的新作中。值得注意的是,與早期對純粹身體迷戀不同,濱口龍介近年作品更凸顯出對身份的持續關注。在他的影像中,“身份”作為自我的本質,是連接主體和公共世界的橋梁,將主體融合到社會結構中。這種融合過程往往不是自動和自足的,而是在與“重要他人”的關系中形成的,伴隨著大量錯位現象的發生。身份錯位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精神結構的錯位,在他人的眼光中,主體由于對身份理解的偏差、面臨混雜性身份處理的矛盾,或對流動身份的困惑而主動或被動地處于持續的身份錯位語境中。
一、模糊的愛人面孔:盲目、質詢與遷移
身份并非主體性存在,而是在與他者關系中由自我認知或他者的看法形成的,其錯位首先在于對身份理解的錯位,在濱口龍介的影片中則密集地表現為對愛人的他者身份誤認。這種現象很早就出現在其短片作品《觸不到的肌膚》里,千尋和直也作為舞蹈訓練的搭檔一直在一起進行現代舞練習,試圖讓肢體保持一定程度的牽引距離。這種訓練使得二者之間形成了某種神秘的“鏈接”關系,但當時直也并未意識到。他一直將自己的愛戀對象誤認為梓,但當梓遇害,他卻為了保護兇手千尋而主動擔下罪名。影片雖未明確直也與千尋關系的后續發展,但梓并不愛直也,直也只是將其誤認為愛人的事實卻是不容爭辯的。這種對愛人的誤認本質上是錯誤地將想象中的愛情“面孔”與某個他者存在進行鏈接的結果,是對作為存在的他者身份理解的錯位。這種“面孔”概念由法國哲學家伊曼努爾·列維納斯提出,認為作為他者的他異性體現為“面孔”,不僅代表某個具體的臉龐,更是一種隱喻,是愛情在主體面前的整體呈現,這里的他異性被視為一種神秘。
濱口龍介對誤認愛人的他者身份的探討在影片《夜以繼日》里達到巔峰。該片通過女主陷入一場“盲目的戀愛”,建構起非理性情感主導下,身份理解錯位的合理性。年輕的女孩朝子去看攝影展,作品內容包括安睡一室的嬰兒、相互依偎的夫妻、孿生面孔的姐妹等,暗示出人與人之間神秘的鏈接關系。之后,她偶然遇到了神秘男子麥克,并不可自抑地額外關注他,她直勾勾地盯著麥克看,甚至還不自覺地跟在麥克后面走,仿佛他們之間天然存在一種神秘的關聯性。這種關聯性營造出一種強烈的宿命感,使得兩人在第一次見面時就迅速確定了關系。從相遇到相愛,整個過程不到3分鐘,僅僅22個鏡頭里,朝子就陷入了愛情。
鏡頭1:近景,朝子正面,座位后方穿白襯衫的麥克入畫。
鏡頭2:特寫,反打鏡頭,朝子回頭看向麥克,接近主觀視角。
鏡頭3:中近景,側面,麥克從朝子背后路過,朝子盯著麥克看。
鏡頭4:中景,朝子主觀鏡頭,麥克看展,有路人在。
鏡頭5:中近景,朝子回過頭停止注視。
鏡頭6:特寫,手拿宣傳冊。
鏡頭7:中景到全景,朝子看宣傳冊,向左走,鏡頭左搖,麥克入畫,后景有路人。
鏡頭8:中近景,仰拍,朝子主觀鏡頭,麥克的背面。
鏡頭9:近景,俯拍,朝子抬頭看。
鏡頭10:全景,后側,朝子跟在麥克后面走出門。
鏡頭11:大全景,前側,朝子跟在麥克后面走出門。
鏡頭12:全景,仰拍,朝子跟著麥克上臺階,分別往兩側走去。
鏡頭13:全景,鞭炮響,兩人回頭,兩人面對面。
鏡頭14~17:中景/中近景,麥克看朝子/朝子看麥克,正反打,高速攝影。
鏡頭18:大特寫,麥克的腳,走向朝子。
鏡頭19~21:近景,側面雙人/麥克/朝子,麥克吻朝子。
鏡頭22:全景,兩人相擁接吻。
在這一組鏡頭中,朝子與麥克的戲劇性行動與關系始終處于公共開放環境中,但卻通過鏡頭邊界的限制人為地在二者之間構建起一個封閉的二人敘事空間(1~3、10~12、19、22),二人之間存在著緊密的注視與被注視關系(3~5、8~12、14~17、18、20),其他人的出現反而成為對這一關系的打斷與介入(4、7~11、13~15)。這種誘導性敘事先驗地將二人捆綁在一起,與間離性的審視視點相結合,形成一種主客觀并置的心理距離呈現,相遇的宿命感由此而生。
在這段關系里,麥克是朝子愛情的符號,朝子通過可見的麥克而去觸摸那個無限的他者。這種神秘關系的基礎是“愛欲”,即認為性別的二元性假設了一種有待融合的整全,構成了朝子與他者之間的“鏈接”。但這種鏈接的存續卻是依托于戀愛幻象的,拉克勞在1977出版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政治與意識形態》一書中曾用柏拉圖的“洞穴寓言”解釋過這種“鏈接”的偶然性與不穩定性。“洞穴寓言”說的是洞穴中被囚禁的人看不見洞外的世界,而只能看到洞內的墻壁。當洞外人的影子在陽光照射下映射到墻壁上時,他們的聲音也傳進了洞里,因此洞穴里的人就認為,聲音是墻壁上移動的陰影發出的,而將聲音與陰影“鏈接”在一起。在這個著名的哲學寓言中,“鏈接”是在話語誤導下完成的,并非邏輯主導,是一種錯位的結合。正如朝子與麥克的相識,一見鐘情就確立了二者關系,其“鏈接”并非建立在相互了解的理性判斷之上,而是基于對宿命性伴侶身份的“誤解”,這一點從二人朋友不敢置信的反應中也得到了進一步印證。
然而,情欲之樂的哀婉便在于這種鏈接里存在著主客體間的二元對立。于朝子來說,在與作為他者的麥克陷入愛情后,麥克就不再是他者,而形成了“我們”。她不斷通過與麥克的接觸追求超越主客體之間的邊界,他們一起生活、共歷死亡、相互愛撫,不斷強化這種“鏈接”的自我暗示。但不可否認,基于二者誤認的關系脆弱不堪,當麥克出去買面包一夜未歸時,朝子的手足無措便足以展現這種鏈接的不可靠性。終于,麥克不告而別徹底消失,這種“鏈接”就又撤回到它的神秘中,朝子也不得不面對這種身份理解錯位帶來的無序。她不知道自己愛上的,是麥克神秘自由的靈魂,還是年輕帥氣的面龐,對命定“愛戀他者”的誤認使其重新成為一個模糊的“面孔”。因而當兩年后朝子在辦公室遇見了長相一模一樣的亮平,誤認便再次發生了。朝子連續兩次將亮平叫作“麥克”,試圖重新建立“存在”與“面孔”之間的接合。被現實否定之后,朝子便一直刻意回避亮平,極力避免“誤認”的再次發生,其戲劇性頂點出現在又一次的攝影展中。同樣的攝影師,同樣的作品,這一次看展的卻是陌生的朝子與亮平,導演僅用了兩個鏡頭就展現出二者關系宿命性的“鏈接”感。
鏡頭1:近景,朝子正面,座位后方亮平入畫,與當年麥克出現的畫面構圖一模一樣。
鏡頭2:中景,朝子刻意躲開,但忍不住再次注視亮平。
在這里,影片雖然未用大量鏡頭來渲染朝子對亮平的關注,但構圖與內容的相似性形成了與初遇時刻的跨時空互動(1),一切似乎又回到朝子遇見自己的愛情的那個瞬間。盡管朝子極盡克制地躲開了,但她也終未逃脫對“麥克”的誤認(2)。不久后在樓梯道,朝子再次一頭栽進錯位的愛情里。
鏡頭1:中景,朝子拿著咖啡壺從消防樓梯離開,鏡頭右下方跟搖,亮平追出。
鏡頭2:近景,朝子低頭,緊張不語,亮平伸手摸臉頰。
鏡頭3:景別收緊,接近特寫,互相摸對方的臉頰,接吻。
鏡頭4:二人中景,接吻。
有了第一次對與麥克相認的描述,朝子與亮平關系確立的鏡頭更為簡單,不再將二人置于公共視野中,而在私密但開放的消防樓道里,前后景皆為樓梯和樓體線條所構成的幾何框架(1~4),形成二人關系內在的壓抑束縛感。但與第一次朝子對麥克的注視始終處于“仰視”的境況不同的是,亮平主動選擇站在低處仰視朝子,形成話語權力關系的逆轉(1~3),并借由愛撫試圖實現對永不可通達的他者的超越,于是朝子放下了滿身戒備接受亮平。
自此,朝子與亮平過上了平靜的幸福生活,與之前和麥克在一起的瘋狂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相處狀態,似乎在確認這次對他者身份的體認。但當麥克出現,一切又恢復到一個混沌的狀態,朝子承認了與亮平的鏈接是對伴侶身份的再次誤認,而決絕地跟著麥克離開。事實上,從第一次離開麥克開始,她對麥克的需求就像持續增長的饑餓,已然構成一種永遠錯位的他者身份。而通過對麥克、亮平身份的雙重誤認,朝子才慢慢厘清了愛情關系里他者的“面孔”,重新建立真正的接合,回到亮平身邊。
這種誤認愛人的他者身份的橋段在影片《偶然與想象》的第三個故事中出現進一步變形。夏子在電梯上偶遇小林綾,將其誤認為高中時的戀人由紀美嘉。二者直到在小林綾家深入交談良久才發現誤認的事實,與其說是小林綾與由紀美嘉相像,不如說是夏子一直愛戀的美嘉是一個模糊的他者“面孔”,其與現實人物的鏈接充滿了愛情的神秘色彩。因而當夏子反應過來自己將愛人誤認,雖然懊悔,但并不影響她在小林綾身上進行相似的情感投射。在角色扮演的游戲里,夏子認可了這種誤認的價值,享受身份錯位帶來的愛情體驗,因而才出現了動人的“愛的傾訴”。更具隱喻意味的是,小林綾同樣也試圖從夏子身上找到自己的“愛戀面孔”,身份錯位在這里成為普適的滿足幻想的安慰劑,誘發并強烈渲染其真實情緒,同時將這種情緒進一步擴散給坐在銀幕前有著同樣情緒客體身份錯位的觀眾。
二、矛盾的混雜性身份:割裂、并置與扮演
斯圖亞特·霍爾曾指出,在當代社會一個人會有不同的身份,它們之間是充滿矛盾的,既相互交織又使彼此之間發生”錯位”。沒有單一的身份能夠把所有其他身份統一到自己名下,即不存在“主身份”,這種身份的混雜性使得主體充滿矛盾性,其根本的特征是在同一性中對異質性和他者的揭露。濱口龍介的影片中,這種身份的混雜存在于三個維度中,一為由于人物多重身份共享時空造成的矛盾個體,二為基于戲中戲結構產生的互文性的角色共存現象,三為因生活需要角色選擇在“真我(作為自然人的我)”與“假我(演戲的我)間來回切換形成的模糊身份。
首先,就人物多重身份共享時空來說,2022年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駕駛我的車》是濱口龍介所有作品中提供最多此類樣本案例的影片。影片伊始,家福和妻子音在床上,暗調環境里,二人都裸體蓋著毯子,音在跟家福說自己剛編的一個青春期女孩的戀愛故事,說完后二人再度相擁而眠。在二人獨處的私密環境中,音同時扮演“妻子”和“編劇”兩種身份,其形象呈現出一種吊詭的矛盾感。之后,觀眾了解到,家福與音的婚姻盡管看似美滿幸福,但二人失去過一個孩子,且音長期出軌,所以二人的親密關系中始終存在難以逾越的隔閡。這種既親密又疏離的關系在音陪家福看完醫生,兩人在家里做愛時顯得尤其突兀。看似動作主動熱情的兩人在不面對對方時,眼神都出現了可怕的靜默,特別是音,目光直勾勾地盯著鏡頭,狀態完全抽離在親密行為之外。隨即,音再度進入“妻子”和“編劇”并存的講故事階段,故事的女主角前世曾是條七鰓鰻,詭異的氛圍充分暴露出其身份錯位在親密關系中造成的割裂感。
而丈夫家福,盡管長期克制隱忍,但在音去世后,其實久久也未能走出妻子曾長期肉體出軌的自我質詢與折磨中。當在廣島擔任導演看演員試戲時,他重遇了妻子年輕帥氣的情人高槻。高槻在與女演員試戲時的親吻動作,使家福回到了他看到高槻與妻子出軌時的歷史記憶里,瞬間行為失態,成為“丈夫”和“導演”身份并存的矛盾體。
鏡頭1:中近景,高槻試戲親吻女演員,畫外有刺耳的噪聲,高槻回頭。二人背面的鏡像里,家福在說抱歉。
鏡頭2:中近景,家福感謝二者的演出。
鏡頭3:近景,鏡頭反打回來,鏡像里家福坐下。
鏡頭4:全景,高槻與女演員從前景離開。
音給家福帶來的長期精神折磨使其作為丈夫始終處于與現實間離的自我封閉中,因而家福對現實的凝視始終通過鏡像呈現(1、3),但職業自覺又使其試圖維持專業感與親切感(2、4),這種心理距離的反復跳切構成了家福的混雜性身份,是他與音分裂的親密關系的表征。一邊是作為被音稱贊和高度肯定的導演,其被崇拜、被關愛、被理解的男性精神需求得到充分滿足;另一邊則是作為被妻子背叛的丈夫,充滿憤怒、不解與羞恥感。正面與負面的情緒荒誕地同時共存在家福身上,使其成為孤獨而焦慮的封閉個體,不愿被他者入侵的車內空間即是這種封閉的空間載體。他拒絕敞開心扉,卻也無力對抗,這也造成了他對生存意義的痛苦思考。
其次,濱口龍介影片中頻繁設置話劇形式的戲中戲橋段,使得演員同時承載“電影演員”與“話劇演員”的雙重身份。如影片《夜以繼日》中女主角朝子的室友真矢,亮平帶朋友串橋第一次到朝子家,便一起看真矢的演出錄像。話劇里,真矢扮演的角色說:“但是身為人至少應該擁有信念吧?若非如此,人生豈不空虛。為什么明明活著卻什么也不去做……”但在現實生活中卻被串橋質疑其表演是“演員的自我陶醉,利用觀眾來吹捧自己”。之后串橋承認自己的攻擊性言辭是出于嫉妒,“看到有人一直堅持著我已經放棄的事兒”。這種電影敘事與戲中戲臺詞所形成的互文性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對表演本體及價值的探討,真矢的話劇演出可看作是其堅毅的內心獨白的外化,與在生活中平靜柔和的形象形成一種錯位的落差感,將真矢的角色形象鮮明地樹立起來。
這種基于戲中戲結構的角色共存現象在《駕駛我的車》中體現得更為顯著,情緒層次也表現得更豐富。影片中,男主角家福作為導演兼主演全程參與了話劇《萬尼亞舅舅》的創作。一方面,他在封閉的車里,一直在通過臺詞與已故的妻子音的錄音對話。“萬尼亞,別說了,你沒聽到嗎”“不行,等等,我還沒說完呢”……影片通過這樣的方式,使家福有機會說出一直未曾言說的話,他渴望與妻子的交流,并對錯過交流懊悔不已。從這個角度來說,戲中戲的作用與《夜以繼日》非常像,同樣是作為人物內心獨白的外化,使家福掙扎的內心世界與平淡克制的外表形成反差,呈現出更加立體的人物形象。但另一方面,家福作為演員,始終在回饋他“聽”到的其他演員的對話,這種戲劇世界里的對話也真實地影響了家福。如影片的最后,聾啞太太用手語告訴萬尼亞舅舅“我們得活下去,萬尼亞舅舅。我們得耐心忍耐命運帶來的考驗……我們將歡欣鼓舞,而且臉上掛著溫柔的微笑,再回望我們此時的悲哀”。在這一刻,戲中的萬尼亞舅舅與家福似乎合為一體了,開始與生命中的苦難相和解,迎來生活的微光。這種和解被后臺的伙伴們與臺下同樣飽經痛苦的司機渡利看到,似乎也傳遞出一種希望的力量。此時,身份錯位成為一種實現自我認同的手段,話劇角色——作為話劇演員的電影角色——看話劇的電影角色——看電影的觀眾,與自我的和解逐級發生。
另外,濱口龍介在呈現生活中人的多面性的時候,會選擇讓角色有意識地“扮演”與自己真實意愿相背離的身份,形成角色在“真我(作為自然人的我)”與“假我(演戲的我)間來回切換的身份錯位。如在《駕駛我的車》中,家福在發現妻子與男演員高槻出軌時,刻意回避時的狀態。
鏡頭1:中景,家福進門。
鏡頭2:空鏡,放著音樂,有做愛的喘息聲。
鏡頭3:全景,妻子和年輕男子做愛,鏡像。
鏡頭4:留聲機空鏡。
鏡頭5:中景,家福看著二人,鏡像。
鏡頭6:全景,過家福肩,二人做愛鏡像。
鏡頭7:中景,家福出門。
即使是當面撞破丑行(1、2),家福也未曾與現實有“面對面”的接觸,而是通過鏡子的反射(3、5、6),鏡像在這里實質起到對“假我”的隱喻作用,不敢面對現實的家福與真實的世界之間始終隔著一條無法逾越的鴻溝。鏡中的家福平靜地離開了事發現場(7),但通過后續他與司機渡利的對話便知,真實的他早已暴怒。這種扮演的極致出現在家福離開家之后,他去酒店開了房間,佯裝自己在按原計劃出差與妻子視頻。事實上,家福在親密關系出現問題后,便一直封閉在自己的世界里,始終保持與真實世界的距離。即使時過境遷,他看到高槻親吻女演員不適時,一時失態地站起來,也會接著就立刻打圓場道歉。他通過扮演錯位的身份來回避現實,原初想象中的完美生活卻早已分崩離析。這種自我保護使得他整個人都封閉起來,不再喜歡與人相交,也不愿建立新的親密關系。
三、后身份:自我的他者性
后身份將原來被看作是整體的‘身份’解構掉,分解成不同層次的因素或要素,其作為一種不穩定的、一直處于變化之中的身份,使這些因素在不同語境下被鏈接在一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后身份是碎片化的、分裂的,而非統一的身份整體。濱口龍介影片中主要利用“時間”與“偶然”兩類工具去強調后身份的矛盾、差異、對抗與錯位。
一方面,濱口龍介利用時間差構建新的身份的碎片,主人公在經歷重大事件后,影片往往會留給主人公一段時間空白做出決定、完成自愈或發生改變。影片會特意標出空白時間,留出時間給變化的身份,《夜以繼日》中麥克失蹤后,二人重逢是兩年多后;《偶然與想象》的第一個故事《魔法》中美子與前男友重逢后是3天后,第二個故事《開著的門》中奈緒色誘大學教授瀨川無疾而終,與佐佐木的重逢是5年后。三位主人公所遇事件本身的發生是客觀存在,不以其主觀的意志為轉移,但如何面對與抉擇卻是電影話語所須建構的。主人公在各自的性格與經歷影響下做出選擇,呈現出主觀的客觀性。以《魔法》中的美子為例,與3天前,不顧一切跑去找嘉和不同,這一次的美子只是在心里幻想了一回她破壞嘉和與谷米關系的情境。
鏡頭1:全景-中景,嘉和進門坐下。
鏡頭2:中近景,美子點頭問好。
鏡頭3:近景,美子閉眼忍受嘉和和谷米的親切交談,隨后開口問嘉和是否考慮好了。
鏡頭4:中景,三人同框,美子坦白和嘉和的關系。
鏡頭5~10:近景/中近景,美子表白,嘉和與谷米聽,震驚。
鏡頭11:中景,三人同框,谷米和嘉和先后離開,鏡頭右搖前推至美子近景,鏡頭回拉,三人回到坦白前(鏡頭4)。
美子、谷米與嘉和的偶遇使得鏡頭得以見證美子身份變化的戲劇性瞬間(1),美子再見嘉和,表現得犀利、直接(3~10),接著影片使用了攝影機介入感非常強的長鏡頭表現這種變化(11)。開始時畫面是中景,谷米得知真相轉身離開,嘉和跟著離開,鏡頭右搖給美子,嘉和從后景跑去追谷米,鏡頭前推至美子近景,美子低頭捂臉不愿面對現實;接著鏡頭后拉,時間回到美子未開口之時。濱口龍介曾在采訪中說他認為這段鏡頭設計“不在時間和空間上動手腳,直接將鏡頭連接到另一個世界的這個想法很有意思”。同時,鏡頭本身的介入性放大了事件本身的荒誕性,是在提醒觀眾“這么荒唐的事情你們也能信嗎”?這種強烈的介入性使得美子與自我的對抗被并置放大,與3天前相比,清晰形成身份錯位性的變化。
另一方面,濱口龍介構建大量偶發性事件去促成人物的轉變,突然形成的局面使得主人公原本的行為慣性被打斷,而不得不面臨轉變,接受自我身份中出現他者元素。如《觸不到的肌膚》中直也突然面對千尋殺死了梓,而即將被逮捕;《夜以繼日》中朝子面對麥克的再次出現,不得不在麥克和亮平中做出選擇;《駕駛我的車》中妻子音突然意外死亡,家福不得不接受永遠不會再得到答案的現實;《偶然與想象》中奈緒突然面對瀨川出乎意料的請求等。在這些局面里,自我身份中新加入的他者元素不是任何形式的另外一個自我,而是與我一起分擔一種共通的實存,主體清晰地認識到這類他者是外在于當下的自我身份的存在,但又不得不接受與他者的“神秘”的關系。以《偶然與想象》為例,當瀨川得知奈緒在全程錄音后,突然提出想要一份錄音,奈緒被瀨川坦然到純粹的態度所打動,與瀨川產生對自我身份與價值認同的共鳴。瀨川指出“只有做到這點我們才有可能在某個瞬間和某個人產生奇跡般的共鳴或共勉”,此時鏡頭突然切換至瀨川教授的正面近景,他正對鏡頭目光堅定,仿佛敘述對象從奈緒切換成了銀幕前的觀眾。這使得奈緒與觀眾并置在了同樣的客體位置,深受觸動的她開始接受瀨川所描述的那個神秘“他者”進入本我。
結 語
濱口龍介對身份與影像的探討圍繞著對他者和自身的持續誤認展開,構成并列的隱喻、分割、對比與對立關系,呈現出錯位敘事的強烈戲劇張力。其情節建構基于大量非因果邏輯與理性判斷的組合事件,表現為意向的模糊性與多義性,給觀眾留下豐富的讀解與想象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