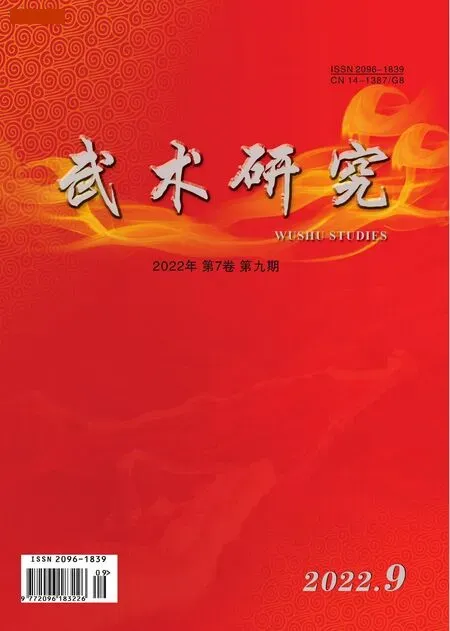古兵器“鏜”的功能與文化內涵研究
歐陽林君 胡超然
1.徐州市歐林搏擊俱樂部,徐州 江蘇 221009 2.江蘇師范大學體育學院,徐州 江蘇 221006
關于“鏜”的描述,《說文解字》注鏜:鐘鼓之聲,從金堂聲。鏜同嘡,是個擬聲,形容打鐘、敲鑼、放槍一類的嘡嘡聲;也形容金屬器物等磕碰的聲音。鏜同時可作為動詞,主要是切削的意思。從名稱可以感悟到鏜的威力之大,其發出的聲音能夠讓人震撼,從而達到威懾,最終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由此可見,“鏜”是華夏先民對待戰爭的智慧結晶。為深入了解“鏜”的來源,筆者查閱大量的古兵器資料,走訪冷兵器博物館,拜訪老武術家等,去尋求華夏先民制“鏜”的蛛絲馬跡。以更好地挖掘、整理和傳承古兵器,對古兵器“鏜”進行探究也就成為武術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1 冷兵器發展概述
原始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為了獲得足夠的食物,人們不得不與自然界的各種動物進行斗爭,久而久之,先民學會了制造和使用工具進行狩獵。為了狩獵和防身,原始的人類在實踐中懂得用樹枝、樹干、木棍當作防身器具利用石片制作石刀、石斧,這既是生產工具,也是原始兵器的雛形。在江蘇、浙江及附近周邊我國新石器的文化遺址中,就發現很多用獸骨、蚌殼、石塊等磨成的各種武器。史料記載,原始社會晚期的部族首領——黃帝已經能造出刀、槍、弓、箭等兵器;到了商代,我們的先祖開始使用青銅鑄造刀、槍等兵器。春秋戰國時期,群雄逐鹿中原,先祖們已經開始用冶煉生鐵來鑄造兵器,十八般兵器也已初步出現,“鏜”便位列其中。到了漢代、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國的冶鐵事業進一步得到發展,開始普遍使用鐵制品鑄造制作刀、槍、劍、戟等兵器,因作戰等需要,其它各式各樣的兵器也越來越豐富;到了明朝,鄭和七下西洋,社會更加進步,十八般兵器兵器種類繁多,其種類遠遠多于十八中。也就是說,所謂的“十八般兵器”:刀、槍、劍、戟、斧、鉞、鉤、叉、鞭、锏、錘、抓、鏜、棍、槊、棒、拐子、流星的說法只是一種虛數的描述,“十八”的寓意應該是指很多的意思。
2 “鏜”的結構造型
鏜其造型、種類繁多,主要是因為,依據其戰場功用、需求不同,以及為應對特殊兵器、特殊環境而特意制作。鏜分為鏜頭、鏜桿、鏜后把三個部分。鏜頭在過去是在鐵匠鋪的紅爐制作,用生鐵和鋼千錘百煉鍛制而成,用于戰場殺敵,既有強度,又有韌性,經久耐用。現在的鏜主要是用來練功、比賽、表演,其戰場的實用性已基本忽略,用紅爐制作甚少。更為方便的是采用現代科學技術打造,如用線切割在不銹鋼板切割出造型,然后再用不銹鋼焊接起來,練功、表演時既光鮮靚麗,又隨身協調。鏜的后把也有叫后鉆的,也是同樣制作。
一般情況下,鏜頭尺寸為長三尺、寬二尺,換算成現代長度單位約為長60公分、寬40公分;鏜桿9尺,約1.8米;鏜后把(后鉆)1尺4寸,約30公分。在冷兵器團隊作戰時期,“鏜”的制式和尺寸是完全統一的。目前,“鏜”作為武術演練的器材,鏜的制作主要依據使用者的身高、力量以及其他身體素質等條件量身定制,不會再有統一的尺寸和重量的要求。鏜頭和鏜桿處有紅纓圍在四周,最初是用牦牛毛編制成。在冷兵器時代,紅櫻有兩個不可或缺的功用:一是在刺殺敵人時,特別是槍的紅櫻可讓被刺的傷口吃風,迅速讓敵流血死亡;二是牦牛毛非常瀝水,它可把敵人留出的鮮血阻擋在鏜(槍)頭出,當攔、拿、抖鏜(槍)時,迅速抖下甩出敵血,不至于流至鏜桿上而影響繼續作戰。現在鏜及槍的紅纓多為一種裝飾。
3 “鏜”的技法、功能和習練要求
鏜的基本技法有:攔、拿、扎、刺、砸、拍、砍、滑、壓、橫、挑、擋、切、捕、折、翻、撩、勾、捅、撈、咬、撥等。攔、拿、扎也是槍的基本用法,可以想象攔和拿時,鏜頭運行的軌跡卻是一個大扇面,鏜頭或帶尖、帶刃,或帶鉤、帶刺,威力無比。三刺斜月鉤鐮鏜扎出時,由于是三刃,敵方無法阻擋,遇敵阻擋則非死即傷。斜月可銷鐵如泥,鉤頭鉤人、鉤馬亦非死即傷。鏜后把(后鉆)可挑、捅、扎、砸等,其威力也比槍把的威力大的多。“鏜”具有刀、槍、劍、棍、斧、狼牙棒等兵器的功能,因此,“鏜”外形顯示出巨大威力,“鏜”既可馬上用,也適宜地面作戰,更適宜探路夜戰。由于“鏜”是長兵器,且“鏜”具有一定的重量,其使用者必定是那些體格健碩的武士。在冷兵器時期,決定戰爭勝利的主要因素就在于士兵的身體和使用的兵器,如果兩者能夠有效地結合在一起,必將給敵人造成巨大的威懾效應。正所謂:“橫鏜立馬,所向披靡”。“鏜”作為傳統器械類武術項目,在挑選運動員時,著重挑選有一定武術功底的、身材強壯、個頭稍高的健壯型的運動員。運動員平時訓練時要和其他運動員一起對基本功和其它套路的訓練,訓練結束后,還要追加身體素質及力量的訓練,特別是上肢力量的訓練。挑選后的遠動員有了一定的力量和身體素質,再練傳統器械鏜時,其動作不論是大是小,都會既表現其動作、身體的靈活性,其功架也平穩扎實。各種動作的連接,鏜的進攻、后撤、防守,都能一氣呵成。鏜不宜有太多的舞花動作,因為鏜沉重,轉身、舞花時相對不如槍靈活迅速。因此鏜的動作,體現在穩、準、狠的力道上。對于整個套路主要體現在其攻防的層次的編排上,這樣在比賽、表演時就可把傳統器械的功力的精美體現出來。
4 “鏜”的文化內涵解析
4.1 戰爭需求催生了“鏜”形制的多樣性
“鏜”的形制多樣,這是因為是在冷兵器作戰時代,作戰用兵要知己知彼,敵方如何排兵布陣,手持何種兵器,我方會根據實際情況去排兵布陣,因此各式各類的鏜就是依據敵方排兵布陣等情況應運而生,其實戰功用就體現出各有千秋。如牛頭鉤鐮鏜在大兵團作戰時,士兵們手持鏜排兵布陣在持短兵器士兵的前面,當敵兵的馬隊沖來時,可用牛頭鉤鐮鏜鏟、扎、鉤、拌馬隊,從而很好的抵擋敵兵的馬隊的進攻,又保護身后手持短兵器的兵團,免受馬隊的進攻,有利于近戰時,手持短兵器的士卒迅速參戰殺敵。
手繪圖復原實物圖,如下所示:

三刺斜月鉤鐮鏜

飛燕青龍鏜

牛頭鉤鐮鏜

彎月冀刺鏜
4.2 體現出原始的圖騰崇拜
原始社會,由于人們的認識水平低下,人類在大自然力量面前顯示的非常渺小,人們無論做什么事情都要向上天祈求,渴望得到上天的護佑。戰爭也自然地成為國家的大事,《左傳.成公十三年》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也就是說,國家要發動戰爭也必須要得到神靈的許可,如果神靈許可,則出師有名,是正義之師,會得到神靈的護佑而獲得勝利;相反,則為非義之師,必遭敗績。而對于戰爭所使用的兵器來說,先民的意識當中早就認為,如果能把自然的力量轉移到兵器中,一定會使兵器具備某種神秘的力量,以此達到最優化的攻擊效果,從而取得戰爭的勝利。基于這樣的意識,先民把一些顯示自然力量的外形炮制到兵器中,就成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即便是在當今世界里,依然會有原始圖騰崇拜的跡象。在某些仍然處于原始文化部落中,至今都有利用自然裝飾自己的濃郁習俗,他們在身上涂抹很多東西,脖子上掛滿各種自然飾品,面部和四肢還紋有各式的圖案,以此來顯示自己具備某種自然的能力。著名的哲學家黑格爾對這樣的現象早有評述,黑格爾指出:“他們的身體要用一些外在的附加物來討人喜歡”。也就說,原始的人對自然力量的崇拜是通過把自然裝飾在自己的身上,從而獲得與自然等同的某種神秘的能量。例如,從復原的四種鏜的造型來看,其中都或多或少地融入一些自然物的形態,體現出華夏先民的智慧,他們不僅要創造工具,還要琢磨自然,并把對自然認識的成果表現在他們創造的工具中,用自然裝飾工具,從而使人類創造的工具也具有自然的力量。
4.3 體現出先民對待戰爭的態度
在《道德經》第三十一章,老子對兵器有過重要的論述:“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然而,實際的戰爭又無法避免,《孫子兵法》第一句就講:“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不難看出,華夏先民即討厭戰爭,但也不害怕戰爭,他們對待武力的態度表現為“不崇武,亦不懼武”。對于農耕民族來說,豐收的季節也是最容易受到游牧民族掠奪的時刻,掠奪勢必會誘發戰爭,這一點可以在兵器的形制中尋找到一些信息。例如:飛燕青龍鏜上面有兩只造型逼真的燕子;而牛頭鉤鐮鏜則是兩對形似牛角的造型。先民認為,飛燕代表著吉祥,預示著豐收;牛則代表著勤勞和力量。把飛燕和牛角的造型融合在兵器中,有著明顯寓意,首先是告訴大家除了勤勞于農耕生產以外,還必須具備強大的武力,才能保證農耕環境的持續發展。其次,可以時刻提醒大家要居安思危,豐收的季節也是最危險的時刻,正如《道德經》第五十八章所說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4.4 道家“以柔克剛”思想的表現
無論是三刺斜月鉤鐮鏜和飛燕青龍鏜,還是牛頭鉤鐮鏜和彎月冀刺鏜。其中的明月、飛燕、耕牛都代表著某種的寧靜和溫柔,但是,在寧靜和溫柔中又蘊含著巨大的能量。月亮可以引發潮汐潮落,飛燕能夠快速靈巧捕捉獵物,耕牛則通過力量來展示強壯。先民們把一些看似溫柔的自然之物鍛造在兵器上,使得原本寒氣十足的兵器具有了生命特征,體現出農耕民族對于自然的細致觀察,先民通過對兵器的獨特認識,從而達到人、兵器、自然“三者合一”之效果。與此同時,在看似溫柔的兵器形制,卻具備了更多的殺伐功能,進一步體現了道家“以柔克剛”和“剛柔并濟”思想。這種形制的鏜就如同太極拳一樣,一動無有不動,一靜無有不靜;內固精神,外示安逸。鏜可以達到無死角的攻擊效果,實現兵器實用功能的最大化。
5 結論
鏜是中華古代冷兵器中的一員,其種類繁多。鏜在其演變的過程中除了中有刃利,兩側分股的基本結構不變外,其形制隨著戰爭和人們認識自然的深度而發生變化。人們對自然和神靈的敬畏使鏜兵器融合一些自然形態,成為表達敬畏自然的圖騰載體,鏜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中華文明基因的見證,通過鏜能夠看出華夏先民對待戰爭的態度,彰顯中華民族勤勞的品質。其形制中的飛燕、耕牛、明月等形狀使得原本寒氣十足的兵器具有了生命特征,一些自然物融于鏜兵器本身,寓意著勤勞和豐收,恬靜溫柔,表達著不崇武,亦不懼武民族精神。其次,蘊含著以柔克剛和剛柔相濟的道家文化,從而達到人、兵器、自然的和諧統一。鏜的文化內涵亦豐富多彩,能夠折射出華夏先民對自然的認識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