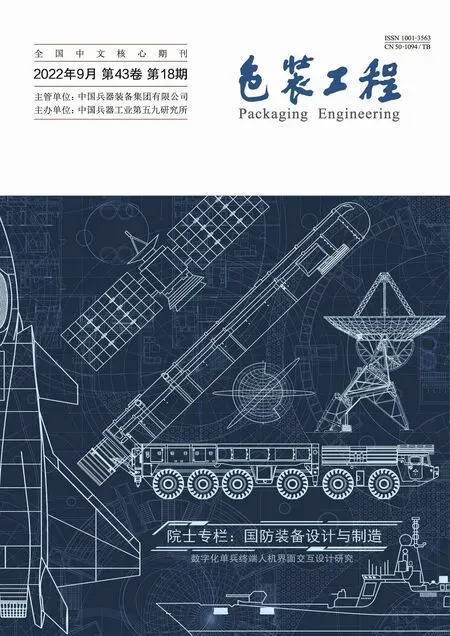古書畫裝裱綾紋樣在文創產品中的再設計研究
王韋堯,張毅,王顯穎
古書畫裝裱綾紋樣在文創產品中的再設計研究
王韋堯,張毅,王顯穎
(江南大學 設計學院,江蘇 無錫 214122)
中國古書畫裝裱藝術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探尋其裝裱紋樣的藝術特征和文化內涵,可以發掘傳統裝飾紋樣中的東方文化魅力。采用文獻與資料收集、實地考察的方法,對古書畫裝裱綾紋樣的實物資料進行收集與整理。運用轉譯與形狀文法,對裝裱綾紋樣中的典型紋樣進行一定的篩選、提取,并依據形狀文法的推演規則,對裝裱綾紋樣進行再設計,以豐富其紋樣的表現形式。結合藝術設計學理論與形式美法則,將創新設計的紋樣運用于文創產品的設計中。通過對裝裱綾紋樣進行創新,應用于文創產品中的裝裱綾紋樣,在創新設計的方法下煥發出了新的生機與活力。裝裱綾紋樣在文創產品中的設計與開發,拓寬了裝裱綾紋樣的宣傳方式,為傳統裝飾紋樣的創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宣揚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
裝裱綾紋樣;轉譯;形狀文法;文創產品;再設計
綾,是中國傳統的絲織品種之一。《說文解字》中對此解釋為:“東齊謂布帛之細者曰綾。”《釋命》里講:“綾者,其文望之如冰凌之理也。”[1]從文獻記載可見,綾是一種近于冰面裂紋的斜紋組織面料。綾自商朝起源,后世逐漸開始將其大量運用于服飾,工藝技術愈加成熟。宋代時期,在各地設立了專門制造綾的作坊,其貴重程度僅次于錦。由于宋朝的帝王對書畫十分喜愛,廣設畫院,書畫事業迎來了空前的發展階段,加之宋朝絲織業的繁榮,其裝裱工藝到達了精美成熟的時期。元代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中所記載的綾花色近30種之多,可見裝裱用綾的名目繁多[2]。明清時期,綾多用于裝裱書畫,裝裱紋樣題材和種類也愈加豐富。從織繡組織學的角度來講,書畫裝潢用綾應稱為“五枚三飛經面緞”,但在裝裱中這類面料統稱為綾[3]。明代周嘉胄在《裝潢志》中提到:“竊謂裝潢者,書畫之司命也”[4],意為裝裱的技法掌握著書畫的命運。中國古書畫之所以成為經典藝術品且代代流傳,一個關鍵的原因就在于裝裱和修復,而書畫裝裱的意義就在于書畫的保護和書畫的美觀。古書畫的裝裱形式、工藝流程及歸納考證近年來日益受到業界學者的關注,相關論著逐漸增多,然而鮮有學者對用于古書畫裝裱絲綢的裝飾紋樣進行系統研究。文章從裝裱綾紋樣的角度出發,對其紋樣的形態特點、藝術設計特征及其文化內涵進行分析,并通過一定的設計手法對其運用于文化創意產品中的可行性進行探討,為文化創意產品的跨界設計與創新開發提供新的思路。
1 裝裱綾紋樣常用題材類別
古書畫的裝裱綾紋樣題材包羅萬象,擁有獨特的風格。通過實地調查與實物圖片收集發現,裝裱用綾的紋樣題材主要有動物紋、植物紋、幾何紋、云紋及其他紋樣。其中以動物紋樣和植物紋樣最為常見,人物紋樣使用數量最少,各圖案紋樣之間相輔相成、互為補充。裝裱紋樣不僅是對書畫作品的修飾和美化,也寄托了那個時代裝裱者對這些書畫作品的全部情感。因此,為更好地挖掘裝裱綾紋樣中的文化內涵,在藝術設計學的基礎上將搜集到的圖案按自然種類劃分為以下幾類經典紋樣。
1.1 動物紋
動物紋是書畫裝裱用綾圖案中種類最為豐富,也是最重要的裝飾題材。主要以龍紋、鶴紋、鳳紋為主,還有一部分是對神祇或者其他祥禽瑞獸的描繪刻畫。
1.1.1 龍紋
龍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征符號,在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古老文明中保持著神秘、威嚴的形象,是裝飾紋樣中極有生命力的題材,富有強大的民族精神感染力[5]。從形態上看,裝裱綾中的龍紋主要有升龍、降龍、團龍三種構成形式。從呈現方式上來看,升龍呈現“龍首向上,龍尾向下”的姿態,降龍的形態則是“龍首向下,龍尾向上”,升龍與降龍往往以單元紋樣的形式出現,且每幅作品中的龍紋造型都基本相似,見圖1a、圖1b。團龍將龍作側身盤轉回旋狀,龍頭位于其中心位置,使其圖案化的感覺更強,見圖1c。龍紋自古以來就被賦予神圣威嚴的形象,象征著吉祥、如意、富貴,神龍的超然形態與崇拜思想延伸到裝裱紋樣中,凝集了中華民族的審美情趣和價值觀念。
1.1.2 仙鶴紋
除了龍紋之外,仙鶴紋亦常被用于裝裱用綾紋樣,是動物紋中典型的祥瑞禽獸類紋樣。飛鶴是仙鶴紋最為主要的表現形式,常與云紋和器物紋組成云鶴紋圖案與雜寶仙鶴紋圖案這兩大類題材。其中云鶴紋最為常見,飛鶴與祥云、連云等組成四方連續紋樣,動態神韻寫實逼真,見圖2。仙鶴在中華民族傳統審美中寓意深遠,不僅僅因其是壽星的坐騎,寓意追求長壽永生而廣為流傳,歷代文人雅士亦常以鶴為喻。裝裱者將仙鶴紋作為古書畫裝裱的經典紋樣,象征書畫家的君子氣概與隱士情節,蘊涵著古書畫作家的高潔情趣、宏大志向與人格追求。

圖1 裝裱綾紋樣中的龍紋

圖2 裝裱綾紋樣中的仙鶴紋
1.1.3 鳳紋
與龍紋類似,鳳紋在中國傳統紋飾中也有著相當悠久的歷史,自古以來便是祥瑞的象征。鳳紋在古書畫裝裱綾動物紋樣中的種類和題材最為豐富,例如南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之六《紹興御府書畫式》中多處記載了各色鸞紋綾的使用,元代陶宗儀的《書畫裱軸》中亦有“碧鸞”“白鸞”“皂鸞”等記載[6]。從形態上看,鳳紋的構成形式主要為飛鳳(見圖3a)和團風(見圖3b)。與仙鶴紋的表現形式類似,飛鳳和團鳳一般不作為單獨紋樣使用,而是與云紋、鳥禽紋、植物紋等輔助紋樣構成裝裱圖案,單元紋樣中鳳紋與鳥禽紋的數量不同,圖案的呈現方式也不盡相同,表現形式也愈加豐富多彩(見圖3c)。鳳紋因其精美細膩的造型和雍容華貴的氣質,深受中華民族的喜愛,在歷代紡織品紋樣中頻繁出現,是象征祥瑞、吉祥的圖案。
1.2 植物紋
在宋代,植物花卉類題材在絲綢紋樣中興起,成為一種時代潮流[7]。這一時代現象也順理成章地反映在古書畫的裝裱紋樣中。裝裱綾紋樣中的植物紋主要為寫實植物紋和抽象植物紋兩大類,其中以抽象類的花卉最為豐富,涉及的題材主要有牡丹、梅蘭、菊花、蓮花等。抽象花卉紋不僅僅會作為單獨紋樣呈現(見圖4a),也會與幾何紋、云紋等互相組合構成裝飾題材紋樣(見圖4b)。植物紋有時也會以纏枝花紋的排列方式出現在裝裱綾紋樣題材中(見圖4c),婉轉流暢的纏枝配以飽滿靈動的花卉,結構綿延連貫,寓意吉祥喜慶、綿綿不絕,蘊含著裝裱者的美好意愿。

圖3 裝裱綾紋樣中的鳳紋[2]

圖4 裝裱綾紋樣中的植物紋[2]
1.3 幾何紋
幾何紋在古書畫裝裱用錦紋樣中更為常見、形態更為渾厚、變化也更豐富,因而裝裱用綾紋樣中的幾何紋常常以中型或者小型的球路紋、龜背紋、“卍”字紋等形式出現,其使用數量較裝裱用錦紋樣也更少。幾何紋在裝裱用綾紋樣中,主要起兩類作用:一種是其他紋樣以幾何紋為框架,在其內部進行填充,見圖5a;另一種情況是用作其他紋樣的底紋,豐富紋樣的造型和表現形式,見圖5b。

圖5 裝裱綾紋樣中的幾何紋[2]
1.4 云紋
云紋在裝裱綾紋樣中主要是以輔助紋樣的方式呈現在織物上,常與鸞鳳、龍、飛鶴搭配,常以渦形曲線為基本構成元素。裝裱綾中的云紋通過相應的組合排列方式、構成的大小、變化多端的結構,進而形成單朵或復合形制的云紋,造型豐富多變,填飾在裝裱綾動物紋之間,襯托出神秘之感和祥瑞之氣,見圖6。
1.5 其他紋樣
在裝裱綾紋樣中,還有少部分其他紋樣,例如文字紋樣、人物題材等。文字紋樣出要以“壽”字紋和“卍”字紋為主。例如,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館藏的清代《唐苑嬉春圖》(見圖7a),其手卷天頭的裝裱紋樣是由團壽紋和古錢紋相間,以四方連續的樣式排列而成。團壽紋外圈為五只寫意變形的蝙蝠,紋樣組合成五“蝠”捧壽的樣式,寓意多福多壽、福壽安康、福財齊全。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館藏的清代《仿黃公望山水圖》(見圖7b),其圖案由蓮花與童子共同構成,奔跑追逐的童子手執蓮花在纏枝間嬉戲玩耍,在傳統觀念中有祈求子孫興旺、多子多福的吉祥寓意。

圖7 裝裱綾紋樣中的其他紋樣[2]
2 裝裱綾紋樣的文化內涵
中國傳統紋樣在發展過程中很大意義上實現了內涵與寓意的升華,映襯著時代文化的特質[8]。裝裱綾紋樣種類豐富多彩、風格獨特,體現出東方獨特的裝裱特色與文藝之美。它不僅僅承載著先祖共通的思維模式與價值觀念,同樣凝聚著千百年來人們的理想信念和審美追求,其紋樣也展現出多元化的文化內涵。
2.1 歷代文人的情感寄寓
如果說書畫作品代表歷代文人雅士的藝術水平,裝裱就是襯托其作品的必要因素,裝裱紋樣自然就是裝裱織物中最為重要的元素。將生活的種種向往都編織在了紋樣里,如珍禽瑞獸寓意富貴吉祥、梅蘭花卉象征純潔、孩童幼子與多籽類植物共同搭配組合,象征多子多福,各類紋樣常以吉祥、平安、富貴立意。裝裱紋樣的選擇不僅僅是歷代文人對自身作品情感價值的提升,同樣寄寓著他們超塵拔俗的風骨神韻和精神品格,使之成為自身道德倫常的載體。
2.2 裝裱藝術的造詣載體
《裝潢志》有云:“裝裱優劣,實名跡存亡系焉”[4],意為書畫裝裱質量的優劣直接決定著書畫的存亡與否,也間接代表了裝裱師獨具慧眼的裱畫技藝。高超的裝裱師對裝裱時間、裝裱對象、裝裱細節都有著精確的把握,通過手、眼、心三者的完美配合,才能完成一幅精美的作品。每一幅作品都承載著裝裱師精湛的技藝和高深的造詣。精致的裝裱技法與裝裱藝術,開拓出一種展示書畫作品并供人談論賞玩的別具一格的社交方式,提升了人民的審美品味。原本僅以防潮防損為功用的裝裱技藝,如今早已發展為展示東方文化的載體。
2.3 民族風韻的文化符號
古書畫裝裱用綾紋樣不似其他服裝用織物,不同歷史時期的圖案風格、紋樣布局、紋樣造型等細節部分有著不同的年代特征[9]。自魏晉南北朝時期起,《論書表》開啟了對中國古書畫裝裱藝術的研究。從最原始的簡素的帛畫書卷到宋代名聲顯赫的“宣和裝”再到如今風格各異的裝裱流派,中國古書畫裝裱憑借其裝裱品勢的多樣性和濃厚的文化底蘊在藝術領域占據一席之地,形成了鮮明的中國特色。這不僅是一份值得珍視的中華文化遺產,同樣也是積淀民族審美與文化熏陶的代表符號。
3 裝裱綾紋樣在文創產品中的創新設計及應用
創意產品設計通過借助中華民族所特有的傳統文化與豐厚的歷史積淀,且兼備形神交融的特征,可以全方位加速我國文化創意設計產業的發展[10]。近年來,北京故宮博物院憑借其精準的用戶定位及結合傳統文化的創新設計,在市場上廣受歡迎,擴大了故宮文創的國際影響力[11]。將傳統文化元素與現代設計藝術進行有機融合,不僅是歷史的潮流趨勢,也是未來藝術設計主要的發展方向之一。裝裱紋樣在書畫裝裱藝術中同樣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通過現代設計手法及理論支持,將裝裱綾紋樣進行重新整理與設計,并融入產品設計中,進而設計出兼具美觀造型與實用功能、蘊含民族精神和審美藝術的文化創意產品,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3.1 裝裱綾紋樣創新設計的應用框架
依據相關應用流程,對裝裱綾紋樣中的創新設計進行歸納總結,應用框架見圖8。該框架主要包括三部分:
1)首先是對裝裱綾紋樣及其內容背景的研究,同時對其紋樣的種類進行一定的概括總結,分析各個紋樣的呈現方式和特征,并進行文化內涵的分析。
2)其次根據典型目標,從中篩選出具有代表性的紋樣,運用創新設計方法,進行圖形的再設計與紋樣轉化。并推演出新的紋樣基本單元和組合形式,通過美學規律與審美認知的重新架構以獲得新的圖案。
3)最后根據衍生后新紋樣的形態,將其應用于文創產品設計,得到創新應用方案。
3.2 基于轉譯和形狀文法的裝裱綾紋樣設計
轉譯從生物學上來講,是指以脫氧核糖核酸(DNA)轉錄得到的信使核糖核酸(mRNA)為模板,合成具有一定氨基酸順序的蛋白質的過程[12]。從藝術設計學角度來講,轉譯可以理解為以傳統紋樣為初始模板,通過一定規律性的設計,將原始紋樣轉化后結合成新紋樣的過程。筆者選取五類經典的裝裱綾紋樣,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仙鶴紋、雜草紋、蓮花紋、菊花紋等結合現代圖案設計法進行再設計,在保留原有特色不變的基礎上進行夸張、抽象處理并進行元素的提取和轉譯,創建出新式紋樣,使其符合現代審美,將其概括匯總后以建立相對應的設計因子庫,見表1。

圖8 裝裱綾紋樣創新應用框架
表1 紋樣設計因子庫

Tab.1 Pattern design factor library
經過紋樣的提取和轉譯后,形狀文法也可以更好地輔佐紋樣的轉化與再設計,實現了新圖案的自動生成。形狀文法由George Stiny和James Gips最早提出,最先將其應用于繪畫與雕塑創作中,后擴展到建筑設計、品牌形象設計和產品圖形的創新設計等領域中[13]。形狀文法依據平移、旋轉、鏡像等特定的演變方式,改變紋樣形態特征,在延續原有圖案特征的基礎上,獲得豐富的創新圖案。以字母“F”為例,根據形狀文法紋樣演化規則,得到延伸圖形。其中的規則1為平移,規則2為水平鏡像,規則3為垂直鏡像,規則4和規則5分別放大與縮小,上述規則稱之為生成性規則。將生成的基本圖形持續按照推演規則進行衍生,進而獲取更加豐富的新圖案,此過程稱為衍生性推演[14]。衍生性推演如下:規則6為45°傾斜鏡像,規則7為繞自身中心點旋轉15°,規則8為繞中心軸旋轉15°。紋樣演化規則見表2。
將上述設計因子庫中提取紋樣,通過一次或多次的推演,生成基礎紋樣單元組合,其演化設計見圖9。
表2 裝裱綾紋樣的形狀文法推演規則

Tab.2 Damask mounting pattern evolutionary rules of the shape grammar

圖9 基礎紋樣推演
3.3 裝裱綾紋樣在文創產品中的創新應用實踐
傳統文化是我國民族文化的珍貴財富,其內容豐富、形式多樣,以此為題材的文創產品占據了很大的市場份額[15]。不管是動物、植物還是其他紋樣,其背后所蘊含的傳統韻味和文化價值,彰顯了所處時代的社會思潮和時代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民族特質的有效發揮。基于以上認識,在現行設計因子提取方法的基礎上,筆者提出了一種基于現代文創市場需求的傳統紋樣設計因子提取方法,以幫助其更好地適應當下市場中文創產品的設計與實踐活動需求。將裝裱綾紋樣中提取出的各類經典紋樣結合設計因子庫中最小單元紋樣進行設計,通過形狀文法進行多次變換、組合,得到新的紋樣圖案。來源于書畫裝裱的紋樣,將其應用于文創中,別有一番文藝氣息。通過上述紋樣的提取、轉譯與推演,創新設計后的紋樣效果圖見圖10。

圖10 創新紋樣效果圖
筆者選取元素造型簡練淳樸的鶴紋作為主紋樣,其圖騰寓意更偏向吉祥如意的民族文化特質。選取幾何紋作為框架,搭設出層次分明、錯落有致的構圖空間,便于紋樣的填充和歸置。與此同時,對設計因子庫中象征“君子”的菊花、蓮花、蘭花的傳統紋樣進行再設計后,與鶴紋相互呼應,以“鶴鳴之士”的寓意象征賢明高潔的才子氣息。創新圖案的紋樣摒棄了古書畫裝裱綾紋樣中的古板造型,在轉譯與形狀文法的創意設計下,紋樣動態豐富、栩栩如生,寓意吉祥,符合現代審美需求。在圖案的色彩處理上,選取黃綠色為主色,白色、藍色和深紫色為輔助色彩,以紅橙色作為細微點綴,整體設計效果簡約時尚又不失層次感,色彩溫和舒適,風格典雅舒適。基于以上圖形的創意設計,將其運用到現代文化創意產品設計中,得到既契合現代人群審美特點又不失傳統設計語言的新產品,基于形狀文法的刺繡創新設計應用案例見圖11。方形的圖案設計應用范圍廣泛,將其作為單獨紋樣進行呈現,可以用于帆布袋、馬克杯、筆記本這類生活辦公用品當中;若將其以適合紋樣進行呈現,亦可適用于方形絲巾或者方形的抱枕枕套等紡織品圖案設計中,以及胸針、手機殼這類小物件的圖案造型設計中。創新圖案的工藝表現以數碼印花、貼圖膠印為主要手法,在適應產品造型的同時適用于工業化、批量化、流水化加工。創新設計下圖案的適配性和市場化推廣得到了很好的展現,完美契合民族風與時代感的同時,滿足了消費者追求傳統紋樣中藝術文化內涵的心理訴求。

圖11 創新紋樣應用
4 結語
裝裱綾紋樣的發展依托于中國傳統古書畫近兩千年的裝裱工藝歷史,隨著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底蘊與審美經驗而形成,獨具民族風格與藝術傳統。文章以裝裱綾紋樣為例,運用轉譯與形狀文法在傳統紋樣中進行推演與再設計,淡化傳統裝飾圖案在文創產品中應用不和諧等問題。該方法在保留了傳統紋樣特色的同時獲得了大量創新方案設計,易形成統一的風格,提供了一個可行且靈活的設計方法,潛移默化地推廣與傳播了中華優秀傳統紋樣。程式化的設計方法便于計算機實現預設的規則,為傳統織物紋樣的計算機輔助設計引入提供了良好的基礎。該設計思路同樣也適用于其他傳統織物的紋樣設計或是傳統圖案的設計再創新,更加復雜的紋樣或圖案也可以應用此方法獲得更多的方案選擇和拓展路徑,以此來更好地滿足市場消費者的多樣化需求。
[1] 宗鳳英. 中國織繡收藏鑒賞全集[M]. 長沙: 湖南美術出版社, 2012: 41.
ZONG Feng-ying. Collec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Embroidery[M]. Changsha: Hun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12: 41.
[2] 趙豐總, 顧春華. 中國古代絲綢設計素材圖系-裝裱錦綾卷[M]. 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7: 14-145.
ZHAO feng-zong, GU Chun-hua. Ornamental Patterns from Ancient Chinese Textiles Mounting silks[M].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14-145.
[3] 傅東光. 乾隆內府書畫裝潢初探[J].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05(2): 111-140, 160.
FU Dong-guang.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the Mou-nting Paintings Art from the Palace Household in the Qianlong Reign[J]. Palace Museum Journal, 2005(2): 111-140, 160.
[4] 周嘉胄. 裝潢志圖說[M]. 濟南: 山東畫報出版社, 2003: 9.
ZHOU Jia-zhou Decoration History and Illustration[M]. Jinan: Shandong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2003: 9.
[5] 孫征, 聶瑞辰. 龍紋的流變[J]. 裝飾, 2001(2): 62-63.
SUN Zheng, NIE Rui-chen. Evolution of Dragon Pattern[J]. Art & Design, 2001(2): 62-63.
[6] 顧春華. 古書畫裝裱綾之鳳紋圖案研究[J]. 絲綢, 2014, 51(8): 33-39.
GU Chun-hua. Study on Phoenix Pattern of Twill Damask Used for Moun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J]. Journal of Silk, 2014, 51(8): 33-39.
[7] 趙豐. 中國絲綢通史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silk[M]. 蘇州: 蘇州大學出版社, 2005: 257.
ZHAO Feng.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silk[M]. Su-zhou, China: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2005: 257.
[8] 相靜. 論中國傳統紋樣在包裝設計中的應用[J]. 包裝工程, 2020, 41(6): 286-288, 292.
XIANG Jing. On the Applic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atterns in Packaging Desig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0, 41(6): 286-288, 292.
[9] 顧春華. 基于絲綢紋樣對中國古書畫裝裱絲綢織物年代的研究[J]. 藝術設計研究, 2018(2): 105-111.
GU Chun-hua. Research on Age of Silk Fabrics for Mo-un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Based on Silk Patterns[J]. Art & Design Research, 2018(2): 105-111.
[10] 王偉偉, 胡宇坤, 金心, 等. 傳統文化設計元素提取模型研究與應用[J]. 包裝工程, 2014, 35(6): 73-76, 81.
WANG Wei-wei, HU Yu-kun, JIN Xin, et al.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Extraction Model of Traditional Culture Design Elements[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4, 35(6): 73-76, 81.
[11] 梁淑敏. “互聯網+”背景下北京故宮文創的開發設計與推廣研究[J]. 包裝工程, 2020, 41(8): 309-312, 316.
LIANG Shu-min. Development Design and Promotion of Beijing Palace Museum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0, 41(8): 309-312, 316.
[12] 馬皎. 寧強羌族刺繡紋樣的轉譯與創新設計研究[J]. 包裝工程, 2018, 39(20): 22-28.
MA Jiao. Translation and Innovation Design of Ning-qiang Qiang Embroidery Patterns[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8, 39(20): 22-28.
[13] 王偉偉, 彭曉紅, 楊曉燕. 形狀文法在傳統紋樣演化設計中的應用研究[J]. 包裝工程, 2017, 38(6): 57-61.
WANG Wei-wei, PENG Xiao-hong, YANG Xiao-yan. Application Study of Shape Grammar in Evolutionary Design of Traditional Patterns[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7, 38(6): 57-61.
[14] 王寧鑫, 詹秦川. 基于立春節氣的文創產品設計方法[J]. 包裝工程, 2019, 40(6): 257-263.
WANG Ning-xin, ZHAN Qin-chua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Method Based on the Beginning of Spring[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9, 40(6): 257- 263.
[15] 劉洋, 門夢菲, 田蜜, 等. 文創產品的創新設計方法研究[J]. 包裝工程, 2020, 41(14): 288-294.
LIU Yang, MEN Meng-fei, TIAN Mi, et al. Innovative Design Method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0, 41(14): 288-294.
Redesig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Mounting Damask Pattern i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ANG Wei-yao, ZHANG Yi, WANG Xian-ying
(School of Design, Jiangnan University, Jiangsu Wuxi 214122, China)
The art of mounting Chinese ancient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refore, exploring the artistic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ts mounting patterns can discover the charm of oriental culture in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This research collects and sorts out the physical data of ancient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mounted with damask patterns using the methods of document and data collection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Using translation and shape grammar, the typical patterns in the framed damask pattern are screened and extracted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the framed damask pattern is re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deduction rules of the shape grammar to enrich the expression form of the pattern. Combining the theory of art design and the law of formal beauty, the pattern of innovative design is applied to th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y innovating the pattern of the mounting damask pattern, the innovative design method applied to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radiates new vigor and vitality.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mounting damask patterns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roadens the propaganda methods of framed damask patterns, provides new ideas for the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and promotes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mounting damask pattern; translation; shape grammar;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redesign
TB472
A
1001-3563(2022)18-0302-09
10.19554/j.cnki.1001-3563.2022.18.036
2022–04–26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群研修研習培訓計劃項目(文非遺發[2017]2號);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立項一般項目(19WMB040);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19YJA760068)
王韋堯(1996—),男,碩士生,主攻服飾文化與藝術設計。
張毅(1967—),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家紡服飾面料設計與文化。
責任編輯:馬夢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