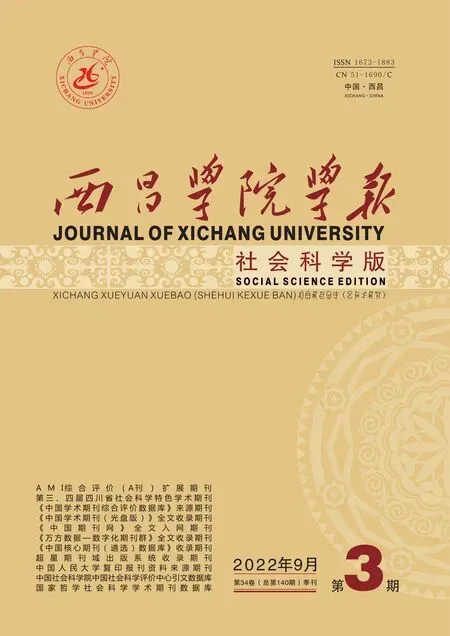民國時期涼山彝區的保哨制度研究
李久旺,馬廷中
(西南民族大學旅游與歷史文化學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本文所敘述的涼山彝區,是指現今的涼山彝族自治州,民國建立以后,將涼山歸入四川省第十八行政區;1939年西康建省后,涼山劃入西康省,成為西康省寧屬地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涼山彝區的保哨制度是晚清時期建立,民國時期興起并衰落,后隨著新中國的建立而終結的基層軍事保護制度。關于保哨制度,民國時期的考察資料均有提及,但學界現在尚無專門的研究,因此本文希冀全面闡述保哨制度在民國時期涼山的運行概況,以及該制度所帶來的影響,這不僅有利于推動民國時期涼山地區政治史的研究,也從側面反映出民國時期涼山地區的民族問題,為現今邊疆治理及提供借鑒和反思。
一、保哨制度建立的歷史背景
涼山地區位于四川省的西南部,西跨橫斷山脈,東抵四川盆地,北負大渡河,南臨金沙江。涼山東部為山地區,西部為高原區,西有大雪山脈,東有大涼山脈,兩大山脈相對峙[1],這也就造就涼山地區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
(一)社會秩序混亂、民族關系緊張
元代以后中央政府在涼山實行以土司制度為主的“間接統治”的治理方式。清政府雖然在涼山的沙馬、雷波、吞都、黃螂、建昌等地設置營壘,派遣流官,革除了當地部分土司、土官[2],但是清政府在涼山腹心地區還是主要實行以土司制度為主的羈縻政策。民國時期,民國政府延續改土歸流的治理政策,在民族地區推行國家一體化的政策。當以流官為主的政府沒有發揮治理效用的情況下,隨著政局變動,在川康滇三省交界處的涼山地區,各種軍閥此消彼長,使得民國政府對于涼山一帶的管理大多時候是處于“真空”狀態。而西康的地方軍閥又承襲清代民族壓迫政策,根據嶺光電的回憶,“那時,社會秩序很亂,彝漢互相拉搶。經常見彝人被捆著,在凄厲的號聲引導下,牽游田壩街,最后拉到小河子去殺。也常聽說某某處的漢人被搶了”[3]。當時涼山彝區社會的混亂,再加上軍閥的剝削和壓迫,使得涼山地區民族關系緊張,從而導致道路不寧,這也成為保哨制度興起的社會因素。
(二)民國時期彝族的等級社會
在涼山地區,彝族依照血統以及建立在人身隸屬關系基礎之上的義務性侍奉與庇護原則將社會成員嚴格劃分為茲莫、諾伙、曲諾、安加和呷西五個等級[4]。其中茲莫(土司)、諾伙(黑彝)是奴隸主統治階級。而曲諾(白彝)、安加(安家娃子)、呷西(鍋莊娃子)是被統治階級。而彝族的奴隸主,為了積累更多財富,不斷外出搶劫,擄掠人口將其作為自己的“娃子”,光緒《越嶲廳全志·邊防》載黑彝“專掠漢人代耕”,在擄掠的人口中,既有本族人口,也有漢族等其他民族人口[5]。彝族奴隸主這種掠奪人口作“娃子”的做法也延續到民國時期,1917年,云南護國軍入川,有一營駐扎在越嶲,后因戰事被迫退入涼山,全營官兵均被擄為奴隸[6]。
民國政府長時間的無效管理,地方軍閥的民族壓迫政策,造成當時民族關系的緊張,加上彝族奴隸主掠奪人口去做“娃子”,這種混亂的社會秩序造成涼山以政府為主導的保哨制度出現。保哨制度的出現也從本質上反映了民國時期涼山地區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
二、涼山彝族保哨制度的概況
“哨”字有巡邏、警戒防守的崗位之意,“哨口”指的是軍隊巡邏瞭望的關卡、崗哨。因此“保哨”一詞有濃厚的軍事色彩。“保哨”是晚清至民國時期的地方政府為保護主要交通道路上人馬過往安全,防止行旅被搶劫掠奪,在道路的主要關口設置保哨點,派人員持槍保護。人馬過往時,必須給保哨人員繳納一定的保哨費[7]。保哨制度實際上緣起于涼山彝區的“保頭制”[8]。所謂保頭制,商旅以適當的報酬,請黑彝首領或其指定的代表,作為“保頭”(即保護者),護送商旅經過一定的路程。商人往往以所運貨品的一定百分數,或按雙方議定數目,送以若干銀子[9]。保哨制度和保頭制雖然都是保護行人通過涼山彝區,但是兩者之間還是存在較大的區別,保哨制度是政府官辦,由軍方派人或者委派黑彝保護行旅通過涼山彝區的主要交通干線。而保頭制實際上是屬于民間性質的制度,個人去請黑彝作為“保頭”,通過“保頭”的擔保則可以通過涼山彝族的腹心地區。因此保哨制度和保頭制度在涼山彝區是相輔相成的,民國時期行旅經過涼山彝區時,由哨所的哨兵負責保護行旅在主要交通干線的安全,但是由于涼山區域很廣,在偏離主要交通干道以后,就由“保頭”負責保護行旅的安全。
(一)保哨的形式
保哨制度在涼山彝區分為兩種形式,一為看哨,二為送哨。
看哨:是指在涼山彝區的主要交通線險隘處設置固定哨卡,哨卡是由投誠的彝族黑彝或者漢人軍隊負責,派人守哨看哨,負責這一路的安全。清光緒十五年,寧遠府規定,看哨支頭黑彝,實行輪流到縣府坐質聽差,由政府每月發給彝餉、哨丁口糧,哨費按規定收取。凡行旅商販過客必須納清哨費始能通過,這種制度被民國繼承[10]。
送哨:與保頭制比較類似,送哨的士兵由負有哨務責任者集結,從某地起至某地止地段內,護送行人通過。最初專門護送公務員、傳教士通過險要地段。之后由于商旅往來頻繁,于是開始收取護送費,并將其作為送哨士兵的口糧[11]。送哨也有時間限制,不是隨時都可以護送行旅通過。抗戰時期,涼山地方政府規定陰歷一四七為哨期,屆時客商行旅,結伴大幫同行,由十七師派兵荷槍護送[9]289-290。
(二)哨所的分布
涼山彝區的哨所設置源于晚清咸豐二年,冕寧縣屬的哈哈、藥瀘口、棉紗灣等地區設立哨所,由當地彝族家支分段負責保護,官府給予糧餉[12]。之后陸續設立諸多哨所,如表1、表2所示。
哨所的分布規律主要分為兩方面,一是哨所基本上設置在各地通往縣城以及外省道路的關鍵路口,通過表1可知,西昌、會理、鹽源、寧南、鹽邊、昭覺、越西、冕寧等各縣之間的道路上均有哨所設置。二是設置的哨所也較多的設置在地勢險要的地方,“這制度的原則,是在地勢比較險要(多半是山口)、匪徒最容易出沒的地點,設立哨口”[13]。由表2可知,鹽源附近的黃臘溝、黃草壩、扎拉山、觀音巖等地勢險要之地均設置了哨所。哨所的此種分布規律不僅有助于保護行旅安全通過,也起到了緝拿盜賊的作用。由于保哨制度并沒有形成完全穩定的哨所分布位置,很多哨所時興時廢,故而不能將涼山地區的哨所進行一一的考證。

表1 晚清至民國涼山彝區的部分哨所設置情況[11]572

表2 鹽源縣主要哨所設置表[10]35
(三)保哨制度的運行
保哨制度的運行主要是由行旅出一定的哨費給哨所的哨兵,由其保障行旅安全地通過涼山彝族的部分地區。因此保哨制度的運行主要是依靠兩個方面,第一是行旅的保哨費,第二是哨所中哨兵的能力。
關于保哨的費用,在民國初期,如果是行旅往來,如販運商貿,每擔征收哨費五分至八角不等,或者是當地保甲派人監察征收,或者是報請備案規定征收標準,由各哨所自行征收。其征收的標準以各哨所的哨兵人數來確定,每月的收入,大都做哨兵的口糧,有時也會一部分做保甲經費、義渡經費、質夷經費。馬幫走過的時候,每匹馬按規矩付一定數額的哨錢(一般是幾角錢到一塊錢);步行的旅客,減半收費。這筆費用,凡是雇馬的,照例歸馬主擔負,由馱價內支付[13]。哨兵的來源分為兩種,一種是在涼山彝區生活的漢人,另一種是當地的彝人。彝漢哨兵所需的哨費也有差別,鹽源、鹽邊、木里間送哨者,均為彝人擔任,白水河、天久哨為當地漢人擔任。彝人送哨,大多是在本家支境內往來,因此派遣哨丁護送行旅,只需要派遣幾人,便可完成任務,因此彝人負責的哨所征收哨費比較少。而漢人送哨,則需要招募哨丁,至少數十人,才能擔任,保哨的地段往往長達數十里,故其保哨費,特別奇重[9]61。如果是帶有官方背景的人員通過,就可以免征哨費,“凡過往客商,到了哨口,就得付一筆保哨費。曾昭掄他們的考察團,因為是半官方性質,沿途哨錢,也就基本免了”[14]。抗戰以前,物價平穩,各地哨所照政府規定的標準進行征收,勉強能維持供養哨兵口糧。抗日戰爭以后,物價飛速上漲,多處哨所收入常不敷開支,在無形之中被裁撤[11]572-573。
哨兵的素質和能力,在保哨制度的運行過程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哨所中哨兵的多寡以及軍事能力對行旅的安全至關重要。當哨兵多且軍事能力強時,行旅能夠安全舒心地通過主要交通干道。鄧秀廷當總團后,召集當地彝支頭人會商,明確責任,后來修筑碉堡,增加崗哨。經過幾年整頓,小相嶺至瀘沽段暢通無阻。經過保哨護路,鄧秀廷名氣大長[12]。如果是在當地彝人擔任保哨的地段,“西康建省以后,地方當局,雇用此等熟夷放哨,行旅更感安全”[9]。相反,當哨所的哨兵軍事能力不足時,也會給行旅的安全造成極大的隱患。1928年,有大商人運貨27馱進西康,請駐軍二連保哨,小商販隨之而行者凡十余人,詎至大相嶺,有匪六七十人出劫,與保哨軍隊激戰,飛彈如雨,哨兵敗潰,商人皆委貨逃走。匪去后,商人回看貨物,只粗重不值錢者在道[15]。因此,保哨制度并不能絕對地保障行旅的安全,更多的是起到了一種保險的作用。
(四)保哨制度的衰落與終結
民國時期政局動蕩,地方政府無法對涼山地區實行有效的管理。1927年,劉文輝打敗劉成勛后,其勢力成功進駐涼山地區。此后,涼山地區便歸劉文輝管轄。但是劉文輝在“二劉之戰”①失敗之前,劉文輝的重心主要是為了獨霸四川,因此對涼山地區的投入有限[16]。在混戰失敗退守雅安后,劉文輝實力大幅削弱,對涼山地區的統治更是力不從心。直到1939年,西康建省以后,隨著寧屬屯墾委員會以及西昌行轅的建立,民國政府對于寧屬地區才進行相對有效的管理。人們執行一項制度的自覺性主要依賴于制度的權威性,而制度的權威性又依賴于制度的合法性[17]。前文所言,政局動蕩下的涼山地方政府無法對彝區實行有效的治理,這也就導致了保哨制度在彝區運行的權威性大打折扣,無法賦予足夠權威性的保哨制度也就開始走向衰落。保哨制度的運行開始亂象頻出,“保哨”價格高昂,哨所林立,收費而不保護行旅,淪為軍閥籌集軍費,地方政府征收雜稅的名目,這里將在后文消極作用中詳細闡述。針對上述哨務問題,1943年,西康寧屬屯墾委員會對涼山彝區的哨務進行整頓,裁撤不必要的哨所、哨所停收保哨費、讓更多彝人承擔保哨任務等等,但是效果并不顯著。1950年涼山解放以后,民族關系得到極大的改善,涼山彝區社會秩序穩定,道路安全,保哨制度在無形中終結。
三、保哨制度的影響
保哨制度在民國時期涼山彝區的發展及其運行,其消極作用占主導。當然保哨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涼山地區與外界的交流交往成為可能。
(一)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涼山彝區的經濟發展
由于民國政府無法妥善處理民族問題及社會問題而導致涼山彝區道路上的掠劫行為頻出,因此保哨制度在涼山彝區的實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道路的通暢,如從西昌至禮州這二十余公里左右的路面,常有盜匪出沒,陷于中斷。后由兩個黑彝家支出面護路保峭,遂保證了這段路暢通無阻[18]。道路的暢通對涼山彝區對外經濟交流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以瀘沽為例,瀘沽是涼山到昆明、去成都必經之地,同時也是一個大站口,但是路途中盜匪猖獗,許多地方設立有“保哨”后才能通過,因而在民國時期瀘沽保持了往日的繁華熱鬧景象[19]。由此可見,保哨制度的運行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涼山彝區的經濟發展,間接促進了民族之間的交流交往。
(二)成為軍閥征收雜稅的名目和壯大的政治資本
保哨制度在后期成為涼山地區行旅、商人的負擔。保哨制度規定,哨費由各個哨所自行征收,從而導致“各哨所自由征收哨費之漫無限制,各地方官署,亦明知弊病百端,而不設法解決”[10],再加上地方政府的管理不善,使保哨制度百弊叢生。哨所能夠自行決定哨費的多寡,不少哨所存在收費很高的問題。民國時期麻隴的煙會有三條路可以通往,這三路都由普威吉土司安排麻隴本地彝民碼頭護送,進出哨的過路人都要在哨點等齊,交費后放行,收費高,一般是貨物價的2~3成。保哨中被搶劫,哨丁仍不負責。哨所的人多與搶匪串通[20]。這種情況下,保哨制度的運行不僅變成行商沉重的負擔,而且哨所的哨兵與劫匪勾結,嚴重威脅商旅的人身財產安全。這也讓保哨制度在無形之中已經失去原有保護行旅的理念。而哨所也開始演變成征收雜稅的關卡,鹽源至西昌和鹽邊主要通道,由駐軍或保商隊看哨,收取護商費、保哨費,實際只收費不保哨[10]34。在抗戰時期,據《川邊季刊》寧屬記實一文載,在行商稅目中即包括保哨費,“哨保:民國14年道路不靖,商人自動請兵護送貨馱,酌予保費。民國15年初,軍方主動抽收,派兵護送,15年末,即收費而不派兵,每貨一馱征洋一元至三元。”[21]這種收費而不保護商旅的行為,讓“保哨費”變質成苛捐雜稅的名目。自西昌至三灣河有十多個關卡。保頭費、保哨費和運費一起相當于成本的50%[22],原本自愿繳納保哨費的“保哨”,已經變成明令正稅之外強征的雜稅,成為行旅、商人沉重的負擔。
民國時期,“保哨”也開始成為涼山地方軍閥發展壯大的政治資本。民國11年(1922年),鄧秀廷打起維持地方治安,保護過往行旅客商的旗號,利用手下民團武裝,插手保哨護路,定下每旬三、六、九為“保哨日”。鄧秀廷親自帶領團丁上路,對集結在山南冕山站的行旅客商收取保哨費,護送商旅經過冕山站起程,經深溝、登相營、九盤營、龍潭溝、相嶺頂,直到小相嶺北越西境內的小哨站,此舉一出,很快得到地方政府的嘉許。鄧秀廷于是以維持治安,保哨護路為由,名正言順發展民團,擴大勢力,理直氣壯向地方征糧派款,抽稅收捐[23]。鄧秀廷借保哨起家,成為涼山一帶有名的軍閥。涼山一些軍閥勢力也開始胡亂設置所謂的“哨所”,名為哨所保哨,實以征收保哨費的名目大肆斂財。民國36年(1947年)7月,李明揚為籌措武裝經費,以“保證交通安全,防范土匪滋擾”的名義,在方村堙口(馬烈鄉境)設立哨所,向過往車輛行商索取“保哨費”[24]。這種保哨不僅無法保障行旅在涼山一帶的安全,反而演變成大小軍閥籌集軍費的手段。
(三)造成民族關系緊張
保哨制度的實施造成民族關系進一步的緊張。民國初年,越西縣知事張英因為翻譯問題錯殺一名彝族婦女,并令將首級懸于西門城樓且不準親屬收尸。這引起了其所在家支的震怒,阻斷小相嶺交通。張英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建立起保哨制度。即逢每月的三、六、九日為哨期。1918年年底,客商及行人較多,駐扎在越西的川軍第四師宿靖南團派出一個連的武裝部隊護送。客商、行人及士兵400多人行至三板橋時,遭到叢林中的近千名彝人伏擊。由于突然襲擊和短兵相接,護送部隊完全失去了戰斗力,不到半個小時,300多人尸橫荒野。此次事件,震動了寧屬及省里。省、縣派員調查處理善后。經過與彝人談判達成了協議:不追究此次事件的肇事者;彝人交出被俘士兵及商旅和機槍;小相嶺的交通安全由彝人負責。此后,道路通暢[25]。由此可見,“保哨”實質上就是民國地方政府處理民族問題不當造成民族關系緊張產生的制度。這種因民族關系緊張、社會秩序混亂而誕生的制度,不僅沒有緩和民族關系,反而讓民族矛盾加劇。
四、結語
清末民國時期涼山地區的保哨制度,是清末民國改土歸流以來,地方政府沒有完全發揮有效作用,再加上地方軍閥實行的民族壓迫政策導致涼山彝區社會秩序混亂的產物。保哨制度的運行離不開政府和軍方的支持,需要政府在道路的主要關口設置保哨點,派人員持槍保護。然而民國地方政府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在涼山彝族地區建構出合理有效的管理辦法和治理模式,再加上政局動蕩,保哨制度的衰落便不可避免。保哨制度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保障彝漢之間的經濟交流,但是其本質上是民族關系緊張的產物,不僅成為地方政府及軍閥征收苛捐雜稅的名目,而且進一步激化當時的民族矛盾。由此可見,政府在對少數民族地區推行邊疆內地一體化的過程中,樹立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民族共同繁榮的意識,為民族地區治理奠定思想基礎。同時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治理需要建立合理的管理機制,變革不合理的傳統社會制度,構建和諧良好的民族關系,這才是民族地區社會問題解決的根本之道。
注釋:
①1932—1933年,四川軍閥劉文輝和劉湘為爭奪四川的控制權而爆發的戰爭,該戰爭以劉文輝失敗退守西康,劉湘成為四川省主席而告終。由于劉文輝和劉湘都是劉姓,故稱“二劉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