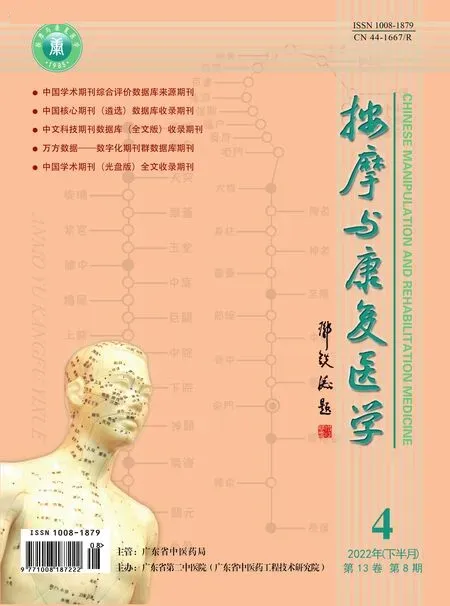基于數據挖掘的治療功能性便秘取穴規律分析
黃仲遠,趙 偉,趙 波,夏子昊,徐定濤,胡 驍,佟昊琛,徐心尉,彭德忠
(成都中醫藥大學,四川成都 610075)
功能性便秘(Functional Constipation,FC)也稱單純性便秘或習慣性便秘,以持續性排便困難、排便間隔延長或排便不盡感為特點[1]。老年人群受生理功能衰退、活動量下降等因素影響,已成為便秘的主要發病人群[2-3]。針灸推拿被用于治療胃腸功能障礙疾病歷史悠久,隨著基于循證醫學原理的臨床RCT研究報道相繼發表[4-6],針灸治療FC的作用機制也越來越清晰。然而,臨床試驗選穴不統一,難以為臨床操作和試驗研究提供可靠的取穴依據。故本研究通過收集近5年來的臨床研究文獻中針灸治療FC的處方取穴,運用數據挖掘方法,對其取穴規律進行分析與總結,為臨床進一步優化FC的針刺防治方案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現代臨床醫學文獻的研究范圍為2015~2020年期間中國國內期刊公開發表的中醫、針灸相關的醫學雜志。
1.2 文獻納入與排除標準
1.2.1 文獻納入標準①研究對象:明確診斷為FC的患者;文獻中缺乏明確診斷標準,但作者明確敘述患者癥狀與FC相符。②干預措施與比較措施:治療組干預措施主要為常規針灸療法(包括毫針或光電熱等形式的刺激),并設立了有別于治療組的對照組。③結局指標:本研究采納所有納入文獻使用的療效評定標準。
1.2.2 文獻排除標準①文獻類型:單個病案、驗案報道、評論、綜述及專家經驗類的文獻,以及動物實驗研究類的文獻;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為兒童功能性便秘患者的文獻。③干預措施:未論及針灸穴位或針灸類處理方案的文獻,微針療法(如僅用耳針、腹針、臍針、針刀或穴位注射等)作用于無具體用穴描述的臨床治療研究文獻。
1.3 文獻檢索 采用計算機檢索,電子資料庫范圍包括中文生物醫學期刊文獻數據庫(CMCC)、中國生物醫學文獻光盤數據庫(CBM disc)、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數據庫(VIP)。檢索年限均限定為2015~2020年,檢索詞限定為“功能性便秘”、“功能性便秘癥”,干預措施設定為“針灸”或“針刺”。
1.4數據庫的構建與預處理①數據庫的構建:依據納入與排除標準確定文獻,采用Office 2019建立數據庫,將文獻中的針灸取穴處方錄入數據庫,數據庫包含所有針灸處方取用的腧穴。②腧穴名稱的規范:本研究參照國家標準《腧穴名稱與定位》(GB/T12346-2006)對所有腧穴名稱的表達進行規范。③針灸處方庫的建立:初步搜索得到文獻286篇,排除不符合納入標準文獻,共納入113篇文獻,最終得到113條穴位處方。對于處方中雙側穴位,錄入一側穴位;對于組穴予以拆分,例如將“八髎”拆分為“上髎、次髎、中髎、下髎”,且只錄入一側穴位。
1.5 數據挖掘①描述分析:使用Excel 2019處理處方腧穴數據,計算出高頻腧穴的使用頻率及各種腧穴的分部、歸經、種類的頻數、頻率,繼而分析、歸納、總結取穴規律。②關聯規則分析:使用IBM SPSS Modeler 23.0中的Aprior模塊進行腧穴關聯規則分析,挖掘腧穴之間的配伍規律。③核心處方分析:根據腧穴在同一位置同時出現的不同頻次及其在處方中的重要程度,采用IBM SPSS Modeler 23.0中的Web復雜網絡繪制腧穴關聯關系整體與核心處方的網絡圖。
2 結果
2.1 腧穴頻數分析 結果顯示針灸治療FC共運用腧穴74個,總取穴頻次721次;使用頻次最高的是天樞和上巨虛,詳見表1。

表1 針灸治療FC常用腧穴頻率情況(頻數>5次)
2.2 腧穴-部位關聯頻數分析 對針灸治療FC所使用的74個腧穴進行分部統計,其中胸腹部和下肢部腧穴共40個,占總腧穴數的54.05%,而其余3個部位腧穴的總使用頻率僅占28.85%,詳見表2。

表2 針灸治療FC的腧穴-部位關聯情況
2.3 腧穴-經絡關聯頻數分析 針灸治療FC的選穴分布于13條經脈,胃經、任脈、膀胱經、及脾經4條經脈的腧穴使用頻次共計574次,占總頻次的79.62%;用穴共47個,占總腧穴數的63.51%,詳見表3。

表3 針灸治療FC的腧穴-經絡關聯情況
2.4特定穴關聯頻數分析 針灸治療FC的取穴包含了特定穴共50個,占總用穴數67.57%;募穴的使用頻次最多,占23.72%,其次為五輸穴(20.94%)和交會穴(19.56%),各類特定穴的使用頻次見表4。

表4 針灸治療FC的特定穴關聯情況
2.5 腧穴配伍關聯規則分析 本次腧穴配伍關聯規則分析,以針灸治療FC的113例處方中使用頻次在5次及以上的25種腧穴為關聯對象。將前項最小支持度設為15%,規則的最小置信度設為80%,得出最常用的15個腧穴配伍,按照置信度的高低排列,排在第1位的腧穴配伍項集為“天樞、氣海”,其支持度提示天樞和氣海同時出現在113例處方中的頻率為30.63%。而支持度排在第1位的兩組腧穴配伍“天樞、上巨虛”為69.37%,詳見表5。

表5 針灸治療FC的腧穴配伍二項關聯情況
2.6 腧穴關聯的復雜網絡分析 采用SPSS modeler Web復雜網絡對腧穴進行分析,設置閾值為絕對、強鏈接較粗,可顯示的最大鏈接數為80,弱鏈接上限為15,強鏈接下限為35,鏈接大小顯示強/正常/弱類別,生成圖1處方取穴整體網絡圖,通過粗線、細線和虛線表示穴位之間鏈接的強弱程度。將閾值改為總體百分比、強鏈接較粗,生成圖2處方取穴核心網絡圖,核心針灸處方組成為天樞、大腸俞、上巨虛、足三里、中脘、支溝、氣海、關元、腹結。

圖1 處方取穴整體網絡圖

圖2 處方取穴核心網絡圖
3 討論
功能性便秘是腸道病中的常見疾病,目前對其病機的闡述有多種學說,包括結直腸動力障礙學說、盆底功能失調學說、胃腸調節肽異常等學說[7],此外也與不良習慣等因素有關[8];從中醫理論角度,多由腸胃積熱、氣虛乏力、血虛津虧等因素所致[9],本病治法以補益氣血、養陰潤燥等為主[10]。針灸治療便秘的最早記載可見于《內經》,如《靈樞·雜病》有“腹脹,墻墻然,大便不利,取足太陰”等記載,《內經》主張用下肢足三陰經穴治療大便不利[11],《針灸甲乙經》補充腹部穴位,唐代孫思邈進一步擴大了治療用穴,涉及下肢部及腹部穴位、骶部穴位等。現代針灸診治功能性便秘的思路和模式,仍遵循辨證論治[12]。
通過本研究發現,在本病治療中,天樞、上巨虛、足三里、大腸俞為常用腧穴。天樞穴,居陰陽升降之所,為天地之樞機[13],穴位區域為腸道的體表投影區,與大小腸之間只有皮膚和腱膜等組織相隔,刺激易傳入其內,因而針刺天樞能夠調節氣機升降[14]。上巨虛穴為大腸下合穴,“治腑者,治其合”,有調理腸胃的功用[15]。足三里亦為胃下合穴,為六腑之氣下合于下肢足三陽經的腧穴[16],研究發現針刺足三里能夠明顯改善腸道功能[17-18];同時,通過經絡感應使胃經經氣疏通,從而促進胃腸道功能恢復。大腸俞為大腸的背俞穴,刺之能夠疏調腸腑、理氣化滯[19]。常用腧穴中,天樞、上巨虛、足三里、大腸俞均有調理腸胃、疏通經氣之效,以之為主穴,則便秘解之。
從腧穴分部與關聯經絡來看,取穴主要在胸腹部、下肢部及腰背部,主要集中分布在膀胱經、胃經、督脈、任脈。重視局部胃經、任脈取穴反映了“腧穴所在,主治所在”的近治規律[20]。下肢部取穴多為胃經穴位,與大腸關系緊密,體現出“經脈所過,主治所及”的遠治規律[21]。背部腧穴多為膀胱經上的背俞穴,與胸腹部募穴相配[22],療效愈彰。
從特定穴來看,特定穴的使用頻率遠超非特定穴,其中募穴使用頻次最高。募穴是臟腑之氣聚集于人體胸腹部的腧穴,六腑傳化而不藏,屬陽,陽病治陰,故募穴對腑病有著特殊的治療作用[23]。其次是五輸穴,是針灸遠部取穴的主要穴位。多選大腸經、胃經、小腸經、脾經等交會穴,以理氣除積,刺激腸腑經絡,氣暢則大腸傳導有力。五臟六腑之氣均輸注于足太陽膀胱經,針刺背俞穴可導氣機、暢氣血,使腸道氣血充盈,腸道得潤。
對腧穴配伍關聯規則結果進行分析,獲得針灸治療功能性便秘癥常用腧穴的組合,分析得到配伍方法有2種:足陽明本經配穴法、足太陽陽明經配穴法。注重特定穴的配伍,多用俞募配穴、合募配穴。取穴整體網絡圖顯示了針灸治療FC處方取穴的整體鏈接,取穴核心網絡圖直觀地呈現了針灸治療FC的核心處方組成為天樞、大腸俞、上巨虛、足三里、中脘、支溝、氣海、關元、腹結。
通過對針灸治療功能性便秘癥取穴規律的數據挖掘與分析,可以看出治療處方重視局部取穴,取穴以胸腹部、下肢部、腰背部為主,取穴特點以特定穴為主,其中特定穴中又多用募穴、五輸穴、下合穴、背俞穴。“經脈所過,主治所及”、“腧穴所在,主治所在”的取穴規律在采用的針灸治療中多有體現,俞募配穴、合募配穴也使用廣泛。本研究利用數據挖掘的方法整理、分析針灸治療功能性便秘癥的取穴規律,進一步優化了功能性便秘癥的針灸防治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