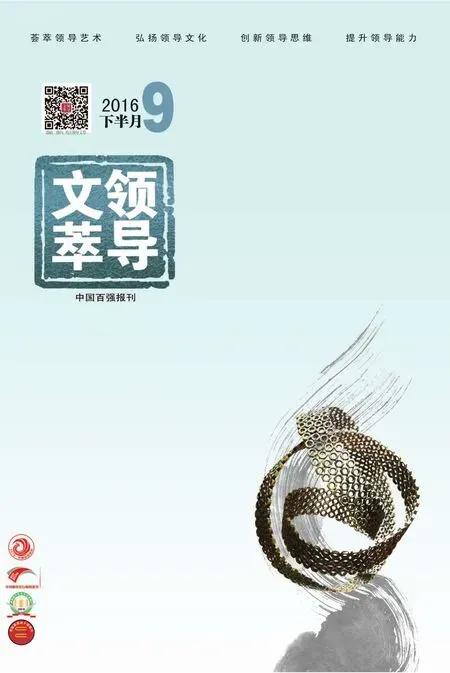唐朝詩人的“武功”
張嵚

李白“能寫又能打”,曾“手刃數人”;杜甫“騎胡馬,挾長弓,箭不虛發”……
向來以名詩名篇驚艷后世的唐朝“詩仙”李白,除了文采飛揚外,還有一個不太為人所知的本事——“武功”造詣。
一些野史或影視劇里塑造的李白,通常是看上去手無縛雞之力,落魄時還經常被欺負的文弱書生形象。但實際上,看李白的詩就知道,他的體能和“武功”一點也不差。比如騎射功夫,李白能做到“閑騎駿馬獵,一射兩虎穿”,可謂縱馬彎弓,瞬間獵殺百獸之王。
劍術更是李白的看家本領,以他《與韓荊州書》里的話說,“十五好劍術,遍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然后“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荊州”。劍術于他而言,不僅是一項傍身的本事,更是理想信念的寄托,在《行路難(其一)》里,他一聲“拔劍四顧心茫然”的詠嘆,不啻把自己視作一把未遇明主的“寶劍”。
李白精湛的劍法常常演繹出讓人震撼的一幕幕。如《結客少年行》里的“由來萬夫勇,挾此生雄風”;在《少年子》里,他更是“鞍馬四邊開,突如流星過”……好一副騎射劍法樣樣精通、快意恩仇的豪俠形象。如此“詩仙”,單是讀著他的詩,滾滾殺氣就撲面而來。
讀者可能會好奇,李白這直追武俠小說里絕世高手的強大“戰斗力”,會不會是他自吹自擂的呢?與李白同時代的人為此提供了重要佐證。
比如盛唐詩人崔宗之筆下的李白曾“起舞拂長劍,四座皆揚眉”。李白的追隨者魏顥(魏萬)也生動描述過他強大的“實戰能力”,說他“少任俠,手刃數人”。據《翰林學士李公墓碑》記載,李白的劍法師承“唐代三絕”之一的裴旻,絕非“野路子”。
不管這些記錄的可信度有多高,最能證明李白“武功”的,還是他一生的浮沉。要知道,李白從25歲起就“仗劍去國,辭親遠游”,看他那一句句詠嘆中華大好河山的詩篇就不難發現,如果沒有強健的體魄,沒有“少年負壯氣”的豪邁和實打實的硬功夫,根本不可能走完這“南窮蒼梧,東涉溟海”的艱苦路程。
當然,在大唐的詩人里,像李白這樣“能寫又能打”的人物并非個例。與李白齊名的“詩圣”杜甫同樣文武雙全。
作為西晉名將杜預的后人,杜甫的體魄不差,少年時就能做到“一日上樹能千回”。壯年時期的他更是“騎胡馬,挾長弓,箭不虛發”,甚至“長鈚逐狡兔,突羽當滿月”。沒有這樣的“武功”,他恐怕也登不上泰山,寫不出名篇《望岳》,更熬不過安史之亂。中唐詩人白居易也曾“金鐵騰精火翻焰,踴躍求為鏌铘劍”。看來,不同年代的大唐詩人心中都有一把劍。
在唐朝前后跨越三個世紀的詩人圈子里,“尚武”的風氣盛行,“武功”幾乎是詩人們的共同追求。翻開《全唐詩》,能讀到的不只是唐朝的風土人情,更有不少關于體育活動的“現場報道”。比如王建就寫下“珠球到處玉蹄知”的馬球比賽;李群玉的“三十六龍銜浪飛”還原了龍舟競渡時的熱鬧;劉行敏的“喚取長安令,共獵北山熊”講的是唐朝人的騎射生活……字字句句,無不反映出大唐的尚武風。
詩人不僅有才情,更有豪情。尚武風氣的背后,是他們不愿作為文人享受風花雪月、錦衣玉食的內心愿望,他們更希望“男兒一片氣,何必五車書”,“寧為百夫長,勝做一書生”,摒棄安逸的生活,走一條保家衛國之路。在《舊唐書》里,有籍貫和姓名可考,選擇投筆從戎、效力從軍的詩人共有180多位,他們以對國家、民族命運的自覺擔當,書寫了大唐盛世的歷史,吸引著后世無數敬仰的目光。
(摘自“朝文社”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