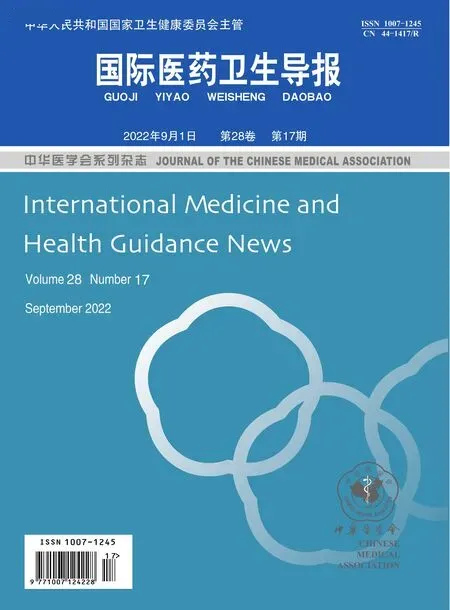IL-4、IL-6、IL-17、TNF-α在不同證型類風濕關節炎診斷中的應用
張婷婷 張程 牛廣華
1遼寧中醫藥大學,沈陽 110847;2遼寧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臨床檢驗中心,沈陽 110032
類風濕關節炎是臨床常見的全身性免疫疾病,以侵犯關節及周圍組織為主要疾病特征,全球內發病率約為1%,且發病率逐年升高。該病不僅損傷患者的關節生理結構,更影響軟骨和骨骼的生長,嚴重影響患者的日常生活,危害其健康[1-2]。目前此病的發病機制尚不明確,研究證實可能與白細胞介素(interleukin,IL)-17、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等炎性因子相關[3]。目前臨床中,主要采用非甾體類藥物、生物制劑等進行治療,以降低患者炎性反應水平、緩解臨床癥狀為主要治療目標,避免炎性反應對關節骨及軟骨組織產生永久損傷,但長期臨床效果較為有限[4]。
傳統醫學中將其歸入“痹癥”“歷節”“白虎病”等證的范疇,由于此病遷延不愈、病程較長,且病勢纏綿,臨床中辨證較為困難[5-6]。相關研究已證實不同辨證分型的類風濕關節炎患者的驗證因子水平存在差異,但相關炎性因子與中醫證型之間的關系仍需進一步探究。本研究通過檢測不同中醫證型類風濕關節炎患者的IL-4、IL-6、IL-17、TNF-α血清水平,探究不同證型與血清炎性因子水平的關系,為臨床辨證論治提供參考。
資料與方法
1、一般資料
本研究為前瞻性研究。選取2021年6月至11月遼寧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收治的類風濕關節炎患者共100例,其中男12例,女88例,年齡36~72(51.48±12.93)歲,病程3個月~21年[(53.98±10.08)個月]。其中中醫辨證分型肝腎不足證、寒濕痹證、濕熱痹阻證、痰瘀痹阻證分別為21例、35例、27例、17例。同時納入60例排除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壓等慢性疾病且生化指標檢測結果正常的健康志愿者作為對照組,其中男14例,女46例,年齡18~60(52.27±13.21)歲。
本研究方案經遼寧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倫理編號:2021052CS(KT)-033-01。所有患者知情同意并與之簽署臨床研究知情同意書。
2、類風濕關節炎患者的納入與排除標準
2.1、納入標準(1)患者符合類風濕關節炎的相關診斷標準[7],且依據《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8]中證型分類標準可分為肝腎不足證、寒濕痹證、濕熱痹阻證、痰瘀痹阻證;(2)就診時疼痛關節數5個及以上;(3)年齡<80歲;(4)納入試驗的30 d內未服用任何免疫抑制劑或激素類藥物。
2.2、排除標準(1)合并有其他感染性疾病或免疫缺陷類疾病;(2)近4周內服用免疫治療藥物或糖皮質激素類藥物;(3)長期服用抗生素類藥物的患者;(4)合并有腫瘤或其他系統性疾病及精神障礙的患者。
3、實驗試劑
IL-4、IL-6、IL-17、TNF-α細胞因子聯合檢測試劑盒購自江西賽基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批號:20201230)。檢測儀器為美國FACS Calibur流式分析儀。
4、試驗方法
對照組及類風濕關節炎患者于清晨空腹取靜脈血2 ml,以3500 r/min、4℃、離心半徑30 cm條件下,低速離心機(TDL8M,長沙平凡儀器儀表有限公司)離心10 min,取上層清液。流式分析儀對各組研究對象的血清IL-4、IL-6、IL-17、TNF-α水平進行檢測,嚴格依照試劑盒說明書中操作步驟進行操作。各樣本均一式兩份進行檢測。
5、統計學方法
選用SPSS 20.0對所有數據進行整理和分析,所有計量數據經檢驗均符合正態分布。計數資料以例(%)形式表示,采用卡方檢驗;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兩組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多組間比較選用單因素方差分析。以P<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果
1、各組一般資料比較
對照組及各分型組患者的性別、年齡等一般資料對比,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表1 對照組與不同證型類風濕關節炎患者的一般資料比較
2、各組IL-4、IL-6、IL-17、TNF-α水平比較
與對照組相比,肝腎不足證、寒濕痹證、濕熱痹阻證、痰瘀痹阻證組患者的IL-4、IL-6、IL-17、TNF-α水平均有所升高,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其中,寒濕痹證患者IL-4、IL-17、TNF-α水平明顯高于其他證型組,濕熱痹阻證患者IL-6水平明顯高于其他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2。
表2 對照組與不同證型類風濕關節炎患者的IL-4、IL-6、IL-17、TNF-α水平比較(pg/ml,±s)

表2 對照組與不同證型類風濕關節炎患者的IL-4、IL-6、IL-17、TNF-α水平比較(pg/ml,±s)
注:對照組為生化指標檢測結果正常的健康志愿者,依據《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中證型分類標準將100例類風濕關節炎患者分為肝腎不足證、寒濕痹證、濕熱痹阻證、痰瘀痹阻證。a與對照組相比,P<0.05;b與肝腎不足組相比,P<0.05;c與寒濕痹癥組相比,P<0.05;d與濕熱痹阻證相比,P<0.05
組別對照組肝腎不足證寒濕痹證濕熱痹阻證痰瘀痹阻證例數6021 3527 17 IL-41.65±0.343.31±0.82ac 8.27±2.20abd 3.12±0.40ac 3.40±0.42ac IL-62.68±0.7357.54±12.04ad 52.18±10.30ad 95.28±16.20abc 51.75±13.03ad IL-1710.18±3.0416.15±3.76ac 56.58±10.80abd 16.59±6.20ac 14.12±4.02ac TNF-α 1.42±0.396.65±1.06ac 16.61±2.90abd 7.15±2.07ac 5.91±1.94ac
討論
現代醫學認為,類風濕關節炎是一種由免疫細胞以及其分泌的炎性因子共同引起的慢性炎性病變,以炎性細胞浸潤、血管新生、滑膜增厚等為主要表現,最終進展為關節變形、功能障礙等[9-10]。類風濕關節炎在傳統醫學中被歸為“痹癥”“行痹”“鶴膝風”等證的范疇,臨床中以患者肢體關節僵硬、腫脹、麻木、酸痛、關節重著伴變形為主要臨床特征[11-12]。
研究證實,中醫藥治療對類風濕關節炎可以起到較好緩解作用,但辨證分型主要依靠醫者的經驗,缺乏更為客觀的臨床證據,且各家學者的辨證思路亦存在差異,遣方用藥及臨床效果也不盡相同。《素問·痹論》中提及:“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痹也。”當機體同時受到風邪、寒邪、濕邪侵襲時,則易發展為痹癥。當風邪較強時,則為“行痹”,以游走性疼痛為主要臨床表現;當寒邪較強時,則為“痛痹”,患者以關節寒冷肢痛為主要感受;當濕邪較強時,則為“著痹”,主要表現為關節重著、酸痛。痹癥以實邪為主,在發病過程中,瘀血、痰濁等病例產物瘀阻經絡,時日久則氣血損耗,可進展為不同程度的氣血陰陽虧損之證,與實邪相互夾雜,進而進展為肝腎不足證、寒濕痹證、濕熱痹阻證、痰瘀痹阻證等多種證型。而類風濕關節炎的辨證界定標準也尚未明確,臨床中的對證診治存在一定困難,因此探究各證型的客觀化、特異化指標對辨證論治的準確性十分重要,應用現代醫學手段與中醫理論相結合,提高患者的治療效率[13-14]。
相關研究表明,IL-6、IL-17、TNF-α及各趨化因子在類風濕關節的發生發展中發揮關鍵作用。輔助性T細胞/調節性T細胞(T helper 17/T regulatory 17,Th17/Treg17)比例失衡與類風濕關節炎的發病密切相關,這一失衡現象會進一步引起炎性細胞因子的分泌,進而上調IL家族等一系列炎性因子水平[15]。同時IL-6與IL-17可誘導血管內皮生長因子的水平上調,促進血管再生,這是類風濕關節炎患者產生軟骨損傷的主要機制之一。IL-6還可以通過相關途徑促使白細胞聚集于關節滑膜中,進而加重炎癥水平,以及激活破骨細胞等作用,進而加重骨損傷[16]。IL-17是一種信號分子,可上調IL-6、前列腺素E2(Prostaglandin E2,PGE2)等水平,同時還可以促進產生基質降解酶。研究證實,類風濕關節炎患者的滑膜炎性增加、病情加重、關節損壞加劇與IL-17水平的上調密切相關[17-18]。IL-4于1982年由Howard首次發現,主要由嗜堿性粒細胞、肥大細胞、Th2細胞等產生,屬于多效性細胞因子。它既可以促進Na?ve T細胞分化為Th2細胞。同時也在抑制IL-6、TNF-α等促炎細胞分泌中發揮關鍵作用,是風濕、系統性紅斑狼瘡等多種自身免疫疾病中發揮抗炎作用的主要因子之一。TNF-α是一種主要由巨噬細胞、單核細胞、T細胞產生的炎性因子,在類風濕關節炎的發生發展中也起關鍵作用[19]。它可以誘導炎性因子的分泌,加劇炎性反應,同時可促進趨化因子的生成,促進炎癥部位淋巴細胞的聚集。TNF-α水平與類風濕關節炎患者的病情嚴重程度呈正相關,它也可以促進金屬蛋白酶及蛋白酶水解酶的水平升高,進而加重軟骨組織的損傷,抑制破骨細胞的重吸收,加重骨損傷[20-23]。
本次研究中,通過分析類風濕關節炎患者的炎性因子水平特點,探尋本病辨證論治的臨床證據。結果表明,對照組及各證型組患者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具有可比性。與對照組相比,肝腎不足證、寒濕痹證、濕熱痹阻證、痰瘀痹阻證患者的IL-4、IL-6、IL-17、TNF-α水平均有所升高,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結果表明,血清炎性因子水平升高是各證型類風濕關節炎患者的共同特點。其中,寒濕痹證患者IL-4、IL-17、TNF-α水平明顯高于其他證型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提示IL-4、IL-17、TNF-α水平升高可能可以作為寒濕痹證患者的辨證輔助依據;而濕熱痹阻證患者IL-6水平明顯高于其他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提示IL-6水平升高可能可以作為濕熱痹證患者的辨證診治輔助依據。
本次研究中,由于研究環境限制,所納入的研究樣本數量有限,未來中應當擴大研究樣本量,或與其他科研單位聯合開展多中心臨床試驗,深入探究不同地域、不同年齡的類風濕關節炎患者的炎性因子水平特征,為臨床辨證論治、精準治療提供理論基礎。
綜上所述,不同證型類風濕關節炎患者的血清炎性因子水平不同,寒濕痹證型患者IL-4、IL-17、TNF-α水平最高,濕熱痹阻證患者IL-6水平最高,或可作為臨床辨證分型依據。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