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也可能會加劇收入和財富不平等
數字技術正在改變經濟,特別是人工智能方面,這些技術正在迅速改變我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但這種轉變帶來了一個令人不安的難題:即使在收入不平等加劇的情況下,這些技術對經濟增長并沒有發揮多大作用。
經濟學家認為,生產力增長對提高生活水平至關重要,但至少自2000年以來,許多國家的生產力增長基本處于低迷狀態。
為什么這些技術未能帶來更多的經濟增長?為什么它們沒有推動更廣泛的繁榮呢?
斯坦福大學數字經濟實驗室主任埃里克·布林約夫森在一篇名為《圖靈陷阱:類人人工智能的承諾與危險》的文章中寫道,人工智能研究人員和企業專注于構建機器來復制人類智能。
當然,這個標題是在引用艾倫·圖靈和他在1950年關于機器是否智能的著名測試:它能否很好地模仿一個人,以至于你無法判斷它不是人?布林約夫森說:“從那時起,許多研究人員就一直在追尋這個目標。”


但是,他說,對模仿人類智能的癡迷導致了人工智能和自動化往往只是簡單地取代了工人,而不是擴展人類的能力,使人們能夠完成新任務。
對于經濟學家布林約夫森來說,簡單的自動化在創造價值的同時,也可能導致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加劇。
他寫道,對類人人工智能的過度關注,壓低了大多數人的工資,“甚至它放大了少數擁有和控制這些技術的人的市場力量”。
他在文章中認為,對自動化的強調而非增強,是對在許多美國人的平均實際工資下降之際,億萬富翁崛起的“最大的唯一解釋”。
布林約夫森不是盧德主義者(反對改進工作方法的人,反對使用新機器的人)。他在2014年曾與安德魯·麥克菲合著過名為《第二個機器時代:輝煌技術時代的工作、進步與繁榮》的書。但他表示,人工智能研究人員的思維過于局限。
“我和很多研究人員交談過,他們說:‘我們的工作是制造一臺像人類一樣的機器’這是一個清晰的愿景。”但是,他補充說,“這也是一種懶惰的低標準。”
他認為,從長遠來看,通過使用人工智能來生產新的商品和服務而不是簡單地試圖取代工人,將能創造更多的價值。
但他表示,對于企業來說,在削減成本的驅動下,更換機器往往比重新考慮流程和投資利用人工智能來擴大公司產品、提高員工生產率的技術要容易得多。
人工智能方面的最新進展令人印象深刻,從無人駕駛汽車到類人語言模型應有盡有。然而,引導技術的發展軌跡至關重要。
由于研究人員和企業迄今做出的選擇,新的數字技術為擁有和發明這些技術的人創造了巨額財富,同時也破壞了那些容易被取代的工作機會。
這些發明在舊金山和西雅圖等少數城市創造了良好的技術工作崗位,而其他大部分人卻被拋在了后面。但這并不一定要這樣。
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達隆·阿齊默魯為自動化、機器人和算法在放緩美國工資增長和加劇不平等現象的作用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
他說,事實上,在1980年~2016年期間,美國工資不平等的增長有50%~70%是由自動化造成的。
這主要是在人工智能技術的使用激增之前。而阿齊默魯擔心,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動化會使情況變得更糟糕。
在20世紀早期和之前的時期,技術的轉變通常產生的好的新工作崗位比他們摧毀的要多,但情況似乎不再如此了。
其中一個原因是,公司往往選擇部署他和他的合作者帕斯夸爾·雷斯特雷波所說的“一般的技術”,這些技術取代了工人,但對提高生產力或創造新的商業機會貢獻甚微。
與此同時,企業和研究人員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人工智能技術在提供更好服務的同時擴大工人能力方面的潛力。
阿齊默魯指出,數字技術可以讓護士更準確地診斷疾病,或者幫助教師為學生提供更個性化的課程。
阿齊默魯說,人工智能科學家和大型科技公司都對做出有利于過度自動化的決定負有嚴重責任。
聯邦稅收政策利好智能化發展。雖然對人工被征收重稅,但對機器人或自動化都沒有工資稅。
而且,他說,人工智能研究人員“對致力于以許多人失業為代價的自動化工作技術毫無內疚”。
但他對大型科技公司保留最強烈的憤怒,他引用的數據顯示,美國和中國的科技巨頭資助了大約2/3的人工智能工作。
他說:“我不認為我們如此強調自動化是個偶然,因為這個國家的技術未來掌握在谷歌、亞馬遜、臉書、微軟等少數公司的手中,而這些公司恰是以算法自動化作為其商業模式。”
反彈效應
對人工智能在加劇不平等方面的作用的憤怒可能會危及該技術的未來。劍橋大學的經濟學家黛安·科伊爾在她的新書《齒輪與怪物:經濟學是什么,應該是什么》中指出,數字經濟需要以新的方式來思考進步。
“無論我們所說的經濟增長、情況好轉是什么意思,收益都必須比最近更平均地分享”,她寫道,“一個由科技百萬富翁或億萬富翁和零工組成的經濟體,其中中等收入的工作被自動化削弱,在政治上將是不可持續的”。
科伊爾說,為了提高更多人的生活水平和增加繁榮,需要更多地使用數字技術來提高各行業的生產力,包括醫療保健和建筑業。
但是,如果人們沒有看到好處——如果他們只是看到好工作被破壞,就不能指望他們接受這些變化。
在最近接受《麻省理工科技評論》采訪時,科伊爾說,她擔心科技領域的不平等問題可能會成為部署人工智能的障礙。“我們談論的是顛覆性的問題。”她說。“這些都是變革性的技術,可以改變我們每天花時間的方式,改變已經成功的商業模式。”她補充說,要想做出如此“巨大的改變”,你需要社會的支持。
科伊爾說,相反,許多人的不滿情緒正在醞釀之中,因為他們認為利益都歸于了少數的繁榮城市的精英階層。
以美國為例,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美國的各個地區——用經濟學家的話來說——都在“趨同”,金融方面的差距也在縮小。
然后,在20世紀80年代,在數字技術的沖擊下,這種趨勢被逆轉了。自動化摧毀了許多制造業和零售業的就業崗位,新的高薪技術工作崗位集中在幾個城市。
根據布魯金斯學會的數據,到2019年,包括舊金山、圣何塞、波士頓和西雅圖在內的美國八個城市的名單中,大約有38%的科技工作崗位。
新的人工智能技術尤其集中:布魯金斯學會的馬克·穆羅和劉思凡估計,僅僅15個城市就占了美國2/3的人工智能資產和能力。
少數城市在人工智能的發明和商業化方面的主導地位意味著財富上的地域差距將繼續飆升。
這不僅會引發政治和社會動蕩,而且正如科伊爾所言,它還可能阻礙區域經濟增長所需的各種人工智能技術。
部分解決方案可能在于以某種方式放松大型科技公司對界定人工智能議程的控制。這可能需要增加獨立于科技巨頭的聯邦研究資金來資助。
例如,穆羅和其他人已經建議提供巨額的聯邦資金來幫助建立美國的區域創新中心。
一個更直接的辦法是拓寬我們的數字想象力,設想人工智能技術不是簡單地取代工作,而是在增加國家不同地區最關心的領域(如醫療保健、教育和制造業)的機會。
改變思想
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研究人員喜歡去復制人類能力,這通常意味著試圖讓機器完成一項對人來說簡單、但對技術上困難的任務。例如,鋪床或制作濃縮咖啡。或者一輛自動駕駛汽車在城市的街道上行駛,或者一個機器人充當咖啡師。但很多時候,開發和部署這些技術的人往往沒有考慮到其對就業和勞動力市場的潛在影響。
弗吉尼亞大學經濟學家、布魯金斯大學魯賓斯坦研究員安東·科里內克說,一旦部署自動駕駛汽車,數百億美元的研發投入將不可避免地會對勞動力市場產生負面影響,奪走無數司機的工作。
他問道,如果這數十億美元投資于更有可能擴大勞動力機會的人工智能工具,會怎么樣?
科里內克解釋說,在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和國立衛生研究院等機構申請資金時,“沒有人會問,‘它將如何影響勞動力市場?’”
舊金山人工智能協作公司的政策專家卡蒂亞·克林諾娃正在研究如何讓人工智能科學家重新思考他們衡量成功的方式。
她說:“當你查看人工智能研究時,你會發現那些被普遍使用的基準,都是與人類表現相匹配或比較的。”也就是說,人工智能科學家對他們的程序進行打分時,以圖像識別為例,就是通過與人識別物體的能力相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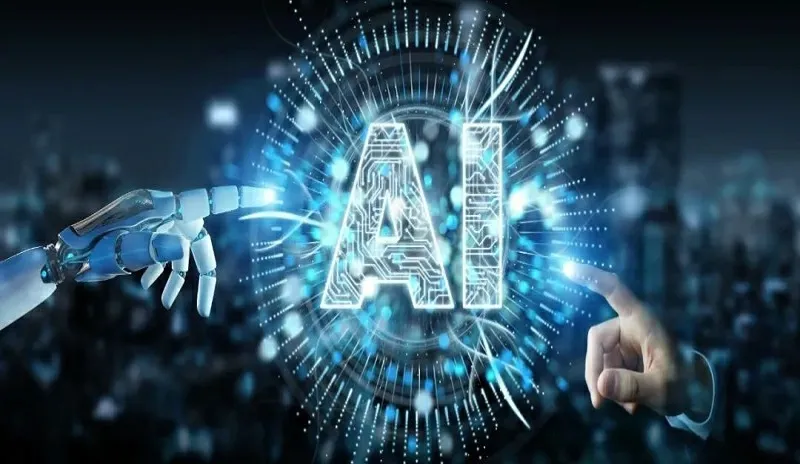
克林諾娃說,這些基準推動了研究的方向。她補充說:“現在出現的是自動化和更強大的自動化,這并不奇怪。”“基準對人工智能開發人員來說非常重要——尤其是對于大量正在進入人工智能領域并困惑著‘我應該做什么?’的年輕科學家來說。”
克林諾娃說,目前人機協作性能還缺乏基準,盡管她已經開始努力幫助創建部分基準。
她與她的人工智能協作的團隊也正在為沒有經濟學背景的人工智能開發者編寫用戶指南,幫助他們了解工人可能會如何受到他們所做研究的影響。
克里諾娃說:“這是在改變敘事方式,即人工智能創新者被給予一張顛覆性質的空白票,然后由社會和政府來處理。”她說,每家人工智能公司都有一些關于人工智能偏見和倫理的回答,“但它們仍然沒有考慮對勞動力的影響。”
流感大流行加速了數字化轉型。企業已經轉向通過自動化來取代工人,這是可以理解的。但這場大流行也表明了數字技術在拓寬我們能力的潛力。
他們為我們提供了新疫苗研發的工具,并為許多人提供了一種可行的居家辦公模式。
人工智能將不可避免地擴大其影響,而值得關注的是,這是否會給好工作帶來更大的損害以及更多的不平等。布林約夫森說:“我樂觀地認為,我們可以以正確的方式引導這項技術。”但他補充說,這將意味著要對我們創造和投資的技術做出慎重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