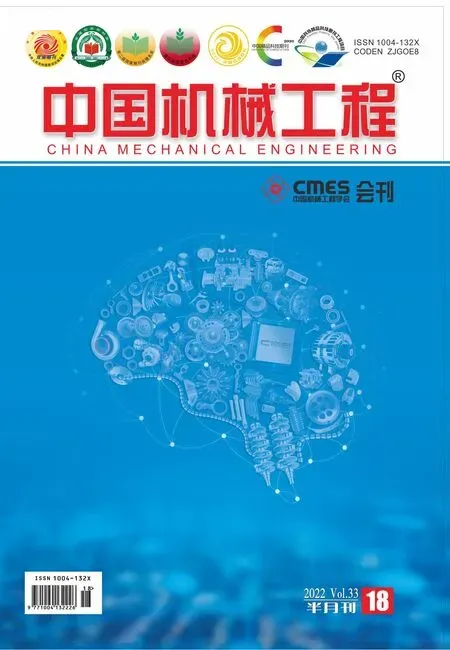內燃機曲軸扭轉疲勞強度試驗研究與分析
叢建臣 倪培相 孫 軍 呂世杰
1.山東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院,淄博,255000 2.天潤工業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技術中心,威海,264400
0 引言
曲軸是內燃機中動力傳輸的核心部件,工作中承受著復雜的彎曲、扭轉交變載荷作用。曲軸形狀復雜,主軸頸與連桿軸頸的連接過渡圓角、連桿軸頸油孔部位等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應力集中現象,在各種載荷周期性變化并相互作用下容易引起曲軸的彎曲和扭轉變形甚至產生裂紋和斷裂[1-3],而且一旦失效往往會引起其他重要機件的毀損,造成嚴重的后果。
彎曲疲勞斷裂和扭轉疲勞斷裂是內燃機曲軸最主要的兩種失效形式。傳統的國四及以下排放內燃機爆發壓力低,彎曲疲勞失效是內燃機曲軸的主要失效形式[4],因此人們比較重視,對曲軸彎曲疲勞性能進行了大量研究。陳淵博等[5]針對某車用柴油機,在提高爆發壓力條件下對曲軸進行了彎曲疲勞試驗和仿真分析,通過模擬彎曲疲勞試驗對曲軸進行圓角結構優化,提高了曲軸彎曲疲勞強度。CEVIK等[6]對球墨鑄鐵曲軸進行彎曲疲勞試驗和有限元建模,得到了圓角滾壓和未滾壓條件下的應力與循環次數的關系曲線,最終得出圓角滾壓工藝可以顯著提高曲軸疲勞極限的結論。叢建臣等[7]研究了曲軸在彎曲疲勞試驗時疲勞裂紋的擴展及疲勞失效判定問題,對曲軸彎曲疲勞試驗驗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導作用。QIN等[4]利用模擬方法研究了淬火過程產生的殘余應力對曲軸的疲勞強度的影響,利用臨界平面法將殘余應力疊加到彎曲應力上,對曲軸截面的疲勞強度進行分析評估,準確預測曲軸的彎曲疲勞強度。而對于曲軸扭轉疲勞失效,由于低爆壓下失效比例小,加之試驗條件的限制,故沒有得到足夠重視,國內外只針對曲軸扭振方面進行了一定的理論研究與分析[8-9],而關于曲軸扭轉失效的實體研究資料較少,劉紅福等[10]、馮美斌等[11]、ALDERTON等[12]對曲軸的扭轉強度進行過實物研究,但也只局限于球鐵曲軸,而且對扭轉失效模式和影響扭轉強度的因素研究得不全面,不夠系統,沒有從整體上對曲軸扭轉失效模式進行深入分析。
近年來,隨著內燃機向高功率、大扭矩方向發展,爆發壓力不斷增大,同時曲軸結構變得越來越緊湊。在內燃機爆壓提高、曲軸結構緊湊的情況下,為了減少曲軸的扭轉失效現象,主要通過匹配減振器對軸系扭轉振動幅值進行更為嚴格的控制[13]。匹配減振器后雖然軸系扭轉振動強度得到控制甚至有所降低,但由于爆發壓力的提高,曲拐所承受的氣缸壓力產生的激勵扭矩以及扭轉振動產生的附加扭矩會相應增大,使曲軸扭轉疲勞破壞風險增加[14]。在曲軸前期設計及試制過程中發生曲柄臂設計不合理導致疲勞強度達不到內燃機設計要求,在使用過程中經常發生因曲柄臂鍛造缺陷、油孔加工不良、軸頸淬火強化等因素導致的曲軸疲勞強度下降,從而引起曲軸扭轉斷裂。
因此,本文對上述影響曲軸扭轉疲勞強度的關鍵因素進行試驗研究,分析曲軸扭轉失效的主要原因并提出改進措施,對提高曲軸的扭轉疲勞強度具有重要意義和實用價值。
1 曲軸扭振分析
為了研究內燃機爆發壓力的提高對曲軸扭轉失效的影響,利用有限元法進行了曲軸扭振模擬計算,分析了曲軸在內燃機中不同爆發壓力下承受的扭矩變化。
圖1是12L排量的某型號六缸內燃機鍛鋼曲軸不同爆發壓力下最大動態扭矩隨轉速變化的曲線。經計算分析得出,在不同爆發壓力下,曲軸最大動態扭矩隨轉速均呈先增大后減小的趨勢,在轉速為1500 r/min和1900 r/min時出現兩個扭矩峰值。曲軸最大扭矩隨爆發壓力的增大而增大,在18 MPa爆發壓力下曲軸最大扭矩峰值為3740 N·m,在21 MPa爆發壓力下曲軸最大扭矩峰值為4380 N·m,爆發壓力增大3 MPa,最大扭矩增大了640 N·m,幅度提高了17%。因此,爆發壓力的提高使曲軸承受的扭矩大幅度提高,極大地增加了曲軸扭轉斷裂的風險。

圖1 不同爆發壓力曲軸最大動態扭矩隨轉速變化曲線Fig.1 The curve of maximum dynamic torque of crankshaft under different peak pressure
2 曲軸扭轉疲勞試驗
2.1 扭轉疲勞試驗定義
曲軸裝配到內燃機中后在使用過程中產生的扭轉斷裂失效無法再現,因此,研究其扭轉失效需要利用單件曲軸扭轉疲勞試驗的形式進行。
曲軸扭轉疲勞試驗是模擬曲軸在內燃機運轉過程中承受交變扭轉載荷作用是否發生失效的試驗過程。試驗時把樣件安裝在特定工裝上,通過專用曲軸疲勞試驗機進行反復加載,試驗樣件在試驗過程中未達到規定的循環次數就產生裂紋被定義為疲勞失效。
曲軸扭轉疲勞失效是指曲軸在扭轉交變載荷作用下循環一定周次后產生裂紋或發生斷裂的現象,主要反映了曲軸的抗扭轉疲勞能力。曲軸的疲勞失效都是由應力集中引起的,由于各部位應力集中程度的不同,失效位置也會不同,應力比較集中的部位容易首先產生裂紋,引起失效[15]。正常情況下,曲軸的連桿軸頸油孔處是應力最集中的部位,自身有缺陷的曲軸,缺陷部位應力集中程度可能大于連桿軸頸油孔處。因此,曲軸扭轉疲勞的主要失效部位一般在連桿軸頸油孔處,很少在其他缺陷部位,如主軸頸與連桿軸頸相連的曲柄臂側面、連桿軸頸下止點分模面處等。
2.2 試樣準備
通過對曲軸使用過程中發生的扭轉失效的總結以及曲軸在內燃機中的受力分析發現,曲柄臂設計、材料夾雜、連桿軸頸油孔加工、軸頸淬火情況等對曲軸的扭轉失效影響較大[16]。據此,以42CrMoA合金鋼材料和QT900-5球墨鑄鐵材料分別生產一款六缸曲軸毛坯和一款四缸曲軸毛坯,然后經粗加工、熱處理、精加工等工序制成表1所列的8種狀態的成品曲軸,用于疲勞試驗,其中軸頸淬火是指所有主軸頸和連桿軸頸淬火。同時,從試驗曲軸上取樣,檢測兩種材料曲軸的金相組織和力學性能,分別見表2、表3。

表1 試樣信息及數量Tab.1 The sample information and quantity

表2 試件的金相組織檢測結果Tab.2 The examination results of specimen metallographic

表3 試件的力學性能檢測結果Tab.3 The examination results of specimen mechanical property
2.3 試驗方案
曲軸扭轉疲勞試驗在進口德國Sincotec公司 POWER TORQUE 40 000 N·m型電磁諧振式曲軸扭轉疲勞試驗裝置上進行,如圖2所示。載荷為對稱的正弦波,加載頻率在60 Hz左右。按照JB/T 12662-2016《內燃機曲軸扭轉疲勞試驗方法》進行試驗。試驗前對試驗系統的載荷進行標定,標定后試驗載荷相對誤差不大于1.5%。規定所有試驗的循環數為1×107,設定系統的共振頻率下降1%,同時試樣表面相應的裂紋長度大于20 mm為試樣失效。

圖2 曲軸扭轉疲勞試驗裝置Fig.2 The crankshaft torsional fatigue test equipment
按照表1中的8種試樣狀態分別進行疲勞試驗。狀態1~4的鍛鋼曲軸采用通過法試驗,即所有試樣均用固定的試驗載荷進行試驗,判定試樣疲勞強度是否達到該載荷水平。通過法試驗的試驗載荷以正常合格曲軸在99.9%存活率下的極限疲勞強度為基準,本次試驗的該型號曲軸正常合格品在99.9%存活率下的極限疲勞強度為15 kN·m,因此基準試驗載荷定為15 kN·m。狀態5~8的球墨鑄鐵曲軸采用升降法試驗,即根據上一個試樣的試驗結果(通過或失效)決定下一個試樣的試驗載荷水平(升高或降低),直至全部完成試驗。試驗完成后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利用下式計算50%存活率下的曲軸扭轉疲勞強度T:
(1)
(2)
式中,Sri為相鄰兩級試驗載荷的平均值;Si、Si+1分別為出現相反結果的相鄰兩級試驗載荷,i=1,2,…;n為有效數據的對子數目。
疲勞試驗完成后,對失效試樣進行解剖分析,確定失效原因。
3 試驗結果
按照2.3節的試驗方案對4種有缺陷的曲軸試樣進行扭轉疲勞試驗,試驗載荷為15 kN·m固定載荷。試驗得出4種有缺陷試樣均發生疲勞失效,失效位置均在曲軸缺陷位置處,疲勞強度低于正常水平,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有缺陷曲軸的扭轉疲勞試驗結果Tab.4 Torsional fatigue test results of defective crankshaft
表5所示為軸頸淬火曲軸的扭轉疲勞強度試驗結果,利用式(1)計算得出,軸頸淬火曲軸在50%存活率下的扭轉疲勞強度為:T=[(4600+4750)/2+(4600+4450)/2+(4600+4450)/2+(4600+4450)/2]/4=4562 N·m。

表5 軸頸淬火曲軸的扭轉疲勞試驗結果Tab.5 Torsional fatigue test results of quenched crankshaft
按照同樣方法計算得出不同表面強化處理工藝和不同油孔加工工藝的球墨鑄鐵曲軸的扭轉疲勞強度,如表6和圖3所示。可以看出,無論軸頸是否淬火,球墨鑄鐵曲軸的扭轉疲勞失效位置都在油孔處,失效位置與淬火無關。軸頸淬火使扭轉疲勞強度大幅度降低,降低幅度在30%以上。軸頸淬火后進行油孔磨拋可以部分彌補因淬火導致的曲軸扭轉疲勞強度降低,但仍不能達到不淬火的水平。對于軸頸不淬火曲軸,油孔磨拋前后的扭轉疲勞強度沒有發生變化。

表6 不同處理工藝曲軸的扭轉疲勞強度Tab.6 The torsional fatigue strength of crankshaft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s

圖3 不同處理工藝曲軸的扭轉疲勞強度Fig.3 The torsional fatigue strength of crankshaft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s
4 影響扭轉強度的因素分析
4.1 曲柄臂設計對扭轉疲勞強度的影響
曲柄臂設計缺陷的兩個試樣扭轉疲勞試驗失效均在主軸頸與連桿軸頸相連接的曲柄臂處,如圖4a所示。由圖4b所示的斷口形貌分析發現,疲勞裂紋源位于曲柄臂表面,由表面向內部擴展。把斷口磨平后制成金相試樣,觀察斷口處的微觀組織,發現裂紋源附近夾雜物等缺陷,曲柄臂表面有深度約0.1 mm的輕微脫碳,在正常要求范圍內,如圖4c所示。曲軸生產加工不是導致其在曲柄臂處扭轉失效的主要原因。

(a)疲勞裂紋 (b)斷口形貌

(c)裂紋源微觀組織(100×)圖4 曲柄臂裂紋及斷口微觀組織Fig.4 The arm crack and fracture microstructure
經有限元計算分析得出,在扭轉載荷作用下曲柄臂側面應力集中最嚴重,應力集中是由結構設計時缺少材料導致的,與實際試驗失效部位吻合,如圖5所示。改變曲柄臂處的設計,增加徑向尺寸后生產小批量曲軸,再次進行疲勞試驗,不再從曲柄臂處失效。由此可見,曲柄臂側面向內凹陷的結構設計容易導致應力集中,扭轉疲勞從此處開裂,降低曲軸扭轉疲勞強度。在曲軸設計時,需要進行結構應力分析,確保曲柄臂側面沒有較大的應力集中,提高曲軸扭轉疲勞強度。

圖5 有限元分析應力云圖Fig.5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FEA
4.2 毛坯表面凹陷對扭轉疲勞強度的影響
毛坯表面有缺陷的兩個試樣在15 kN·m固定載荷下進行扭轉疲勞試驗,均發生疲勞失效,疲勞強度低于正常水平,失效位置均在曲柄臂的凹槽處,如圖6a所示。切割裂紋部位并解剖,發現裂紋源在曲柄臂表面凹陷的字號處,由表面向內部擴展,如圖6b所示。

(a)疲勞裂紋 (b)斷口形貌圖6 曲柄臂扭轉疲勞裂紋及缺陷Fig.6 The torsional crack and detect at crank arm
曲柄臂的凹槽容易引起應力集中,在交變扭轉載荷作用下,缺陷處應力集中加劇,當應力集中程度超過了材料本身的抗應力水平時便產生了裂紋[17],隨著裂紋的不斷擴展曲軸發生失效。在曲軸標識的設計和位置選擇時,需要設計為向外凸出的標識,避免凹陷標識導致的材料應力集中,同時標識位置盡量選擇對強度影響較小的配重鐵等部位。
4.3 材料夾雜對扭轉疲勞強度的影響
材料有夾雜的兩個試樣在15 kN·m固定載荷下進行扭轉疲勞試驗均發生失效,疲勞強度低于正常水平,而且在連桿軸頸下止點處失效。裂紋與曲軸軸向平行,主裂紋較粗較長,橫穿整個連桿軸頸,主裂紋兩側有較多鋸齒狀小裂紋,小裂紋與軸向成45°角交叉擴展,是典型的因扭轉力矩產生的剪切裂紋,如圖7所示。

圖7 連桿軸頸下止點扭轉裂紋Fig.7 Torsional crack at bottom dead center of con-rod journal
圖8為裂紋部位的夾雜物分布照片,圖9為夾雜物能譜圖。經檢測發現,連桿軸頸裂紋位置恰好是曲軸毛坯分模面處,且裂紋位置有較多的夾雜物,其主要含有硫、錳元素,詳見表7。

圖8 裂紋附近夾雜物分布(500×)Fig.8 The inclusion distribution near crack

圖9 夾雜物能譜圖Fig.9 Inclusion energy spectrum

表7 夾雜物能譜成分檢測結果表Tab.7 The detection results of inclusion composition by energy spectrum
曲軸分模面是圓棒型鋼材開始熱模鍛成形時多余金屬流出形成飛邊的中心面。鍛件整個形變過程中原材料中心部位的缺陷和夾雜物向分模面匯集而密布于切邊處,如圖10所示。

圖10 曲軸分模面夾雜物分布照片Fig.10 The distribution of inclusions on parting surface of crankshaft
對于鍛造可變形的非金屬夾雜物,如硫化物和多數硅酸鹽等,在分模面沿金屬延伸方向而呈片狀形式存在;對于鍛造不可變形的非金屬夾雜物,如氧化物和氮化物等,則在分模面沿金屬延伸方向呈面網狀形式存在[18]。分模面處過多的夾雜物導致晶粒間的結合力弱,強度降低。在扭轉載荷作用下,該處應力集中并提前達到材料的疲勞極限應力,導致裂紋產生并失效。
因此,在曲軸鍛件生產過程中,需要提高原材料鋼材的純度,減少圓棒型鋼材中心部位的夾雜物含量,同時優化曲軸毛坯鍛造方式,使鍛造過程中原材料內部夾雜物不流到曲軸軸頸表面,提高曲軸表面的材料強度。
4.4 油孔加工對扭轉疲勞強度的影響
油孔內壁粗糙的兩個試樣在15 kN·m固定載荷下試驗,疲勞強度低于正常水平,失效位置在連桿頸斜油孔處,裂紋方向與軸向約成45°角,如圖11a所示。圖11b所示為連桿頸裂紋斷口形貌。觀察發現,裂紋源在斜油孔內壁離軸頸表面約10 mm處,裂紋呈放射狀向油孔兩側基體內部擴展,同時發現油孔內壁有明顯的比較粗糙的加工刀痕。

(a)連桿油孔裂紋 (b)斷口形貌圖11 連桿油孔疲勞裂紋及斷口形貌Fig.11 The oil crack at pin journal and fracture morphology
圖12所示為斷口裂紋源附件的金相組織。在斷口裂紋源附近切取金相試樣,試樣經研磨、拋光后用4%的硝酸酒精腐蝕,在光學顯微鏡下觀察其顯微組織。裂紋源附近不存在夾雜物,組織為正常的回火索氏體。由此判斷,裂紋源的產生不是由夾雜物和組織異常所引起的。

圖12 裂紋源金相組織(500×)Fig.12 The microstructure of crack source(500×)
圖13為油孔內部裂紋源位置的掃描電鏡觀察照片。經觀察發現,油孔內壁加工刀痕處有明顯的微裂紋。在往復試驗載荷作用下,微裂紋處產生嚴重的應力集中,裂紋繼續擴展發生疲勞失效。

圖13 油孔內壁電鏡照片(200×)Fig.13 The SEM micrograph of oil hole inwall(200×)
在曲軸油孔加工過程中,優化合金鉆頭的涂層,精準匹配潤滑油氣量,可以減小金屬切削摩擦力,同時選用高精度液壓夾持鉆頭刀柄以減小鉆頭旋轉時的撓度,從而提高油孔內壁粗糙度水平,減少因油孔內壁粗糙和微裂紋導致的疲勞失效。
4.5 軸頸表面淬火對扭轉疲勞強度的影響
圖14所示為軸頸淬火曲軸疲勞失效試樣的斷口形貌及金相組織。經分析發現,疲勞裂紋源位于油孔內壁,距軸頸表面約8 mm,油孔口處的淬火層深度約為3 mm,裂紋源并不在淬火層內,已遠離淬火層,而且失效試樣的油孔內壁相對光滑,無明顯加工刀痕等缺陷。

(a)試樣斷口形貌 (b)斷口磨削拋光腐蝕后圖14 淬火曲軸扭轉失效試樣斷口Fig.14 The fracture of hardening crank torsion failure specimen
圖15所示為油孔內壁拋磨前后粗糙度對比情況。經檢測對比發現,磨拋后的油孔內壁粗糙度Ra與拋磨前處于同一水平,Ra值均在1.4~1.6 μm之間。由此判斷,油孔內壁粗糙度不是影響曲軸扭轉強度的主要因素。

圖15 拋磨前后油孔內壁粗糙度對比Fig.15 The roughness comparison of oil hole inwall before and after polished
對試樣斷口磨平、拋光、腐蝕后按GB/T9441《球墨鑄鐵金相檢驗》標準對裂紋源處進行顯微組織檢驗。結果表明:裂紋源處球化組織良好,球化2級,球徑大小為5級,如圖16a所示,基體組織由珠光體和少量鐵素體組成,珠光體片間距很小,組織正常,如圖16b、圖16c所示。這說明軸頸淬火曲軸疲勞強度低與油孔部位的材料組織沒有關系。

(a)裂紋源球化組織(100×) (b)裂紋源金相組織(100×)

(c)基體組織放大(500×)圖16 油孔裂紋源微觀組織Fig.16 The microstructure of oil hole crack source
利用Stress-3000(G3)型X射線衍射儀測量曲軸油孔內壁的殘余應力,檢測結果見圖17。不磨油孔的試樣在距油孔口6 mm處的油孔內壁存在100 MPa左右的拉應力,拋磨油孔試樣的油孔內壁為-300 MPa左右的壓應力,油孔拋磨前后的內壁殘余應力變化很大。

圖17 拋磨與不拋磨油孔內壁殘余應力Fig.17 The residual stress of oil hole inwall between polished and non-polished
上述試驗結果分析表明,影響曲軸扭轉疲勞強度的最大因素是軸頸淬火,主要原因是淬火過程中在曲軸油孔內壁淬火層以下某一區域由于熱影響形成了一定的拉應力,當外加應力載荷與油孔自身拉應力疊加超過材料強度極限時,引起材料提前開裂,導致曲軸疲勞強度降低[19]。
5 結論
(1)隨著內燃機爆發壓力的提高,曲軸扭轉振動增大,扭矩增大。六缸內燃機爆發壓力由18 MPa提高到21 MPa,扭矩增大17%。
(2)曲軸扭轉疲勞失效主要在連桿油孔、曲柄臂和連桿軸頸三個位置。連桿油孔是曲軸扭轉疲勞失效最常見部位,裂紋源一般在油孔內壁距軸頸表面約8~10 mm;曲柄臂失效主要由曲軸設計缺材和毛坯表面缺陷導致;連桿軸頸失效主要由連桿軸頸分模面存在材料疏松缺陷導致。
(3)曲軸軸頸表面感應淬火使油孔內壁某一區域形成了一定的拉應力,降低了曲軸的扭轉疲勞強度,強度比不淬火曲軸降低約30%。油孔內壁拋磨工藝可使軸頸表面淬火曲軸的扭轉疲勞強度提高2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