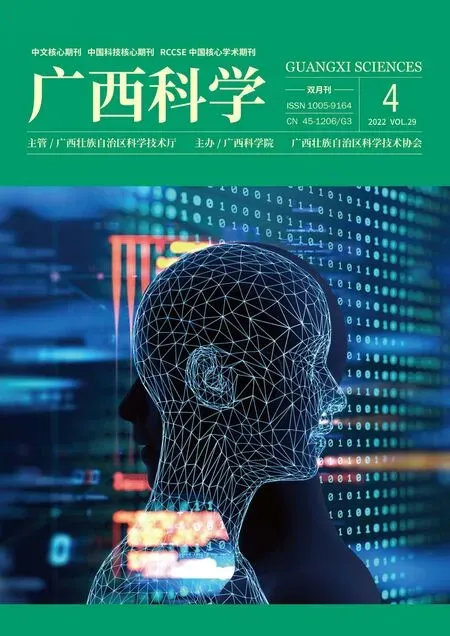紅樹林廣州小斑螟發生與氣象因子的關系研究*
張 悅,陳燕麗,黃 瀅,許文龍
(1.中國農業大學,北京 100193;2.廣西壯族自治區氣象科學研究所,廣西南寧 530022;3.防城港市氣象局,廣西防城港 538001)
紅樹林主要生長在熱帶、亞熱帶的潮間帶,是陸地過渡到海洋的特殊森林群落,是海洋生物資源的寶庫之一。在農業發展過程中,紅樹林能夠提供豐富的動植物產品和燃料等資源;在環保方面,則能發揮調節氣候、保護動植物資源、減少自然災害等功能。
紅樹林處于海洋與陸地的交錯帶,屬于生態脆弱帶和生態敏感帶,因其生長環境溫度高、濕度豐富,是蟲害發生發展的重災區。在紅樹林生長過程中發生的蟲害種類很多,近十余年廣西紅樹林幾乎每年都不同程度地遭受蟲害,導致紅樹植物生長受限,嚴重時大面積死亡。蟲害也是調控紅樹林植物種群動態的重要因素。廣州小斑螟(OligochroacantonellaCaradja)是紅樹植物白骨壤最普遍也是最主要的食葉害蟲,屬鱗翅目(Lepidoptera)螟蛾科(Pyralidae),其種群密度在每年的5-6月有明顯的峰值。該蟲具有暴食性,蟲害發生時短時間內白骨壤林的葉片可被吃光,嚴重阻礙白骨壤的正常生長[1]。2004年廣西壯族自治區山口國家級紅樹林生態自然保護區暴發了40年來最嚴重的廣州小斑螟蟲災,白骨壤中絕大多數葉片葉肉、幼葉及果實均被害蟲啃食,種子幾乎顆粒無收,樹木嚴重枯萎,對第二年的繁殖造成嚴重的影響;2015年柚木駝蛾(HyblaeapueraCramer)蟲害,造成紅樹林大面積枯萎死亡,紅樹林生境面臨嚴重威脅。大面積嚴重蟲害的暴發引起了專家學者的重視[2]。
目前已有的研究表明,海溫[3]、厄爾尼諾事件、大氣環流[4,5]等大尺度因子對蟲害的發生流行具有明顯的前兆性指示,氣候變化可能造成蟲害危害的地理范圍擴大,程度加劇[6]。氣象因素是影響森林蟲害發生發展的重要因子之一,包括溫度、相對濕度、日照、風速和降水等因子。氣候變化及氣象要素的相互影響、共同作用可以通過影響害蟲自身的生態學特征、天敵的行為和數量、植株體內營養成分以及整個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綜合作用于害蟲的種群數量,從而影響害蟲的發生頻率和程度[7]。如影響森林蟲害發生面積、松材線蟲病疫情發生的氣象因子影響力由大到小依次為≥10℃積溫、年降水量、干燥度以及年平均風速、年蒸發量[8]。明確蟲害與氣象因子的關系,對于建立相應的氣象指標有效預報及防治病蟲害、做好氣象保障及確保紅樹林繁殖生長至關重要。通過室內飼養試驗和野外觀察,發現廣州小斑螟發生與灘位、方位、海水的水溫等環境因素相關[1]。梁燕紅[9]還將數據挖掘技術引入紅樹林蟲害成因分析中,得出廣州小斑螟發生成因影響力由大到小依次為1月降水量、1月平均氣溫、4月平均氣溫、4月降水量。但選取的氣候要素、時段及時長尺度有限,鮮見其他氣象因子的相關研究。因此,本文基于廣西壯族自治區山口國家級紅樹林生態自然保護區2004-2015年廣州小斑螟蟲害災情數據及氣候資料,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法,以月、旬為尺度逐步揭示影響蟲害發生的關鍵氣候因子及影響時段,為紅樹林廣州小斑螟蟲害防治預警提供科技支撐。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域概況
研究區域地處北海市合浦縣(108°51′-109°46′ E,21°27′-21°55′ N),屬亞熱帶海洋性氣候。歷史50年(1961-2010年)年平均氣溫23.2℃,且氣候變暖趨勢顯著(P<0.01),氣溫增長速率為0.2℃/10 a。年降水量1 768.4 mm,總體有增多趨勢,降水量每10年增加53 mm。年際間差異較大,降水最高時達2 878 mm,最低時為907 mm(圖1)。所處地理位置光熱條件較好,海灣侵入內陸,封閉性好,風浪、潮汐、余流的作用較弱,岸灘比較穩定,海水污染程度很低,水質潔凈,擁有良好的濱海濕地生態系統,是中國紅樹林濕地的保護重地。目前北海市紅樹林濕地面積約3 700 ha,約占全國內地紅樹林面積的16%,除合浦紅樹林保護區外,馮家江和大冠沙等河口潮間帶或海岸均有紅樹林生長[10]。

** indicates significance at P<0.01
1.2 數據來源
1961-2000年及2004-2015年氣象數據來自北海市合浦縣氣象站,距離山口保護區3 km。氣象要素包括逐日最高氣溫、最低氣溫、平均氣溫、降水量、空氣相對濕度等。2004-2015年廣西壯族自治區山口國家級紅樹林生態自然保護區廣州小斑螟發生面積來自文獻[2]及該保護區管理處。
1.3 統計分析
采用農業氣候分析方法,分析紅樹林蟲害發生發展過程(5-6月)中及發展前的7個月(上年10月-今年4月)的氣溫、降水量、相對濕度、風速等氣象環境因子特征。
廣州小斑螟發生程度以年發生面積為依據,因子普查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法,分析紅樹林蟲害發生發展過程(5-6月)中及發展前的7個月(上年10月-今年4月)不同月、旬尺度上的氣溫、降水量、相對濕度、風速等氣象環境因子與受災面積的相關關系,篩選與廣州小斑螟發生程度顯著相關的關鍵氣象因子及影響時段,相關系數的檢驗采用雙尾t檢驗。
氣溫相關指標選取月(旬)平均最高氣溫、平均最低氣溫、平均氣溫和平均氣溫>30℃日數。濕度相關指標選取月(旬)平均相對濕度、相對濕度<70%日數、相對濕度>80%日數和相對濕度>90%日數。降水量相關指標選取月(旬)累積降水量及平均降水量。風速相關指標選取月(旬)平均風速。
考慮到昆蟲對溫度和濕度條件的綜合要求,采用溫濕系數表征溫濕綜合條件,即
溫濕系數=相對濕度/溫度。
2 結果與分析
2.1 2004-2015年研究區域氣象條件
溫度方面,2004-2015年蟲害發生期間(5-6月)及發生的前7個月(上年10月-今年4月)中,5月的平均氣溫最高,為29.2℃,6月>30℃日數最多,為13 d;1月平均氣溫最低,為14.8℃(表1)。
降水方面,2004-2015年蟲害發生期間(5-6月)及發生的前7個月(上年10月-今年4月)中,6月的平均降水量最高,為10.73 mm;上年12月的平均降水量最低,為1.02 mm。風速方面,1月的日平均風速最高,為2.07 m/s;上年10月的日平均風速最低,為1.87 m/s(表1)。
相對濕度方面,2004-2015年蟲害發生期間(5-6月)及發生的前7個月(上年10月-今年4月)中,3月的日平均相對濕度最高,為81.6%,同時相對濕度>80%和>90%的日數也最多,分別為19 d和6 d。上年12月相對濕度最低,同時相對濕度<70%日數也最多,為17 d (表1)。

表1 2004-2015年北海各氣象要素指標
2.2 2004-2015年年份間氣象要素對比
北海市災情較為嚴重[受災面積>1 000畝(約666 666.67 m2)]的年份為2004年和2008年,較輕[受災面積<100畝(約66 666.67 m2)]的年份為2005年、2007年、2011年和2012年,分析對比了兩種受災類型年份及歷史40年(1961-2000年)降水量、風速、溫度和相對濕度各項指標的差異。溫度方面,受災較重年份5月(蟲害發生月)的日最高氣溫、最低氣溫及平均氣溫均略高于受災較輕年份及歷史40年均值。且受災較重年份5月和6月(均為蟲害發生月)日平均氣溫>30℃日數顯著高于歷史水平(P<0.05),即受災較重年份蟲害發生月的總體溫度較高(圖2)。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相對濕度方面,總體而言災情重的年份各月相對濕度、相對濕度>80%日數和相對濕度>90%日數均顯著低于歷史水平(P<0.05),分別比歷史值低6.3%、34.4%和53.5%。受災輕年份的相對濕度<70%日數顯著大于歷史年份。災情輕、重年份之間相對濕度差異不顯著(圖3)。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降水量方面,災情重的年份降水量略高于災情輕的年份,蟲害發生月5月及上年10月、11月,受災重的年份降水量顯著高于災情輕的年份及歷史年份,5月、10月及11月災情較重年份的降水量分別為災情較輕年份的5.8倍、2.7倍和1.8倍。風速方面,2004-2015年各月平均風速低于歷史年份(圖4)。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2.3 月尺度相關性分析
溫度方面,2004-2015年廣州小斑螟的發生與6月平均氣溫>30℃的日數呈負相關且相關性最高,相關系數和決定系數分別為-0.55(表2)和0.30,與6月最低氣溫、5月最高氣溫和6月平均氣溫同樣呈負相關。與上年10月平均氣溫>30℃日數呈正相關且相關性較高,相關系數和決定系數分別為0.46(表2)和0.21。

表2 2004-2015年各月份溫度相關指標與受災面積的相關系數
濕度方面,廣州小斑螟的發生與2月和3月相對濕度<70%日數呈正相關且相關性較高,相關系數分別為0.51和0.50(表3),決定系數分別為0.26和0.25。與5月、6月溫濕系數呈正相關,但與蟲害發生前幾個月的溫濕系數呈負相關,說明害蟲發生的不同階段所需的環境溫度和濕度配合是不同的。
降水量方面,蟲害的發生與1月平均降水量和累積降水量相關性最高且呈正相關,相關系數均為0.49(表3),決定系數均為0.24。風速方面,蟲害的發生顯著受2月和5月日平均風速的影響,且呈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分別為0.84和0.68(表3),決定系數分別為0.71和0.46。

表3 2004-2015年各月份相對濕度、溫濕系數、降水量及風速相關指標與受災面積的相關系數
綜上,基于月尺度的分析可知,蟲害的發生受蟲害發生月(5-6月)及當年2月、3月各氣象因子影響較大,其中與2月及5月風速呈顯著正相關。
2.4 旬尺度相關性分析
基于月尺度的分析結果,以旬為尺度,分析了蟲害面積與蟲害當年2月、3月、5月和6月各旬氣象要素的相關性。溫度方面,2004-2015年廣州小斑螟的發生與6月上旬最低氣溫和平均氣溫>30℃日數相關性最高,相關系數為-0.75和-0.72(表4),決定系數為0.56和0.51。

表4 2004-2015年2月、3月、5月、6月各旬溫度、相對濕度、溫濕、降水量及風速相關指標與受災面積的相關系數
濕度方面,蟲害的發生與3月上旬平均濕度<70%日數相關性最高,相關系數為0.82(表4),決定系數為0.67。其次為2月中旬相對濕度<70%日數,相關系數和決定系數分別為0.56(表4)和0.31。蟲害的發生還顯著受2月上旬溫濕系數影響,與其呈正相關,相關系數和決定系數分別為0.69(表4)和0.48。
降水方面,蟲害的發生顯著受2月上旬降水量影響,且兩者呈正相關,相關系數和決定系數分別為0.86(表4)和0.74。風速方面,蟲害的發生同樣顯著受2月上旬風速影響,相關系數和決定系數分別為0.58(表4)和0.33。
綜上,基于旬尺度的分析可知,蟲害的發生顯著受當年2月上旬環境條件影響,并與風速、降水量及溫濕系數呈正相關,與日平均氣溫呈負相關。
3 討論
風對昆蟲的傳播起著巨大作用,它可以幫助昆蟲飛翔和遷移。本研究中2004-2015年廣州小斑螟發生顯著受2月上旬風速的影響,且兩者呈正相關。這可能是由于2月風速與害蟲取食等活動的關系十分密切,影響昆蟲遷飛擴散[11],該結果類似稻水象甲(LissorhoptrusoryzophilusKuschel)在微風條件下出現遷飛峰期[12]及黏蟲[Mythimna separata (Walker)]有偏愛迎風起飛的習性[13]。
濕度和降水量同樣是影響害蟲數量變動的主要因素,喜濕性害蟲要求濕度偏高(相對濕度≥70%),喜干性害蟲要求濕度偏低(相對濕度<50%)。廣州小斑螟蟲害的發生與2月上旬降水量及相對濕度呈正相關,該結果與前人的研究結果一致,即蟲害發生級別與1-2月降水量關聯性最強[9],這可能是由于濕度因素適宜其生長要求時,害蟲會迅速繁殖,達到嚴重等級的可能性較大[9]。相似蟲害如稻縱卷葉螟(CnaphalocrocismedinalisGuenee),其在春季雨水充足空氣濕度較高時,更易大發生[14],這可能是由于廣州小斑螟和稻縱卷葉螟發展前期均要求濕度偏高。
溫度對蟲害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有利于害蟲生長發育和存活,加速種群增長,增加害蟲發生世代數,提高越冬存活率[15]。溫度是維持昆蟲體溫的熱能來源,害蟲會因低溫而停育甚至死亡,同樣地,溫度過高也會對害蟲的發育起到抑制作用,如稻飛虱的發生與冬季最低溫度成正相關,冬季最低溫度上升有利于稻飛虱卵越冬,從而造成來年害蟲數量增多[16]。白背飛虱的若蟲和全世代發育速率、成活率隨溫度升高呈Logistic曲線變化趨勢,當溫度超過35℃時孵化率下降,若蟲死亡[17]。對于廣州小斑螟的發生而言,前人研究表明,當蟲害發生前期(2月)及蟲害發生期(5-6月)降水量都較少的情況下,2月平均氣溫將成為蟲害發生量的主導因素[9]。而本研究區域內蟲害發生期(5-6月)降水量較大(236.0 mm),因而蟲害的發生與前期(2月)溫度無顯著的相關性。本文中廣州小斑螟的發生與6月上旬溫度呈負相關,可能由于溫度增高,害蟲取食較多,消化快而發育加快,壽命相對縮短。
然而本文僅考慮一定地面氣象條件對廣州小斑螟發生發展的影響,但實際其發生發展除受地面氣象條件的重要影響外,還受大尺度環流背景、海水溫度、蟲源基數、自身生物學特性、天敵情況及人為防治等綜合因素的影響[18],今后的研究中可結合海水水溫、取食量試驗及風向等監測數據,綜合各項指標構建廣州小斑螟適宜度等級監測預報模型,并用于評估危害程度,開展相關農業氣象業務和服務,為政府和生產部門及時采取防范措施、有效防控提供科技支撐和決策依據。
4 結論
本文基于2004-2015年廣州小斑螟災情面積數據及氣候資料,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法,分別于月尺度和旬尺度篩選與廣州小斑螟發生程度顯著相關的關鍵氣象因子及影響時段,結果表明研究區域內廣州小斑螟的發生顯著受2月上旬環境條件的影響,并與風速、降水量及溫濕系數呈正相關,與日平均氣溫呈負相關。